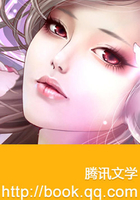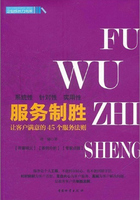众人被她一惊一乍的吓了一跳,李侧妃喝道;“你这蹄子,要死吗?作甚么大惊小怪的,有话说就是了,也不看看王爷在这儿呢吗?”
杏儿吓得赶紧跪下回道:“是奴婢不好,惊了王爷和王妃娘娘。”水溶摆摆手道:“好了,你且说你想到什么了吧?”
杏儿才敢回道:“奴婢记得约莫十天前,夫人正在午睡,奴婢就出去了一趟。”水溶见她欲言又止地,就问道:“你不好好在屋里守着,出去干什么?”
杏儿见问,嗫嚅了一阵,脸憋得通红,方期期艾艾地回道:“奴婢……奴婢上茅厕了。”众人听了都捂着嘴儿偷笑,水溶也撑不住了笑了一回,复又正容道:“说下去。”
杏儿说道;“奴婢那日不知吃了什么不相干的东西,肚子绞痛个不停,就在茅厕里蹲了半天。”其实她没好意思说,李侧妃把送来的点心、补品的都散给下人了,杏儿又是她身边第一得用的,看见吃的就囊桑了个饱,撑的拉肚子去了。
“奴婢出来后,头就晕乎乎的,晃晃悠悠地往院里走,还没进院门口就见一个人鬼鬼祟祟地往里进。奴婢想着这个时分怎么还有人到处走动,就加了意,只见她神神秘秘地进了夫人的正屋,夫人正在午睡,奴婢紧赶着就进去了。”
“那莲儿却正往外走,不防就和奴婢撞了个满怀。奴婢当时气得骂着她:‘你个死蹄子,不在屋里挺尸,跑这儿干什么?’当时莲儿满脸笑容说道:‘侧妃午膳前吩咐了,让我到冰窖里拿些冰块来,谁知道找看冰窖的人找了半天才找着,刚取来就紧赶着送过来了。’奴婢当时也没在意,这事就过去了。如今想来,定是莲儿无疑了。”
只见莲儿跪在地下浑身如筛糠般地抖着,没等水溶问话,就跪上前去,磕头如捣蒜般地回道:“主子饶命啊,不是奴婢放的雌黄和石榴花啊。”
众人俱都面面相觑:这真是不打自招啊,她怎么知道里面放的是雌黄和石榴花的?
水溶也笑了:“既然不是你干的,你怎么知道盒子里的胭脂掺有雌黄和石榴花啊?”莲儿没想到自己这般不经吓,现在已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也就没什么好辩的了,索性只低着头不说话。
李侧妃在床上疯了一般就要下来,杏儿忙上前扶住了,劝道:“夫人,你才刚小产,可大意不得呢。还是好好养着吧。”
李侧妃破口大骂着:“好你个莲儿,还真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呢。杏儿,拿着这个,把她的手戳烂。”说着,就递给杏儿“一丈青”,杏儿上去就戳了一下,莲儿哭嚎起来,脸上渗出了血。
水溶拧了拧眉毛,喝道:“主子办事的时候,哪有你插手的?真是一点规矩不懂。你主子身子不好,你不跟着劝劝,反而越发仗了胆?就在这儿打起人来,成何体统?”吓得杏儿缩了手,再也不敢上前。莲儿只管跪在一边哭求着。
李侧妃见水溶不让打,还话里有话的说自己不懂规矩,心里不禁怒上了火,想着孩子刚刚没了,还不让自己出出气吗?自己要是咽下这口气,以后府里的那些人还怎么看自己?想到这里,仗着以往水溶宠她,就大声喊着人:“来啊,把这个贱蹄子卖到窑子里去,让千人骑万人压,方消我心头之恨!”
水溶见她失去了理智,断喝一声:“你急什么?这是你现在出气的时候吗?你一个侧妃怎么一点体统都没有,就这么明眉对眼的和一个丫头吵起来了?那些话也是你说的?她一个丫头能兴起什么风浪?”李侧妃被他问得哑口无言,只好讪讪地躺回去了。
水溶继续问着莲儿:“本王知道,你断没有那个胆子。说罢,是谁指使你那么做的?”
莲儿咬紧了嘴唇,心里疾速地思量着:要是自己说出去了,即使能活得一命,这杀害王爷子嗣的罪怕也是难逃。如果不说,自己大不了一死,父母亲和弟弟还有一大笔钱呢。
莲儿的眼风瞥了一下齐庶妃,齐庶妃吓得脸色煞白,手中的帕子差点掉了。水溶早看在了眼里,盯着莲儿不放。
莲儿咬紧牙根说道:“王爷,没人指使奴婢,是奴婢受不了侧妃的折磨,才这么做的。”一语既出,惊了一屋的人。
李侧妃直要杏儿上前打着问她:“到底怎么折磨她了,今儿当着王爷的面都要说清楚。免得背了个虐人的名儿。”
水溶心中也自惊奇,这李侧妃不是把莲儿从清漪园带过来的吗?怎么着,她也该感激才对啊,怎么竟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这其中另有隐情?
水溶面上沉着地问道:“你是这屋里的丫头,李侧妃怎么会折磨你?必是你胡说,想开脱罪名吧?”
莲儿忙磕了个头,回道:“王爷不知,奴婢也是有父母的人,本想在府里好好地伺候主子们,挣些月钱好贴补家里。只是林庶妃进府里后,侧妃夫人就把奴婢和瑾儿拨到清漪园伺候新来的林庶妃。”莲儿说到这儿顿住了。
水溶又问道:“这有什么不好?难道这就是你说的侧妃折磨你吗?”
莲儿抬起头来,看了李侧妃一眼,李侧妃对着水溶哭道:“王爷,妾身在这屋里熬了这么多年,而今您就由着这个贱婢如此胡咬吗?”
水溶也不理她,盯着莲儿道:“说下去。”
莲儿终于鼓足勇气继续回道:“林庶妃是个新来的,夫人就让奴婢们处处刁难她。后来在庶妃生日那天,夫人送了两盆白色杜鹃,暗中嘱咐奴婢引着庶妃送一盆给王妃娘娘。奴婢也不敢问明情由,就照做了。侧妃威胁奴婢,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让人抓了父母和弟弟呢。”说完就跪在那儿呜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