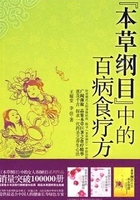“天啊!有自杀倾向,得劝劝,是不是产后抑郁症?这可不能小瞧,很多新妈妈都是刚刚造出一条人命,又弄出一条人命。我有个高中同学,生个孩子哪儿都好,就是三天没见拉屎,一检查是肛门闭锁,肚子里头小肠大肠直肠都好,就肛门那儿多了一层膜,和咱妇产科常见的处女膜闭锁差不多,做个小外科手术就能解决问题。
“结果人言可畏,邻居同事交头接耳,说什么祖上无德之类的才会生孩子没屁眼儿,不仅公公婆婆,连她亲妈都跟着唉声叹气,结果我同学整天以泪洗面,最后抱着孩子跳楼了。”
“别以此类推,你同学那是产后抑郁,车娜这个我觉得不是,她就是焦虑,真正的抑郁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即使是对过去十分感兴趣的东西也一样。你看车娜上了手术台就跟打了半罐子公鸡血似的,她要是抑郁,咱都别活了。你丫别一知半解,连个精神科医生执照都没有,动辄给人家乱扣这种帽子。”
对百舸争流之中不肯落后,又一贯以极度自我、组织性和高效率为骄傲的知识女性小愤青来说,这孩子来的可能真不是时候。进了电梯,我还想开腔,琳琳把示指准确地竖在鼻唇沟和唇中线处,示意我收声。
出了电梯,琳琳说:“你丫以后小心点,私事千万别在电梯里说,想害死我?电梯就是一个暂时封闭的小社会,隔人有耳,还有你的视野范围根本无法达到的四个死角,谁知道是不是躲着默不做声的主任或者专门搬弄是非、听风就是雨的八婆同事。”
“嗯嗯,不说,不说。”我附和着。“除了自己的私事不说,别人的私事也别说,科里的是非更不能说。你可能觉得站在旁边的都是病人和家属,即使有个穿白大衣的也是皮肤科的,和咱妇产科完全不搭嘎,说什么无所谓,可谁知道他是不是咱们科谁谁的亲戚朋友,和掌握我们生杀大权的领导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一边嗯嗯回应着,一边跟琳琳进了病房,心想,这家伙肯定什么时候在电梯里大放厥词吃过亏。这次我也进步了,虽然没瞧见她经历的风雨,也看到了属于自己的彩虹。
我和琳琳一进病房大门,就见护士长脸红脖子粗地站在六人间病房门口,一脸凝重、气恼外加哭笑不得。原来,昨天下午住进来的两个新病人,一个想挨窗子睡,一个想靠门睡,半夜里俩人一商量,擅自抱着枕头被褥就换了床位。这两个病人一个是习惯性流产进来保胎的,一个是胎儿先天愚形大月份引产的,都得吃药,药性却完全不同,保胎的吃黄体酮胶丸,堕胎的吃米非司酮。
早晨,护士按照医嘱,把病人各自的口服药装到标有床号的小药杯里推车发药,走到床边核对病人姓名,才发现病情、病人和药物都不对路。要是没有严格的“三查七对”制度,或者发药时病人不在床边,护士把药杯随手往病人床头桌上那么一放,后果不堪设想。
敢情病人把住医院当住酒店了。怪不得护士长抓狂跳脚,当这种“每个小错儿都可能铸成大祸”的临床一线小头头,真不省心啊!
13
女性最佳的生育数是2~3个
这边护士长刚消气,那边护理员脚步匆匆,推着轮椅跑进病房,只见病人整个瘫软在轮椅上,脑袋歪在一边,旁边的家属一边小跑一边嚷嚷:“快抢救,休克,休克了!”
这不是我昨天收下的不孕症病人吗?这对夫妻结婚六年,前四年挺潇洒,一心要过二人世界连做三次人流,后两年忽然父性母性齐发却造人未果。上上下下一查,女的两边输卵管都积水了,这次住院是等着做宫腔镜和腹腔镜联合检查。我们打算在腹腔镜下将双侧输卵管开窗整形,把牛郎精子和织女卵子之间的天堑变通途。如果手术能够成功分离输卵管伞端的黏连,输卵管内部又没有遭到严重破坏,哪怕一边输卵管能用,她都有机会怀孕;如果不行,也能给病人一个痛快话,让他们彻底放弃自己努力的念头,趁年轻赶紧去做试管婴儿。
本来打算明天手术,谁想到,昨天下午病人突然打喷嚏、流鼻涕、浑身疼,临下班又发起烧来,还不停咳嗽。晚查房时,我们都觉得她的症状像病毒导致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说白了就是感冒。很多病人都这样,马上要做手术了,谁不害怕呀,不光殚精竭虑还日夜忧愁,结果什么问题解决不了,还把自己免疫系统给弄乱套了。正气不足,邪必侵之,人类周围细菌、病毒无处不在,微生物作为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要完成借助哺乳动物传宗接代的使命,它们选择目标时,大多是挑软柿子捏。
她一下子烧到39度,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决定今天给她拍胸片,这才有了刚才的一幕。
我和琳琳还有病房里已经来上班的大夫护士赶紧把病人转移到床上,我摸了她的脉搏,规律、有力,测量血压心率正常,听心肺也没问题,再看病人满身都是汗,病号服都湿透了,她不是休克,是虚脱。
护士迅速抽了血,输上液体,送血样到急诊生化室做紧急化验,低糖低钾是病人晕厥最常见的原因。
家属大喊:“为了今天早上抽血,病人昨天晚上十点以后水米没打牙,我说让她吃点东西再去拍片,护理员说啥不同意,说去晚了排不上队,耽误了她不负责。结果排队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好人都受不了,何况她还发着烧。我说回去吧,护理员愣是不同意,说这是大夫医嘱,必须执行。张大夫你说是人命重要,还是拍片重要?我老婆要是出什么事,我跟你们没完,连你们院长一起告到法院。”
平时出了什么事,都有琳琳帮我解围,这次倒好,她老人家躲在护士站开化验单,也不吱声。她可能是泥菩萨过河,正为自己肚子里那点事闹心呢。
这时病人醒过来了,只是还非常虚弱。大人和小孩生病不一样,很多小孩感冒动不动就烧到39、40度,但是烧一退,照吃照玩,跟没烧过一样。但是对大人来说发烧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骨头关节连着肉一起酸疼不适的感觉难以名状,我有切身感受。
平时采集病史都是一张桌子隔着俩人,我一边问一边奋笔疾书;查房时我两手背在身后,或者插进白大衣兜,要不就是双手抱肩。看到她气若游丝的样子,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安慰她,索性拉起她的手问:“好点了吗?”
她微睁着眼睛浅浅地点了点头。因为临床时间尚短,下一步,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从医疗的角度看,她没休克,生命体征平稳,该抽的血抽了,该输的液体也输了,我该去忙自己的事了。做医生每天都离不开给病人做检查时的身体接触,但那是隔着橡胶手套。此刻拉着病人的手,皮肤实打实的接触,让我的心房发生轻微的颤动,这种感觉很难形容,总之是浑身上下不自在。
没想到,她反倒紧紧握住我的手,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哭着说:“张大夫,我好害怕,你别走。”
两手的赤裸紧握传递了炙热的依赖,一阵阵的滚烫让我不知所措,最终,我还是单方面本能和主动地松开了她的手。
但是我没有走开,我把她床头挂着的毛巾拿到热的水龙头下,拧了几把,给她擦了擦汗,顺手把她前额的刘海往一边整理了一下。我学着我妈给我试体温的模样摸她的额头:“好像不太烧了,别着急,输点液就有精神了,一会儿再给你喝点热水,吃点东西就好了。平时不太发烧吧?刚才你都烧糊涂了。”
她的爱人看她好了,自然消了气。护士已经手脚麻利地帮她量了体温,琳琳帮我做了突发事件的病程记录。病人和家属的好坏虽然没写在脑门上,但医生大多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判断其性格特点,是偏执的、多疑的,还是变态的、狂躁的,差不多都能做到心中有数。这位家属不是无理取闹的人,他只是不懂虚脱和休克不是一回事。我这才想起“交代病情”的事,这是医生应尽的义务。
我说:“刚才的事儿,我给您解释一下。”他连忙摆手说:“不,不,不用解释了,我都眼看着呢,她没事儿就好。我刚才太着急,原谅我大喊大叫的。”“那您……不会到院长那儿告状了吧?”
“告什么呀!我就是心疼老婆,才一时气急的。张大夫,不瞒您说,我爹妈死得早,就老婆一个人疼我,现在因为要给我生孩子让她受这份罪,我能不着急吗?刚才您摸她额头,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是爱发烧,我娘就是这么摸我脑门的,本来烧得头晕脑涨,娘一摸头,再拉到怀里搂一会儿,什么难受劲儿都没了。”
我看到,他的眼中有泪光闪动。
除了怕自己的病人挂掉,医生最怕的事就是被告状和投诉。家属走后,我和护理员聊了几句,希望她工作不要那么教条,病人情况如果不好,应该尽快推回病房,要是半道上出了什么事可如何是好?
没想到她一口的满不在乎:“有什么大不了的,休克我见多了,不是她这样的,好不容易排上队了还没拍上胸片,下午不还是我的事儿吗?”
“别瞎说,小心被护士长听见,你不想干了?”
“怕什么,还不到1000块钱找我这种身强体壮,门诊病房里外门儿清,还懂护理知识的人做苦力,你们协和占大便宜了!我要是一走,你们病房瘫痪一大半,护士长都得抱大腿求我留下。别说我不想干了,护士长早都不想干了,你才来几个月,慢慢就有体会了。”
我是科里最年轻的一年级豆包,她虽然年龄比我小,但是算工龄,她已经是工作很多年的老辣椒了,平时手脚倒是麻利,有点医学知识,还动不动对我们开出的化验单指指点点说三道四,自然是不肯听我的。
她口中仍然念念有词,我本想说服她,却被她说得一愣一愣的。在我也就二十出头的个人世界观里,早已抱定“生是协和的人,死是协和的魂”的坚定信念,并且打算咬定协和不放松,决意要把这牢底坐穿,我还当谁都跟我想的一样呢!
琳琳把我拉到一边说:“走,交班去,理她干吗!这种人注定一辈子做外勤,性格人品决定命运,这道理难道你不懂?别见谁都想拯救,当自己是圣母玛利亚啊?”
哈利路亚,不管怎么着,这事总算过去了。
平了这事,我们都到会议室早交班。
昨天夜班没有特殊情况,在夜班护士和值班医生絮絮叨叨流水账一般的交班中,记忆的脚步再次将我带回童年。
小时候,回到我妈身边以后,我最喜欢两件事,停电和生病。
因为供电不足,家属区经常拉闸限电,我妈点上蜡烛,就着微弱的烛光,在钢板上写蜡纸,再油印后发给学生们做题签。我在一旁没事做,也点上一根小烛头,那天我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连衣裙,手托蜡烛无聊地在地上转圈玩。
我妈抬起头看见我,说:“像个小天使。”我心中一阵激动,我在书上看到过天使,那是个漂亮的小孩,有白色的翅膀,代表圣洁和可爱。那以后,我便夜夜盼着再做她眼里的小天使。谁知厂里有了自己的发电机,我妈再不用忍受昏暗跳动的烛光,我的心却陷入失落。孩童的想法总是幼稚,就像村里发大水,我们坐在高高的屋脊上,甩着小腿,拍着巴掌看顺水而下的破桌子烂椅子,觉得好玩,全然不知灾难的到来和大人脸上的愁苦。小孩子的心里,好像只有自己和自己在意的周围,没有世界。
那时候我一生病就发烧,我妈最常用嘴唇试我的额头,看看还热不热。我爸说摸额头咋不用手?放着体温表不用,有毛病。我妈说成年人的手掌经历太多,早已粗砺不堪,哪儿还感觉得出冷热?生病的孩子总能得到比平时更多的关爱,比别的兄弟更多的照看。我妈温暖的嘴唇贴在我的额头上,身体相互靠近的一刻,我能闻到她身上温热、香甜、略带少许汗味的母亲味道,浑身的难受就好了大半。
我曾熟记每一种体温测量方法,口表、腋表、肛表,也能熟练背出每一种测量方法测得人类体温的范围,还能背出稽留热、间歇热、弛张热、回归热的特点,更知道如何通过特殊热型找出发热背后的真凶。而剑拔弩张的一刻,这一切都没派上用场,我只是用了从母亲那里感受到的一种方式,一条擦汗的温热毛巾,一只放在病人额头上的医生的手。医生的手,不光可以隔着橡胶手套给病人开刀,带着浓浓的消毒水味给病人做身体检查,其实,它也能像妈妈的手,不仅感受病人的体温,更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传递关爱,拉近距离,抚慰焦躁,驱除恐惧。
自己也当妈妈之后,我照着育儿书上的方法,用肘部感知女儿洗澡盆中热水的温度,学着母亲的样子,用嘴唇感受女儿额头的温度,体会那句“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的同时,也不免暗恨我妈当初怎么就那么狠心地把我放下。
放下,可能是因为我妈不懂童年对一个人的重要性。现在,仍然有很多人不懂这一点,或者即使懂,也无可奈何。放下孩子的一刻,自以为放下了沉重的负担,没承想也放逐了孩子的童年,放纵了母爱的逃逸。
我尽可能多地拥抱我的女儿,见缝插针地亲吻她,再难也要把她带在自己身边。我想让她从里到外彻头彻尾地感到安全,有安全感的人就不胆小、不纠结、不缩手缩脚,长大以后,即使脱离妈妈的怀抱,她也能安然面对人间的百态。
为此,我妈总是笑我溺爱孩子。我默默地想,我为什么不溺爱她呀?等她将来走向社会,得有多少人欺负她,得有多少讽刺挖苦尔虞我诈肮脏丑陋等着她呀!我妈说,不吃苦中苦难做人上人,你这样养女儿,将来她就是温室里的花朵,如何出人头地?我默默地想,我为什么非要让她出人头地呀?王朔说,成功不就是多挣几个钱,然后让SB们知道吗?做什么作业,不做!我可不指着你将来成什么,你当我女儿我谢你还来不及呢!你将来就是享受。你是书香门第的小姐,将来太有钱了。我叫你一辈子不为钱工作,只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当然了,这些都是我默默地在想。否则我妈一定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以为自己是谁呀?有本事先成为王朔,起码有名有钱,再学人家怎么养女儿。其实,我就想让她做一个温柔可人的女孩,要多读书,但不要多高的学历,早点结婚,然后,起码生仨孩子。大志问:“为啥是仨?”
“为啥?因为我很久以前看过一篇英文文献,说女人的最佳生育数目是2.4个,这样可以保护子宫内膜,减少子宫内膜癌、乳腺癌还有好几种癌的发病率。”
对于说话总是有理有据的我,大志只有翻白眼的份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