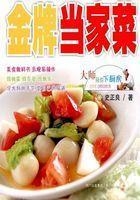出差去了泰国。所谓出差,无非是作为随团记者,跟着一群人免费旅行。曼谷的夜晚,炎热而浮躁,人们坐在敞篷的出租车里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我们去了按摩店,泰国女人黑且瘦,却都劲道十足,在这里倒是学到了两个泰语单词,轻一点是 baobao,重一点是 nana。
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容易记住了。在我身边坚定的吃喝分子中,有两个迷人的姑娘,一个叫包包,一个叫娜娜。如果我想轻一点,我就想到包包;如果想重一点,我就呼唤娜娜。
当我在炎热的曼谷按摩时,不断地呼唤包包和娜娜的时候,这群人正聚集在大观园附近的一家餐厅里,大吃大喝,还不断地给我发短信。据说他们那天又喝大了。
总是要说一些由头。包包是一家杂志的编辑,著名的“神仙姐姐”。我更愿意叫她“包神仙”,偶尔也会叫她“包不住”。这个绰号来源于一次酒局上的玩笑,我送给包包一句诗:“青衫包不住,呼之欲出来。”因为那天她穿着一件青色的上衣。
事实上,包包这个 1972 年出生的资深美女,更多的时候是粉红女郎的色系。每次见面她都是一身粉色装扮,从上衣,到裤子,甚至鞋子。包包有些“琼瑶女郎”的风范,柔情似水又风情万种,漂亮干净,尽管她的孩子都已经上初中了,她羞涩的时候还是青春期的模样,谁也不会想到她早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她之前做过主持、模特,善于插花、摆布家里的陈设,有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气,但是她还写过一本关于美食的书和一本关于家庭装修设计的书,那本关于美食的书名字叫《烟火人间》,总而言之,包包算是“才色双全”。
包包善于神神道道,说《周易》论面相,偶尔扮成一个大仙儿的模样。这个“青春期妈妈”眼睛里总是流露出“这是为什么呢”的神情,偶尔说一句过火的话,脸就迅速泛红,娇羞的模样颇惹人怜爱。她热衷的话题是:办公室八卦、我们的八卦、各种八卦..
娜娜则是重量级的人物,酒风彪悍,话茬猛烈,口吐莲花,典型的北京姑娘,有里有面儿,大开大阖。有一次我们闲来无事做“前生测试”,得出的结论是:她上辈子欠我的。于是这辈子开始偿还,她是我的房东(尽管我不怎么给她房租)、司机(经常吃完晚饭捎我回家)、知心大姐(我遇到无奈且失落的事情,总是朝她倾诉,尽管她也不怎么爱听一个傻大黑粗的结巴男唠叨)和司仪(我结婚时准备叫她当司仪)。总之,她能够胜任所有的角色。
我们一起在各种饭局上厮混,从五星酒店到民间小馆,随叫随到,到之能战,战之能胜,所到之处,无不杯盘狼藉,善于把客场混成主场,把高级馆子吃成自家厨房。
与包包第一次见面是在东方广场的一家餐厅。前些日子经常去那里,那家餐厅已经写着“停业”两字,可见时间之倏忽。她那天是粉色打扮,我以为她比我小,而她以为我要比想象中胖。“听着赵子云的名字,怎么也是个白面小生的样子。”这是后来她跟我说的话。
包包古道热肠,又喜欢一些小资的情调,有些“红楼梦”,还有些村上春树,说话轻轻柔柔,像有鹅毛掏着自己的耳朵。有一次,我们坐在出租车里,她用她娇羞的声音,跟我讨论着,我估计那天的出租车司机师傅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开车。
包包有一次跟我说,她在阳台上养了几只喜鹊。我没有明白的她的意思,经过一番解释,我终于明白。她把柿子放在阳台的窗户外面,有几只喜鹊把柿子吃得很干净,于是她每天都会把几个柿子摆在阳台上,那几只喜鹊每天都会定时来这里吃丰富的柿子大餐,而包包在一旁看着,就像那几只喜鹊真的是她饲养的宠物。
事实上,喜欢养宠物的是娜娜。她养了一条硕大的古典牧羊犬,傻乎乎的长毛遮挡住眼睛,娜娜为其命名“米其林”,偶尔我们一起去郊区游玩,娜娜总是会带上小米。
娜娜也是古道热肠,在饭桌上经典迭出,幽默是她最好的装饰品。2008 年,对于娜娜来说,有点难,离婚,丧母,生病,一塌糊涂,可是每次见娜娜,听到她爽朗的笑声(用一个俗气的比喻:银铃般的笑声),似乎这些磨难从来没有击败过她。
偶尔娜娜在家里准备家宴,我们一起去品尝娜娜的手艺,她会做最传统的春饼,立春的时候一起享用;也会做鸡煲翅这样的高难度大餐。她一个人在厨房,变魔术一样侍弄出一桌好菜。更多的时候,我们在餐桌上聚首,冬天的时候,娜娜也敢穿着轻薄的丝袜出门。我们一起畅饮,偶尔她会做出不醉不归的架势,但是很少见她喝多。有时候我们晚上一起经过平安大道,我就会高声,用拐弯的声音大唱左小祖咒的《平安大道的延伸》——“如果你感到悲伤的话,就不要去平安大道。”
然后大家说笑着远去,丝毫没有悲伤。
2008 年 10 月,我操办自己的婚礼,包包与娜娜都是“婚礼筹委会”一员,经常借着商量婚礼的机会喝酒。
娜娜被钦定为司仪,另外一个男司仪是老罗,这两个人一个姓张,一个姓罗,给我“张罗”婚礼主持不在话下,都是大话喷子,俏皮话就像路边的野花,随便抖落就是满地。可是娜娜终于没能如约主持婚礼,我只知道是她母亲病重,却不知道就在我的婚礼举行的时候,她正在殡仪馆参加她母亲的追悼会。她的母亲病逝于我婚礼的前一天。后来她在博客上贴出她和母亲的大头贴,相似的笑,永远的感怀。后来她说欠我一个婚礼主持,我说,要是有二婚,还叫她操持。事实上,我觉得我欠她的要多一些,至少从感觉上,我欠她一个安慰的拥抱。
有时候,我经常想,这群酒肉朋友算什么呢?其实酒肉朋友最贴心,没有丝毫的利益掺杂其间,仅仅是吃喝玩乐,掏心窝子,互诉衷肠,倾吐着理想与现实,也倾吐着秽物。我们在一起吃饭的频率太高了,甚至一起吃饭比和老婆吃饭的次数都多,以至于成了亲人。2009年春天,我们一起给一家杂志拍摄大片,一个个换上晚礼服出场,感觉那么不真实。换上晚礼服的包包和娜娜,风情万种,都是漂亮姑娘,我总是淡忘了她们的性别,把她们当成哥们儿,在一起说胡话,讲黄段子丝毫不掩饰。有时候我们在高级餐厅吃着正襟危坐的大餐,觉得不爽,一起溜走换一个烧烤的排挡继续吃,或者吃完了再去 KTV 唱歌。娜娜总是唱苏慧伦的歌,包包总是唱《剪爱》,我总是唱着陈升的老歌。
歌声会持续到半夜,饭局也会持续到半夜,久久不散。
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从 2004 年吃到 2009 年,现在聚在一起的频率少了许多,各自有各自的事情。这个城市里不缺乏各种圈子,但是缺乏美好的人。这些人都是美好的人,我们有着美好的饭桌往事。
而今的包包,经常往返于北京和香港,她儿子在香港上学;娜娜有了一条狗和一个幽默的男友,准备年底结婚,在求婚的现场,我们见到娜娜哭了。那似乎也是娜娜柔软的一面,爱情与友情,总是令人沉醉。
夜晚的风一点点吹拂着往事,那么轻,那么重。这 个 城 市 里不缺乏各种圈子,但 是 缺 乏 美 好 的人。这些人都是美好的人,我们有着美好的饭桌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