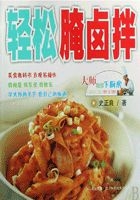前几年,CCTV 商量着做一档美食栏目,找我商量一下策划,于是我给他们提供了一款很 CCTV 的策划,做一个“抄美食的老家”的美食加旅游的栏目,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鲜的,无非是一个吃喝旅行团,去世界各地吃当地最有名最新鲜的美食。后来终于是没有消息了,可能是成本过高,难以有充足的广告支撑。
这个想法实际上来源于蔡澜,他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古风,他说:“最好的人生就是尽量地吃吃喝喝。”
所以他有一个“蔡澜之友”吃喝团,去世界各地吃当地最好的美食,由蔡澜亲自点菜,自然能保证质量,美食在乎“当地”与“当季”,所以唯有这种方法,才能品尝到无上美味。
而事实上,我是个没有出过什么远门的人。尽管吃过不少东西,基本上全是在北京,偶尔出个远门,也是去延庆,怀柔什么的,就算把我打回老家去,也不过是河北霸州,坐 943 路公交车就直达了。
前两年的梦想是去阳澄湖吃一顿大闸蟹,后来就连着去了两次。先是飞到上海,再坐车一个多小时抵达阳澄湖。每次去都是当地的蟹商接待,八月十五前后,刚刚开湖,我们亲自坐着小船捕蟹,阳澄湖的不大的水面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养蟹的围网,叫人看着多少有些心酸:野生的阳澄湖大闸蟹几乎绝迹,其中还有不少是“洗澡蟹”,大闸蟹们的主食也都是玉米做的饲料,它们养尊处优,长至三两左右,就被一一打捞上来,用细绳拴住腿脚,带上阳澄湖特有的防伪标志——一枚戒指,然后被发往各地的超市。
我们往往是在湖边找一家餐厅坐定,前菜是各种当地的美食,有一些水鸟做成的卤菜在其他地方见不到,这种鸟喙很长,名字忘记了,味道尚佳。主菜也不是蟹,而是常见的鸡鸭鱼肉,待到最后,满满一盘清蒸大闸蟹上桌,此时我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然后努把劲,再掀起一把小高潮。蟹美味,但是也如不在座的人美味,一群好朋友胡乱说笑,外面天色渐晚,湖面上略见星星点点的光,加了姜丝的黄酒尚温,蟹黄的滑腻尚在,晚风透过窗子,拂在面颊,略感惬意和爽快。
然后会转路去一趟千岛湖,杭州的南面,驱车的话会路过不少的村镇,黑白的房屋在路边零落。我还记得有一个镇子的名字叫“受降镇”,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名字的来历,也不想去查,留点遗憾也好。盘山的路抵达淳安,海瑞曾经在此为官。千岛湖的鱼头有名,并且经过注册,名为“淳牌有机鱼”,我们跟着渔船下水,在船上吃一顿船工做的鱼头,味道有些寡淡,但是能咂摸出鱼的新鲜。撒网捕鱼也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旅游项目,湖底的鳙鱼都是成群游动,渔船会把所有的鱼群赶到一片水域,巨大的网从下抄起,无数鱼从湖面高高跃起,闪烁着银光。大的有几十斤重,小的也有七八斤沉,有的大鱼跳跃到船只的甲板上,摔得半死,游客们忙着把它们抱起,摆着各种姿势,拍照,留念。
县城里随处可见鱼头的餐馆,旅游景点的地方餐饮大概都是一个样子,没有更好,也没有更坏,都是差不多。我们去了当地最好的一家,吃鱼头煲。鱼头煲奶白色,鲜亮,浓郁,可能是盐放少了,我还是觉得有些淡,或者当地平时口味就是如此。我还是觉得不甘心,寻找到船工,叫他们带着去吃一些稀奇的鱼类,而不单是鳙鱼的鱼头。他们带我在船上吃几种不知名的鱼,有的鱼嘴很长,似乎叫刁子鱼,还有大小不一的银鱼,味道很鲜,但是刺硬,一不小心卡在牙缝里,别扭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湖面上的捕鱼活动还在继续,不过是换了一群游客,看到鱼群纷纷跳跃,他们依然是禁不住地喝彩,拍照。
如此下来,我似乎对美食旅游团失去了些许神秘与兴趣。之前还盼望着去日本的鱼市上吃最新鲜的刺身,或者在秋刀鱼的季节,品尝秋刀鱼。我还惦记过久居法国普罗旺斯的彼得 · 审梅尔,希望和这个老家伙共进午餐;或者去德国的街头去喝一欧元一扎的黑啤。如今,这些东西似乎都不太能提起的我的兴趣。
最好吃的饭永远都是和朋友在一起吃的饭,最好的城市也是有朋友的城市。年初的时候去四川成都,一个晚上,诗人杨黎带我去吃了四个地方,第一顿饭是在玉林的一家馆子,然后去了朋友开的一家酒吧,再接着似乎去吃了一顿夜宵,最后一顿我实在想不起来吃的是什么了。那时候天色已经蒙蒙见亮,我喝了酒,困得要把头扎在桌子上,我们还在吃,还在聊天,有时候什么也不聊,无语也不见尴尬。
后来我又见杨黎,问他那天凌晨我们最后吃的东西是什么。杨黎告诉我是海味面。我觉得那是最好吃的美食,尽管我早就忘了它是什么味道。
我终归是一个容易厌倦的人。抄美食的老家,本来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到现在想起来,也不过了了。每次有朋友从外地回京,总是眉飞色舞地向我介绍那里的美景美食,或者艳遇。我也会蠢蠢欲动,向往那个地方。
有一年秋天,我们去了海边,夜里在海边烧烤,四处无人,黑得寂静,只有我们几个人和一堆火。我觉得无论在哪里,哪怕是在自家的小院,我们一群人在晚上吃烧烤,也还是这个味道。只是没有海浪一波波冲击海岸的声音。
2006 年的 11 月,我一个人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外面滴落着小雨,我跟着当地的女子一起在屋檐下避雨,又一个人跑到 7-11 便利店,买了几瓶啤酒,买了一些零食。
回到酒店,我坐在房间的露台上,看着马尼拉的夜色,自己喝酒。喝四瓶,感觉还是在异乡,喝再多一些,就没有了陌生感,恍惚中,北京饭局上的老友们纷至沓来,他们拍拍我的肩膀,说:“来,走一个。”
我 终 归 是 一个容易厌倦的人。抄美食的老家,本来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到 现 在 想 起来,也不过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