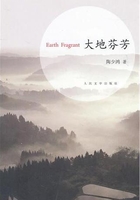谦和初中毕业,因为文革和家庭成分,他回乡务了农。正在上“农中”一年级的芳兰,学校罢课闹革命,她也从堂嫂家回乡务了农。芳兰在堂嫂家住过几年,练就一身好本领。她能看人脸色、眼神行事,会揣测他人的心思。她长的漂亮,心灵手巧,手急眼快,且做一手好的针线活,用飞针走线形容,绝不过分。谦和是“独苗”,娇生惯养。19岁了,已然是大小伙子了,张文华还不舍得让他担一担水,力所能及的活,也舍不得让他干。如此溺爱,后来的事实证明,大错特错!
由于多年的“成分”缠绕,心情压抑,郁闷受气,又没了丈夫,张文华的脾气变得易怒、暴躁、刚烈、敏感、多疑。用如今的理解,也许与更年期有关。少不更事的芳草,一度认为张文华不够温柔,对孩子没有耐性,不够体贴,缺乏母性的柔婉、细腻和温和。
芳兰机灵,她若看到张文华的脸是“阴天”,就格外地乖。她瞥视着张文华的脸色敛桌子、刷碗、扫地、收拾屋子,显得既勤快又利索。而张文华不在身边,芳兰左躲右闪变着法不干活。那些琐碎的事情,自然就归了芳草。芳草自幼讲究条理、爱干净,一见盆朝天、碗朝地,她就看不惯。母亲在,那些活轮不上她。母亲不在,她一会儿也闲不住。
芳草10岁开始做饭。东北的饭,相当好做。每顿饭,就是往又大又深的锅上,贴玉米面、高粱面或谷子面的大饼子。当然得把锅烧热了再贴,不然,大饼子就往锅底溜。玉米面饼子是白色的,很好吃。后来,农村开始种黄玉米,黄玉米比白玉米产量高。黄玉米面饼子是蛋黄色的,虽然好看,但不如白玉米面饼子好吃。高粱面饼子是黑红色的,谷子面饼子是烟黄色的,吃了会大便干燥、拉不出屎。锅里熬上半锅土豆或大白菜,灶里添上柴禾,一会儿工夫,连饭带菜就全熟了。每天早上,母亲、谦和、芳兰去队里干活,芳草早早起床把饭做好等他们“歇气儿”回来吃。她从不敢恋被窝,若时间允许,就吃了早饭上学。若起床晚了,她匆忙把饭做熟,来不及吃,便赶紧背着书包跑出家门。放学回家,芳草还要为家人做晚饭。
芳草对文字非常敏感。有时,一边烧火做饭,一边找来杂七杂八的书囫囵吞枣地读。她深深地被《平原枪声》里马英和郑敬芝的英雄气概所折服。她非常佩服马英的英勇顽强,佩服郑敬芝的聪明机智。看到高兴之处,她会格格格地笑出声儿来。看到英雄被困重围,她会急得落下泪来。芳草非常欣赏《战斗的青春》里许凤和李铁那种同志加友谊的革命热情和他们纯贞、圣洁的革命爱情。看《三国演义》刘备送徐庶回曹营难舍难分的情景时,她竟然被他们恋恋不舍的感情所感染,动情地哭成了泪人儿。《火种》、《烈火金刚》、《新儿女英雄传》、《苦菜花》、《朝阳花》、《迎春花》、《战火中的青春》等书籍,都给了芳草文学和正义的熏陶。她如饥似渴,愈读愈上瘾。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不读书却不行。芳草常常读着读着,锅就被就烧干了。她捧着一本书,还在那儿浑然不觉、孜孜不倦、如痴如醉。等到黑烟滚滚大饼子煳了,把她呛得直咳嗽,她才发现不妙。每每这时,是她最害怕、最胆战心惊的时刻。
尽管张文华经常在芳草耳边说:“你要好好读书,我表哥郭维城就是大学毕业。上了大学,就有出息了。”而张文华心疼粮食,她一见烧煳的大饼子,便不问青红皂白,嘴上骂着:“小臊老婆,小娼妇……”手也随之劈里啪啦在芳草身上一顿乱舞。
谦和自幼娇生惯养,脾气甚大,看见烧煳的大饼子,他摔盆摔碗嗷嗷大叫。芳草吓得抱着头,躲在一旁,像小猫咪似的不敢言声儿。芳兰精明,她不喊不叫。但烧煳的大饼子她绝对不吃,专拣不太煳,或把煳地方抠下来再吃。芳草自知理亏,赶紧把所有大饼子烧煳的地方抠下来自己吃。那又黑又焦的东西吃到嘴里,又干又苦,实在难咽。而她却装做无所谓,坦然下咽。然后,她高高地昂起头,十分不满地瞪着母亲和谦和,面带怒色一声不吭。心想:我没浪费粮食,糊的我也全吃掉了呀?她做着只有她自己才明白的抗议。由于爱读书,而且聚精会神、全神贯注,她曾多次把饭烧煳,也就有了多次皮肉受苦的机会!
张文华让芳兰和芳草一起,用扁担去抬水。芳兰大芳草几岁,二人抬水时,芳兰在后面让芳草的扁担短,她那边的扁担长。芳草个头矮小,一行走,装满水的水桶就往前边溜。向前走一步,水桶就磕芳草的后脚脖。芳草上来倔脾气,便把扁担和水桶往地上一扔,嚷道:“扁担老是你那边的长,我这边的短,敢情不磕你脚脖子你不疼,我不抬了!”嘴噘得老高。本来模样就丑,生起气来,样子更难看。芳兰怒目横眉,拳脚相加。芳草自然不肯示弱,她个头矮小,打不过芳兰,干吃亏不说,芳兰还要到张文华面前,告上个小状:“小臊草竟和我打架,我俩抬水,她不好好抬,小臊草懒。”芳兰在张文华面前撒着娇地嚷嚷。
芳兰聪明、漂亮、心眼多。人,都喜欢聪明漂亮的孩子,张文华偏爱芳兰似乎也合情合理。芳草挨打挨骂,便是命运注定她不幸!她想:我若有个爸爸多好!妈妈打我,爸爸看见不会不管,爸爸肯定会帮我。在学校,别的同学谈到自己爸爸的时候,芳草总是默默地听,一声不吭。小时候芳草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个爸爸。每当想到这些,她就会惴栗不安,就会胡思乱想。王吉洲在世时,曾给芳兰和芳草合扯过一块很好看的花布,张文华给芳兰和芳草各做一件小棉袄,那瓦蓝瓦蓝的底色上面,有一朵一朵粉红色的小花,还有绿绿的叶子,在粉红色小花的四周衬托,非常好看。芳草一看见自己的小花棉袄,便想起自己的父亲。我再也没有爸爸了,我没有爸爸了!想着想着,她就哭了。她渴望有爸爸的心情十分强烈,甚至到了发疯发狂的程度。有时,她一个人跑到父亲的坟前,哭着喊:“爸爸,你快活过来吧,我想你!”
望着离家不远处的火车轨道上飞驰而过的火车,她会大喊:“爸爸,你在火车上吗?你快下来!我是你的女儿!”只要受了委屈,芳草就会独自站在无人的地方,冲着天空大声喊:“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快回家来!”她想念父亲,神思恍惚。在单亲家庭成长的她,自幼深感压抑、自卑,时时被不安全和恐惧感所笼罩。单亲家庭,使芳草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关爱、缺乏呵护,遇到心理问题无人可以倾诉。最终,她形成了自卑、孤傲不群的性格。这,是人性中致命的弱点!
张文华是个刚强的女性。自王吉洲去世,她独自抚养三个孩子,支撑着那个风雨飘摇的家。在苍凉而冷酷的年代,她吃尽人间之苦,一个人默默吞噬人间的悲凉。
每逢春节,年三十开始,张文华便铁板着面孔,样子十分威严。谦和大几岁,大年初一早起,他便首先叩头跪拜母亲,芳兰跟着鞠躬,芳草紧随其后,给母亲行礼。即使这样,他们也不见母亲脸上有丝毫喜色。一到过年,芳草便因此而紧张。她不明白母亲为何不快。每逢佳节,张文华便如此。或许,她思念丈夫?抑或一遇年节,她便哀怨自己苦难的命运、默忧日后潦倒的生活?芳草不理解母亲究竟为何不悦?和别家小孩相反,芳草最怕过节!
张文华很少笑,自记事起,芳草再不敢靠近她。芳草只模模糊糊记得自己幼小的时候和张文华一个被窝睡觉的情景——张文华用手抚摸自己光滑娇嫩的小躯体、小肚子和小腿,像玩弄小动物一样抚弄自己。芳草感觉自己在母亲怀里睡觉真好,真舒服。或许,那是芳草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候。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张文华的脾气变得暴躁。性格也变得刚烈不堪。然而再强悍、再烈性的马,也有温顺的时候,她也具备母性最原始的温柔。有许多次,芳兰躺在被窝似哭似笑、撇着嘴、撒着娇地说:“妈,你得把我的棉袄棉裤烤热,不然,我就不起炕。”张文华便乖乖地把芳兰的棉衣,拿到灶火边去烤。一次,她怕棉衣没烤热,时间烤久了些,竟把棉裤烤煳了。张文华架不住芳兰撒娇,也喜欢芳兰撒娇。这时,芳草也学芳兰的样子,“我也要烤,给我也烤。”而她却忸忸怩怩、嗫嗫嚅嚅,像是在撒娇,娇撒又撒的不自然。因为在芳草心里,母亲给芳兰做事,似乎理所应当。她让母亲做事,总感觉不仗义,也就忸忸怩怩、嗫嗫嚅嚅。自三年大饥荒那年芳草记事起,她就再没和母亲撒过娇。没有了和母亲撒娇的日子,也就没有了幸福!
芳草有个怪毛病,每当她挨了打,抑或白天干活累,夜里准做噩梦。不是被人追,就是被人截,抑或找厕所找不到,千辛万苦找到个厕所还不背人。只好凑凑合合,赶紧蹲那儿便尿。有时尿一半醒了,有时,一泡尿全尿到炕上了。早晨醒来她便傻了眼。张文华打她骂她奚落她是常事。别说别人不原谅她,即使她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挺大的姑娘还尿炕,这让自尊心极强的芳草有说不出的苦恼。一次,张文华诡秘地说:“等年三十夜,你去拜拜三星,拜了三星,就不尿炕了。”
芳草不知那是母亲爱的戏弄,抑或纯粹的戏弄。她十分认真而羞涩地问:“怎么拜呀?”
“你就说,‘拜拜三星儿,拜拜祠儿,可怜可怜尿炕人儿,黑天不得干窝儿睡,早晨起来见不得人儿。”连拜三遍。张文华紧绷的面颊上,芳草隐约见她有憋不住的笑意。年三十夜,外面白雪皑皑、寒风刺骨。芳草跪在僻静处,冲着天空中亮晶晶、距离一样远的三颗星星,虔诚地拜了三星、拜了祠,连拜三遍。张文华得知,她紧闭双唇,掩面而笑。芳草望见母亲不露声色窃笑,她也腼腆而不自然地笑了笑。可惜她的虔诚,并未感动上天,尿炕的毛病照旧。她为母亲戏弄自己感到懊恼,感到自尊心大受伤害。只要她白天挨了打,或者活计太累,夜里准做噩梦,也就成了习惯性尿炕了。为此,芳兰常以“小臊草”相称。芳草恨她恼她,更恨自己不争气。
芳草12岁那年,一天,外面刮着无情的大风沙,刮得人睁不开眼睛,张文华给了芳草7角钱,说:“去,到城里买7角钱的咸盐来。”
芳草非常愿意帮母亲跑腿儿买东西,因为,她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骑驴”。芳草手里攥着7角钱,心里盘算:盐1、3角一斤,我给妈妈买5斤咸盐便能剩下5分钱。等到春节,我的钱包若能存6角钱就好了,就能买一双好看的花袜子穿了。芳草边走,边在心里美滋滋地琢磨。
当地人管大风叫“穷风”。的确,穷风越刮越大,简直要把人刮跑,刮得昏天黑地,对面不见人。藏古县的穷风一刮起来比21世纪北京的“沙尘暴”要厉害八倍。芳草不时地用手捂着被沙子打痛的脸,一会儿顺着风跑,一会儿逆风吃力地前行。穷风无一点规律,一会儿往东刮,一会儿往西刮。芳草的两只手,一会儿挡住这边的脸,一会儿挡住那边的脸。走了好久,也没走出去多远,那可真叫“寸步难行!”不好,芳草忽然发现手里攥着的7角钱不见了。她心里开始咚咚打鼓,赶紧顺来时的路回去找。穷风刮得天昏地暗,她迷路了,急得她直想哭。芳草不知道来时的路是从哪里走过来的,找了半天也未找到那7角钱。钱,早被大风刮跑了,她还在那儿执拗地找啊找、找啊找,钱丢了。她哭丧着脸,怯生生地回家了。家,等待她的是母亲用春天刚刚发芽的柳树条一顿抽打。
“让你把钱丢了,让你把钱丢了!咸盐没买来,钱你倒给丢了,我抽死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丢钱,小臊老婆……”张文华边抽边骂。
那真叫出火!芳草身上,有一道道紫红色的血印。她流着泪左躲右闪不吭声,心想难道我愿意丢钱?你今天就是把我打死,那7角钱我也找不回来了,你爱咋打就咋打呗!芳草颇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意味,那一夜,她又尿炕了。早起,她偷偷把尿湿的被子晾到背人的地方,悄悄上学了。那以后,她对张文华有了怨恨,在心灵深处对抗起那个家,对抗起她认为像后母一样的妈妈。最终,她成了一个冷眼不语的旁支派!家没有温馨,家是令人恐惧、使人厌恶的地狱!走在路上,她心事重重,面带忧伤,紧琐双眉。她忧郁的双眸,无望地眺望天边飘拂的几缕白云,心神恍惚。望着望着,心,就开始激动,开始颤抖。眼泪,就会情不自禁地流淌下来。她不想擦拭,任那咸咸的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淌。
张文华常对芳草发无名火,不知什么时候惹怒了她,她便:“小臊老婆,小娼妇,当年生你,就是多余,看你整天噘着个驴嘴唇,像谁欠你八万吊钱似的……”数落芳草。她骂这些话,从不顾及女儿家的自尊心。大概,过后她也后悔。而脾气一上来,她便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十足的更年期综合症和精神受刺激的表现。
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妈妈生了我,却不喜欢我,我没有圆妈妈要儿子的梦想,我是家里多余的人,是这个世界多余的。我不能上学了,还总惹妈妈生气,芳草想,不如死了算了。死了,就不痛苦了!芳草家房前200米处,有一口深井,半个村子的人,都到这里来担水。井里的水甜丝丝的,非常好喝。这天,她沮丧地来到井边,坐在井沿上往下望,井水又深又清澈。清澈的井水,能清晰地倒映出她的倩影,像一面透明的镜子,清清楚楚地把芳草变成两个人。一个在水晶宫,一个在天空,像一对孪生姐妹,海天之间,遥遥相望。芳草饶有兴致地往井水里投去一粒石子,水晶宫的她,立刻像鱼美人一样在清澈的海水里,自由自在地游啊游。而天空中的她,坐在井沿上,望见水晶宫的一切,非但对里面的鱼美人不感一丝兴趣,还愈看愈眼晕,愈看胆子愈小,一点没有“猴子捞月亮”的神秘感觉,更不敢往井水里跳。
她想我若跳下去淹死,就像爸爸一样永远也不能活了!我若能活几天,死几天,该有多好!像韩老师教我的时候,我就活着。同学喊我“小地主”的时候,我就死掉。妈妈打我骂我时,我就死,对我好时,我就活着,那该多好!她迷迷糊糊,胡思乱想。望着清澈的井水,芳草抑郁的眼神,游离而飘忽。好久好久,她就那样在井沿上坐着,呆呆地想入非非。一会儿,她双手撑地,试探着慢慢、慢慢的想出溜下去;一会儿,又收回双腿坐在井沿上。
无意间,她一抬头,远远的芳草看见张文华站在院子里,正望着自己!突然,一股强烈的逆反心理,使她又产生了活的欲望。
芳草瞥视一眼远处的母亲,心想你看着我要跳井,都不来救我,莫非,你愿意我死掉?哼!我偏不死,你越骂我,我越活着,看你能把我咋样!她站起身,哈下腰,抻了抻裤脚,打扫一下沾在裤脚上的土,拽了拽上衣,垂头丧气、嘟噜着脸,愤愤然地回家了。
寒来暑往,春去冬来。转眼芳草到了十八大九的年龄,她开始欣赏自己了。她愿意看自己的丑模样,也非常喜欢照镜子。可是家里穷,没有镜子。芳兰聪明,她天天到外面的玻璃窗前照“镜子”梳头。换上一件干净衣服,芳兰也到“镜子”前照一照。芳草模仿芳兰的样子,也常到玻璃窗前照“镜子”。虽然,只是玻璃窗,不是镜子,却也大致能照出自己的模样来。令她奇怪,芳兰怎么照也没事,她一照,张文华准瞪眼。张文华瞪眼睛时,脸上没有丝毫笑容,双眸睁得老大老大,白眼球和黑眼珠一动不动,像凝固了似的。她双唇往前翘着纠合在一起,眼光非常锐利。芳草一开始接触母亲锐利的目光,极其恐惧害怕。时间久了,年龄大了,接触那样的目光多了,恐惧感便大大减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