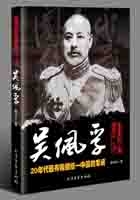芳草倔强而任性,她心想芳兰照镜子你咋不瞪眼?我一照,你就瞪。今天,我就让你瞪个够!她故意站在玻璃窗前,左照、右照、前照、后照,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自己不下一百眼,她不肯离开玻璃窗。一边照自己的丑模样,一边偷眼朝屋里望,她心里在和张文华叫劲,抑或逆反心态反色彩地撒娇。如此叫板,芳草心里有种酸涩的快感。张文华站在屋中,她明白芳草是有意识在与她对抗,便抄起一把笤帚,从屋里冲到外面大吼:“小臊老婆,小娼妇,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将来准是个不安分的人,好人谁像你这么美,啊。我前世造什么孽了,生下你时,我咋不把你掐死,留着你将来准给我丢人现眼!看你美呀浪啊,让你照起来没完,让你照,我让你照!”张文华边吼叫,边挥舞着笤帚像猫捉老鼠、像鹰捉小鸡一样奔向芳草。
芳草失去了理智,胆子也被母亲揍大了。心想怎么着也是挨揍呗,她居然不加思索地嚷道:“张文华,你是个狠心的地主婆!”
张文华听了,更愤怒了。笤帚狠狠地落到芳草身上,芳草不躲不藏硬撑着,像一头倔毛驴似的。张文华极其反感听“地主婆”,就像芳草不愿意听同学喊她“小地主”一样。“让你骂,我让你骂!你一朵花还没开,就这样不孝顺,将来,你一定横生倒养,你记住我今天的话。小臊老婆,小娼妇……”张文华咬牙切齿,笤帚使劲在芳草身上挥舞。她哭得眼睛像水蜜桃。翌日去队里干活,有人问:“芳草,你眼睛怎么肿了?”
“睡觉没枕枕头,控的。”芳草不自然地说,还凄然地笑了笑。
家,对她来说并不温暖。家没有绿洲的温馨;没有港湾的平静;没有平等与自由。芳草有个发小,名叫淑琴。直到芳草出嫁,她俩都是形影不离的好友。虽然如此亲密,好得如同一个人,而芳草的心事,她从不好意思和淑琴说。直到出嫁离开家,芳草从未和淑琴说过一句自己内心的彷徨与痛苦!
王吉洲去世后,经常有好心人劝张文华改嫁,都被张文华婉言谢绝。为此,张文华经常感慨道:“我不能让你们跟着我,去当带俘虏子,让人家瞧不起,给气受……”这,是一种何等的母爱!然而,这样的话听多了,处于青春期不知天高地厚的芳草,也就不像刚听张文华说此话时那样认真了。芳草一本正经地说:“我看,你还不如改嫁。你改嫁了,我们就脱离地主的“光环”被解放了。不但你有了丈夫,我们几个还有了爸爸,岂不是三全其美么?”芳草还说:“你以为你守寡,就能修心养性啊?有话无处说,有委屈无处诉,便竟拿孩子当出气筒……”
芳草真是吃了虎心,喝了豹胆!人虽不大,却专捡逆耳的话说给张文华听,还咬文嚼字装大人。为这话,张文华又狠狠地骂了她一通:“小臊老婆,你还没嫁汉子,竟敢说这样的话,啊!以后你再敢这样说,我撕烂你的嘴。不信,你再说说试试!好女不嫁二夫郎,除了你这个养汉老婆,竟改嫁改嫁的。”张文华虽然如此骂芳草,而她心里,对自己守寡,未必心甘情愿!毕竟,人是感情动物,人的内心都有狂野的一面,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配偶陪伴自己。常言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张文华是被保守思想把她的思维固定了,她不敢有一丝非分之想。“坚守”的语言重复得多了,久而久之,这种思想便成了她真正的思想!
张文华不仅经常数落芳草,还对芳草的思想心存芥蒂。以后的日子,她经常在芳草耳边有意敲锣边——好女不嫁二夫郎。女人,要从一而终。女人和男人“做事”不能主动,女人若主动,男人就认为女人不是好女人。爱美的女人不是好女人,将来必定成娼妇。讲吃讲穿的女人,不是好女人,将来一定是破鞋。女人要自尊自重,不可轻浮,不可水性扬花,不可见异思迁。女人,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张文华是有意识地以一种严格而传统的礼教,教育她的孩子。她还常常感慨地说:“我表哥郭维城就是上了大学,有大学问,才干大事情的。你要是继续上学读书,说不定,将来也会有点什么出息呢!”
如此一系列语言,芳草随时都能听到。耳濡目染,有意无意,芳草便记住了母亲的诸多“不能”“不可”。同时,芳草也明白了母亲是愿意自己继续读书的。而她左右不了社会;左右不了贫穷。因而,命中注定芳草一辈子是文盲。
芳草爱干净,爱美。常常挑剔张文华这不卫生,那不讲究。张文华说:“谁像你这么美,这么浪,这么穷讲究?将来你找的婆家,一定是天底下最埋汰的人家,非板板你这穷讲究的毛病!”后来,此话被张文华言中。张文华的一言一行,芳草从心里抵触。她认为自己的自尊心和人格都被母亲无情地践踏了。她的心,如同沙漠,渴望甘泉的滋润;渴望绿洲的温馨;渴望爱的抚慰。她常常自己琢磨:难道我这么大的姑娘,就不许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难道爱美就是错误?爱美,就是坏女人?天下爱美的女孩,难道都是“破鞋”?执拗而逆反的心理促使,张文华愈对她存有芥蒂,她愈偷偷对着镜子照,偶尔她也心存秘密的罪恶感!偶尔,她觉得自己光明磊落得不得了。张文华愈反对她照镜子,她愈对着镜子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表面,她很自信。内心,她很自卑。芳草出嫁后,才慢慢悟出一个道理:那是母亲在用一种十分正统,甚至,有些变态的方式,在教育她的孩子要做一个本本分分、严守妇道的女人!在21世纪,这种教育观念,显得多么过时,多么落后,多么循规蹈矩,多么缺少温情、缺少爱!而这种观念,有形无形,影响着芳草后来的生活。
十年动乱刚开始,想来使人啼笑皆非。那社会、那人,都像患了病似的。一日,张文华进城办事。刚进城,忽然碰上一群臂带红袖标的红卫兵在那儿吵吵嚷嚷。四周,有许多围观的人。张文华很好奇,她也凑上前,想看个究竟。不看则罢,一看,把她的魂差点吓飞。有几个红卫兵,正拽着一个正拼命挣扎的姑娘,强行咯噔一剪子下去,剪掉了姑娘的长辫子,说只准梳“5号头”或梳两个犄角辫,这是革命,否则,是反革命。一转眼,一群红卫兵又把一个老太太的发纂儿给剪了下来,嘴里还振振有辞:“以后,你不准梳纂儿了,听见没有?这是忠于毛主席,破四旧,立四新,知道不?”
“是,是是是,知道知道,以后我不梳纂了,不梳了,不梳了。”老太太恐慌的脸上堆着僵硬的笑,她咧着嘴连连点头答应。心里,却非常不满。心说我梳纂和忠不忠于毛主席有啥关联?我都梳20多年纂了,难道,这些年我没忠于毛主席?老太太惊慌失色,边走边不时地回头张望,神情紧张而惶惑,她像做了违法的事一样!
非常时期的非常行为,封闭社会的封闭式歪理,把人们搞得既疯狂又紧张;既愚昧,又偏激;既神魂颠倒,又荒谬无常。张文华躲在人群外,目睹这一切,把她吓得魂飞魄散,想办的事情也没办,便贼眉鼠眼一路小跑回家了。而张文华没直接回家,她径直跑到妇女队长住所。新上任的妇女队长对地主成分的张文华还算客气。张文华一进门,便慌慌张张地说:“凤梅呀,你快点,快把大娘的纂剪了吧,不然,这叫不忠于毛主席!你是知道的,大娘对毛主席可是顶礼膜拜,一直从心里忠于他老人家呀!凤梅,我的好侄女,你可要给大娘作证,啊!”
“大娘你剪纂就剪纂呗,干啥这样慌慌张张?我也没说你不终于毛主席呀?”妇女队长姚凤梅愣愣怔怔地望着张文华说。
“哎!你可不知道啊,刚才我在城里,那帮红卫兵可把大娘给吓坏了。”张文华心有余悸道:“凤梅呀,你没看见,你是不知道的!”
发纂谁都能剪,张文华偏跑到妇女队长家,让姚凤梅给剪,这不能不说张文华那根敏感的神经,用心之良苦。张文华拿着被剪掉的一缕长发,沿着羊肠小道,深一脚、浅一脚,慌促忧郁、百思不解地回家了。
芳草把那缕长发,偷偷卖了6分钱,存进自己的口袋里。为此,她兴奋了好几天。
一天,张文华突然问:“芳草,你看没看见我剪掉的那缕头发?”
芳草摇头说:“我,我没,我没看见啊。”
梳了多年的发纂,她想留个念兴、还是别的什么?母亲为什么找她那缕头发?芳草不明白母亲的心。自记事起,芳草眼前的母亲,脑后一直梳着个发纂,像宋庆龄似的。两小时前,张文华还是原来的形象!突然她变成了《红色娘子军》里“南霸天”的坏蛋形象。芳草心中对张文华有说不出的厌恶!她热爱“吴琼花”,讨厌“南霸天”。自那以后,芳草更讨厌张文华了。她甚至多少天,都不和张文华叫妈。
饭前,张文华冲着毛主席画像,第一个张罗唱《社会主义好》。饭后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口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芳草斜眼瞪着张文华,躲在她身后,看着自己像神经病一样的母亲的一举一动。张文华口袋里,天天掖着毛主席语录本,路上遇见熟人,她赶紧举起语录本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吃饭了么?”
“对方赶紧道:“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我还没吃呢。”
人们都像中了邪似的,神经兮兮地说些前言不搭后语、风马牛不相及的寒暄话。无论白天黑夜,只要毛主席说了一句话,生产队便聚集贫下中农,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口喊:“最高指示,坚决照办,永远执行……”听到打鼓敲锣声,张文华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地贴在玻璃窗前,往外张望。嘴里嘟嘟哝哝,不知她叨叨些什么话。张文华期盼队里有一天能叫上她一起去街上游行,而她全然忘了,那样的游行是贫下中农的集会。她是地主、右派家属,根本没她什么事!
由于文革、由于地主、由于右派、由于守寡和传统礼教,张文华的性格愈来愈扭曲!而骨子里,她是善良的。
芳彤14岁去了天津,读完中学高考落榜。便在天津制药厂就业了。1963年“四清”,她还乡了。说是城市里动员娘家是农村户口的子女还乡务农,到农村接受锻炼,单位许诺:锻炼3年允许返城。方彤23岁,刚刚结婚并有了身孕。芳彤的丈夫徐立本,原籍山东,17岁考入大连技工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方彤的单位。二人婚后不久,便开始了牛郎织女式的生活。方彤圆脸型、大眼睛、双眼皮,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鼻梁虽有几个雀斑,却也掩盖不住她的美丽。3年困难时期,城市每人每月有26斤商品粮,但农副产品紧缺,芳彤三天两头给家里写信要这要那。农村生活比城市艰难,她不晓得,也从不思考。芳彤写回家的信,都是如何如何艰难困苦,怎样怎样没有钱花,没有衣穿。张文华千般惦记、万般挂念这个远在异地的大女儿,想尽办法给以资助。她用自己当少奶奶时的一件米色卡其布旗袍,改成一件风衣给芳彤寄了去。芳彤不喜欢,变卖8元钱挥霍掉,之后又来信要衣服。张文华义愤填膺:“大臊老婆,大娼妇,就知道自己合适,不管家人死活!”
方彤下放到农村不会干农活,她出尽了洋相。铲玉米苗她把草留下,把苗产掉。拔谷草,她把草留下,把谷子拔掉。自方彤回到老家,芳草心里格外高兴。因为她与芳兰格格不入,正好又来了一个姐姐,这让芳草心里美滋滋的。方彤干农活不如农村妇女泼辣麻利,常常被别人远远的拉在后面。芳草挨着方彤地垄,一边干自己那份活,一边帮芳彤干,一人干一个半人的活,经常累得四肢乏力,满头大汗。
芳草积攒了8元钱。方彤得知,花言巧语哄到手,给自己买了雪花膏和万紫千红香脂。方彤回天津探亲,她把芳草用自己攒钱买的一条花枕巾,偷偷塞进自己旅行包。芳草想一件漂亮毛衣想了很久,她攒了钱让方彤在城市里帮助买毛线。毛线方彤没给买,钱却肉包子打狗了。村子里的女人,托方彤买一些小地方买不到的商品,方彤先挪别人的钱为自己所用,然后好久好久,才把东西买了给人邮寄过来。成长在大城市的方彤以自我为中心,花钱大手大脚、自私自利,无论是谁的钱,她都敢花。芳草内心十分不解,她很彷徨,姐姐怎么这样?
光阴似流水,转眼,芳兰23岁了,她定好了出嫁的日期。
平日,芳兰爱在张文华面前奉迎卖乖,害得芳草总挨骂,芳草和芳兰的感情一直疙疙瘩瘩。在地里干活,芳兰若落在后面,芳草也会上前帮忙,而芳草内心保存着一份嫉恨。然而,听说芳兰要出嫁,芳草心底那块无人窥视的海面泛起滚滚眷恋的波澜,把她推进难以割舍的感情旋涡,使她陷入难舍难分的痛苦情感之中。芳草曾无数次幻想:哥哥姐姐都比我大,我是家中老么,他们应该都对我好!芳草总想在家中找个知音。而事与愿违,她却找不到。得知芳兰结婚要走,芳草反而觉得是自己对姐姐不够好。她心里,产生了无限的自责和不舍。那天,芳草亲自把芳兰和即将成为她二姐夫的王子安送到汽车上,他二人去沈阳旅行结婚了。当载着新婚伉俪的汽车开出车站的一刹那,芳草的泪水,像决了堤的洪水喷涌而出。
芳兰和子安的新家距离芳草家有一段路程。子安是大专文化,父母是知识分子。儿子找了个农村媳妇,子安的父母持反对态度。因而二人结婚便完全自费。新婚的日子,二人缺这少那,这更增加了芳草同情芳兰的心。
3年大饥荒早已过去,而农村直到改革开放,才真正不缺粮食吃。每到秋季,粮食成熟了,贫下中农仨一群、俩一伙结伴去生产队地里偷粮食。上级领导下来人挨家挨户搜查,大部分贫下中农、贫协主席、妇女队长、出纳员、计工员、会计,队里的骨干家庭都被搜出偷窃来的粮食。噢!原来,他们有猫儿腻!芳草恍然大悟:难怪人家不缺粮食,我家却年年粮食不够吃!芳草开始玩世不恭,开始对社会现象不满。
芳兰怀孕了。她和子安的粮食虽然将就够吃,却手头拮据不舍得买菜。芳草心想我何不学学那些贫下中农,去偷。对,我也去偷,豁出去了。晚上,芳草去队里一次次偷来大白菜给芳兰送去,以缓解芳兰暂时窘境。几棵白菜焉能解决问题?芳草却固执地认为,一定能解决问题,有菜,就比没菜强。尽管,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白菜。芳兰被感动了,经常特意用子安供应的白面,做上半盆疙瘩汤让芳草吃。芳草吃了白面疙瘩汤,心里暖融融的,觉得这就是亲情,亲情就是这样子!一对冤家姐妹,感情逐渐缓解,逐渐有了理解和沟通。随着时光的流逝,不愉快的往事在芳草心中被慢慢淡忘。她以为大姐二姐,都是自己的姐姐,是和自己连筋、连血的亲人,自己没有理由和她们不好!在这个喧嚣纷繁的世界,血总是浓于水,亲情是最可靠、最宝贵、最圣洁的感情。
她哪里晓得,人生所有的情,都会时而淡薄、时而疏离,万事都在千变万化。永远的亲情,是芳草一生所追逐、所渴望、所望眼欲穿、望尘莫及之物!若干年后,她曾哀叹:亲情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