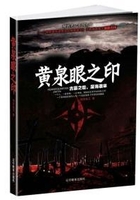芳草站在那儿,两手捂住右肩膀上露着的肉,颤抖着声音、吭吭哧哧、支支吾吾地说:“我妈说,让我到这来,问问您家里有钱没有。”
“有钱没有”芳草说的声音又轻又小,连她自己都没听清自己说的话。小辣椒怒不可遏,她手指着芳草的鼻子说:“有什么?有钱是不是?告诉你,没有!有钱也不给你们剥削人的大恶霸地主!你们这房子,是剥削来的,你知道不知道?你还敢觍着脸到我家来要房钱!你家老地主不来,倒让你这个小地主来了,谁来也不行。凭什么你们家有房子,我们家没有?啊!告诉你,以后,你再敢到我这儿提房钱,我就打折你的腿。你给我滚,滚,滚!”赵一冰冲着芳草,大声地喊。
在芳草听来,小辣椒的喊声,像狼嚎,她哭着跑出小辣椒家。学生和老师,本来就是孩子面对大人。下属,面对上司。又以这样的“乞讨”形象,这样的“地主”身份,遭到如此一番训斥,芳草那颗稚嫩、脆弱、无助的小小心灵,深深地受到了伤害和无情的恐吓。她,迎着飕飕的风,让苦涩的泪水,无声而尽情地往下流淌。芳草恍恍惚惚、步履维艰地往前走,耳边回旋着“剥削人的大恶霸地主,滚!滚!”
在学校,芳草被叫成“小地主”。而今,地主的前面又添了“大恶霸”的词汇。她搞不懂,为什么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却不能住?为什么不是赵老师的房子,她却住得心安理得、理直气壮?!芳草心中开始有了恨,却不知究竟恨谁。
也许,她恨自己的家庭?恨那个生她养她的“地主”家庭!我为什么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为什么?芳草想:风儿啊,你把我带走吧,把我带到天边,把我带到无人的地方去吧!我不要在地主家庭里生活,我不要。只要脱离这个家庭,我去哪儿都行!一路上,芳草飘飘忽忽,像做梦似的。不知不觉间,走到回家必经的铁道旁。她望着停在铁轨上从大庆运过来的、载满油罐和从大兴安岭运过来的、装满木材的火车,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在芳草心中,油然而生:死!她生命中第一次想到“死”这个字眼。对,我要死,我不要活,我要像爸爸一样,去“土包”里一个人呆着。
我要离开这个罪恶的地主家庭!离开它,是它让我倍受欺辱;是它让我濒临辍学;是它让我在同学面前难堪、自卑、抬不起头!
芳草年龄虽小,而她的心,却与她的年龄,不成正比。她平静地躺在了铁轨上,眼里没了泪,心中只有恨。芳草上学长年钻火车,对火车、铁轨并不陌生,也不恐惧。她闭上了眼睛,只等那痛快的时刻快快来临。不知过了多久,芳草听见有个男人粗声粗气地嚷嚷:“喂,这是谁家的姑娘,喂喂!”一只大手扒拉一下芳草的脚,说:“姑娘,姑娘,你咋地了,你咋躺在铁轨上了?啊,这多危险!这趟车快到钟点了,一到钟点,火车就开了。火车一开,你就没命了呀!”
芳草未吭声,也未动。她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那男人用力一拽,把她从铁轨上拖了出来。芳草望了一眼身穿蓝色铁路服,头戴蓝色硬壳帽的铁路工人,他手中握着一红一绿两把小旗。不知为什么,芳草哭了,好像见到了亲人。
“姑娘,你咋地了?你这是为啥呀?”穿铁路服的人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不解地问。一股酸涩的味道,从芳草胸中泛起。她嘴唇慢慢蠕动一下,却什么也没说。她用一种异样、彷徨无助的眼神望了一眼那男人,默默的走了。没走多远,她心事重重地回头望了一眼拿小旗的铁路工人,那人正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望着芳草。
回到家,张文华急切地问:“房钱要来了吗?”
芳草眼里喷着怒火,狠很地瞪了一眼在一旁用期待目光望着她的张文华,一句话也没说。
“我问你话呢?你咋不吱声儿,你没听见呀!”张文华望着芳草倔倔的样子,生气地问道。
芳草如愤怒的火山,终于爆发了:“你为啥不去要房钱?为啥让我去要?因为你是地主婆是不是?你是地主婆子——”她歇斯底里地嚷:“你为啥和地主结婚?为啥不和贫下中农结婚?你不和地主结婚,我就不是地主了——,我就是贫下中农了——”她边哭边喊,像个疯子,像个混蛋。或许,当初她就是个混蛋,那么不理解自己的母亲。芳草完全丧失了理智,胸中充斥着无边的恨。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张文华在生产队并不好过——右派家属、地主、寡妇、外来户。队里脏活、累活都少不了让她干。贫下中农干好活、俏活,她却没有那个资格。生产队晚上经常给地主、富农开会,讲一些让人精神受刺激的话,张文华整天大气都不敢出。此刻,张文华听见自己的亲生女儿如此辱骂自己,她也怒了、疯了。她手持烧火棍,劈头盖脸便朝芳草打来。张文华越打越气,越气越打。芳草执拗地挨着打,不哭也不动,咬紧憎恨的牙齿,任凭烧火棍在她身上飞舞。
打累了,烧火棍被张文华打折了,终于,张文华住手了。再看芳草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红一块肿一块,像一幅五彩图。张文华开始骂,开始哭。她把一肚子委屈,都打了出来,骂了出来,哭了出来!
那个不讲道理的赵一冰找到居委会,向居委会添油加醋地鼓动一番。居委会主任姓李,人称“李大包”。李大包额上长了个像鸡蛋黄大小的肉包,此人是个极左的厉害婆子,专门会整人。因而,人送绰号“李大包”,意蕴坏包。王吉洲原本不是右派、20世纪50年代末期,硬是那个居委会主任李大包给扣上个“右派”的帽子,还把芳草家的满族改成了汉族!不知赵一冰怎样的一番慷慨陈词,没多久,芳草家土改后国家允许保留的3间住房,便无条件地被没收了。从此以后,芳草家没了产权房,也没有了那1.3元的房租。事实上,从被遣送到农村,芳草家就没收回几元钱的房租。因为,无论何方仙圣租房,一开始给两回租金,知道芳草家是地主成分后,便再也不给租金了。
有点“房租”,就有一点点期盼。房子被没收了,生活中仅有的一点点期盼,也没有了!解放以后,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不好的人,随时都要受人歧视。不像改革开放后,谁有本事谁发财。谁发财,谁是英雄。谁发财,谁是好汉。谁受穷,谁是懦夫。谁受穷,谁是能力不够。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路神仙,各显神通。没有谁富有谁就是“地主”,谁就要受到歧视。谁穷谁就是“贫农”,谁就无上光荣那一谬说!至此,芳草家真真正正成了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吃了上顿没下顿、衣衫褴褛的“恶霸地主”了!
在学校,同学给以白眼,老师给以白眼,那位赵老师一见到芳草就瞪眼,还煽动性地和同学们说:“要和地主、富农划清界限”鼓动同学孤立芳草!同学都是小孩子,自然听老师的话。芳草小小年纪,每天都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芳草睁着迷茫的眼睛,望着迷蒙的世界。
她想起那首不知唱了多少遍的歌,孤独的她便自己在心里默默地唱: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
芳草最感兴趣的,是音乐老师教的那些美妙动听的歌曲——《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前……”
还有那首脍炙人口的——《让我们荡起双桨》: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
那些美而好听的歌曲,那些激励人上进、感召人灵魂的歌词,都深深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少年时代的芳草。从那些歌词里,她学做人,做一个好人!随着文革的到来,她又学会了许多新歌: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像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翻身农奴的心儿照亮/……”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在这样的教育下,芳草充满了对共产党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同时她对地主、资本家无限仇视,尽管自己也是“地主”。无论学校让填什么表格,芳草都在“社会关系”或“政治面貌”一栏中,工工整整地写上“舅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芳草和舅舅只见过一面,甚至,都谈不上有这样的社会关系,而她还是乐此不疲地把“党员”填到表格里。以此想表白什么,她自己也不清楚。填表格时,她无论如何不爱填“地主”,她一见“地主”二字就神经过敏,就无地自容!
芳草记忆中最深刻的,是那次音乐老师又教了一首新歌,新歌的名字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歌词里有这样的话:
……那时侯/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上/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
冬天的风雪/像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裳/她去给地主/缝一件虎皮长袄/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
那节音乐课,课堂纪律出奇地差,每唱几句,同学们便回头回脑偷眼看无辜的芳草。每当大家唱到“地主”,芳草的嘴虽然张着,而“地主”二字并未从她嗓子眼清清楚楚地吐出来。她只是含糊不清地把那句台词哼哼过去。芳草心里复杂极了,既恨那个狠心的地主让那位“妈妈”给缝虎皮长袄,又想到自己的母亲似乎就是那个可恨的地主。唱着唱着,根据同学的眼神,觉得自己也是那个狠心的地主。过会儿,又默默地憎恨同学们投过来的、使她恐惧不安的目光。学那首新歌的时候,芳草的心痛苦而矛盾、复杂而充满怨恨。究竟恨什么、恨谁,她不清楚。课间,同学们哼唱那首歌,芳草却躲得老远。甚至,她敏感的神经还无限地怀疑同学是有意识在自己面前唱那首她不爱听、听了就感到痉挛的新歌。大概从那时候起,芳草的性格中有了“多疑”这个字眼。无论如何,这学,芳草上得异常艰难!刚刚上小学五年级,如花朵一样的年纪,芳草的性格发生了质的变化!她变得孤僻、自卑、自暴自弃、玩世不恭、感情脆弱,喜欢独自流泪,和谁她都不爱讲话,俨然是个哑巴。
“时代”使一棵蓓蕾扭曲、变形、枯萎了,无奈,芳草辍学了!她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前途是什么。芳草只有13岁,还不懂得什么叫未来。“文革”第二年,豆蔻年华的芳草,参加了农业劳动。由一个少女,变成了一个农民。
世上有多种多样的苦差事,其中就有农民种地这一种。单调而重复的动作从1秒钟到60秒钟,从1分钟到60分钟,从1小时到10小时,甚至到12个小时、14个小时太阳下山为止,你始终在做同样一个动作。可以说,那不是自由体操式轻松的动作。而是你的心脏、你的肺腑、你的血脉、你的筋和皮肉,通通扒出来,而后四散开裂,刀耕火种般原始式的劳作!一个13岁的女孩,从那时候起,芳草便和大男人们一起,开始了这种原始性的劳作。经常有人说“知青”下乡时如何如何艰难,怎样怎样受苦。其实,若与当地或天下所有的农民一辈子不息的劳作相比,“知青”那点“苦”只能说是锻炼,或说是体验。
到17、18岁,芳草已是队里出名的好劳动力了。她和大男人们一起,到附近有副业关系的玻璃厂,用大长铁锨装卸火车,在固定时间内,装卸30吨或50吨煤、火碱、沙子、石头,芳草从未落后过。她不甘人后、不输于人。割高粱、割玉米、割谷子、割大豆。播种、拉犁、扬场、脱粒,她样样干在前头。春播、夏锄、秋割一切农活,在劳动过程中,芳草总爱和男人们比个高低上下,遥遥领先于别人,是她最开心、最惬意的事情。芳草用全部的身心、超能量的劳动,释放心中的一切不满、郁闷和压抑。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地主,右派”带给芳草无尽的惆怅;无尽的自卑;无尽的屈辱。在那特殊的年代,在不符合她身份的“出身”的羁绊下,芳草骨子里狂放不羁、争强好胜、藐视一切的性格,得到了强有力的压制。同时在这种压制下,更加深加固、更坚定了她的性格——被扭曲了的坚毅,孤傲,不屈的性格。
成长的道路,虽然坎坷不平,而她,还是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她的心中充满不平,充满希冀,充满幻想,充满渴望。
她期待着美好生活的到来!
家庭·年代
芳草出生时,正是国家轰轰烈烈搞第一个5年计划时期。国家百废待兴,励精图治,人民大众祈望太平幸福,祈望安居乐业。百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万众一心,齐心协力,到处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热火朝天建设美好家园的繁忙景象。
建国初期,在人口上,国家决策者还不想控制人口的增长。因为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中国地大物博,有人似乎就有一切。生育问题,并未列入国家计划范畴。因而,才有了芳草这个后来被称为“多余儿”的人。
张文华生芳草已是第7胎,前面曾生了5个女孩、一个男孩。其中二丫、三丫和四丫生下未活多久,便相继夭亡。5个女孩,最后只剩下两个。唯一的一个男孩生下来让全家人伤透了脑筋,他7天不曾睁眼,也不曾哭一声,只少量吸一点奶,微微地喘着气,以此证明他还活着。等到7天头上,他才慢慢睁开双眼并有了哭声。一般情况,人们都讨厌孩子哭。孩子一哭,大人就焦灼不安。然而,这个男孩出生时,全家人极力盼望这个奇怪的孩子能哭一声。那天,他终于啼哭了起来,全家人欣喜若狂,一家人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他就是谦和。大凡孩子的名字,都与家长的愿望,紧密相连。而“谦和”二字,与后来谦和本人的性格,却大相径庭。千顷地,一棵苗,王吉洲原本就是独苗,到谦和这儿,第5胎才生这么个小子。父母自然拿他当心肝的心肝、宝贝的宝贝。脑袋顶着,怕掉;嘴里含着,怕化。像天上掉下了活神仙,地上长出了土地爷一样宝贵。
谦和下面,张文华及全家人盼望再生个男孩,好给谦和作伴。而事与愿违,却又生了个女孩。女孩就女孩吧,前面死了仨,迄今为止这算是第二个女孩。况且此女长的细皮嫩肉、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粉红唇瓣,全家人笑逐颜开,喜不自禁。她就是芳兰。
尽管国家不提倡计划生育,张文华也不想多生了。因为,多生育孩子对家庭、对自己总不是好事。而没有避孕措施,张文华又第7次怀了身孕。既来之,则生之呗。全家人,又盼星星、盼月亮,祈望再生个男孩。张文华找算命先生卜卦,卜卦先生摇晃着没有多少头发的半秃脑袋,不伦不类地之乎者也道:“孕之者,乃男婴也。此婴,不凡也。切记卧床养息乎,谨行慢走乎。”全家人乐不拢嘴,坚信张文华又怀上了男婴。然而天公偏偏不做美,这盼来的第7胎,又是个女婴,且奇丑无比。她小鼻子、小眼睛、头发稀疏,无一点惊人之处。取名“多余儿”。因其白白胖胖,又名“丑肥”。她就是芳草。若解放初期提倡计划生育,这个世界,原本不会有芳草这个人!生命,真是偶然,却也是必然!张文华年过四旬,最后这个女孩,着实扫了她的兴。张文华为此,不知痛哭了多少回。这多余的女婴,光丑也就罢了,可偏偏经过“大饥荒”、“文革”,加上单亲家庭、地主成分、右派子女,她的性格也变得难以琢磨。她动不动就生气,整天噘着上唇微微有些向外鼓的嘴巴,见什么都不顺眼。和谁她也不爱讲话,又倔、又拧、又孤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