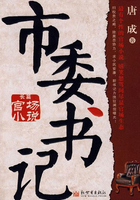因为担心把咖啡洒在地毯上,杜洛瓦一口将它喝光,然后开始考虑该用什么方法去接近新任上司的太太并和她搭上话。
正在这时,他突然看见瓦尔特夫人已经喝完手中的咖啡,因为离桌子比较远,一时不知道该把杯子放哪儿。他赶紧走上前,说道:
“让我来吧,夫人。”
“谢谢,先生。”
杜洛瓦放好杯子后,又走回来:
“夫人,您知道吗,在沙漠的那两年,《法兰西生活报》曾经陪伴我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这是我们在法国之外,惟一能够看到的报纸。它既有文学性,又有思想性,不像其他刊物那么单调。我们可以在报纸上了解一切信息。”
瓦尔特夫人微微一笑,目光中透露出友好的神情,一本正经地说道:
“为了让这份报纸符合时代的需求,瓦尔特先生的确花了不少功夫。”
接着,他们开始聊了起来。虽然彼此的话题未免有些简单平淡,但杜洛瓦的嗓音十分动听,目光炯炯有神,两撇小胡子更是给他增添了几分魅力。这两撇漂亮的胡子分布在嘴唇两侧,天然拳曲,金黄中带点红色;末梢微微上翘,颜色稍浅。
接着,他们谈到了巴黎及其近郊,谈到了塞纳河沿岸的风景和城市,谈到了夏天的娱乐等等。总之都是那些可以整天谈论而又不费神的轻松话题。
这时,诺贝尔·德·瓦伦先生端着一杯饮料朝他们走过来,杜洛瓦立刻知趣地走开了。刚和弗雷斯蒂埃夫人聊完天的德·玛莱尔夫人叫住他,突然问道:
“这么说,先生,您是真的想试试记者这一行喽?”
杜洛瓦向玛莱尔夫人大致谈了谈自己的计划,然后和她聊起刚才和瓦尔特夫人聊过的话题。因为对这些话题已经十分熟悉,他显得从容自若,同时加入了许多刚刚听来的趣闻。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德·玛莱尔夫人,好像这样可以为他的谈话增加一些深刻的含义。
德·玛莱尔夫人也像那些自命不凡并急于表现其风趣幽默的女人那样,滔滔不绝地对他讲述旅行时遇到的趣事。她态度亲密,一只手搭在他的手臂上,压低嗓门,好像在和他说知心话,但实际上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面对着这位如此关心自己的夫人,杜洛瓦不免心神激荡,他恨不得马上对她表示自己的忠心,随时保护她,并向她展示自己的才华。就这样,杜洛瓦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再也无心听她讲话。
这时,德·玛莱尔夫人突然喊了一声:“珞林娜。”
小女孩听到母亲在叫她,立刻跑了过来。
“坐过来,亲爱的,站在窗口容易着凉。”
杜洛瓦突然想到了一个疯狂的念头,他很想亲吻一下小姑娘,好像这个吻可以传到她母亲那里。
他用一种长辈的口吻,亲切地问道:
“小姐,能让我亲一下吗?”
小姑娘惊讶地抬起头来看着他。德·玛莱尔夫人笑着说道:“你可以这样回答:荣幸之至,先生,但是只在今晚,下不为例。”
杜洛瓦马上坐下来,抱起珞林娜,将她放在膝盖上,然后在小姑娘波浪形的秀发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小女孩的母亲惊讶地说道:
“天啊,她居然没有躲闪,真让人震惊。要知道,她平时只允许女人抱她。杜洛瓦先生,您真是魅力无穷。”
杜洛瓦面红耳赤,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只是轻轻地摇晃着坐在腿上的小姑娘。
弗雷斯蒂埃夫人朝他们走过来,发出一声惊叹:
“天啊,珞林娜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乖巧?真是罕见!”
雅克·里瓦尔这时也走过来,嘴里叼着一支雪茄。杜洛瓦起身准备告辞,生怕因为一时疏忽讲错话,而毁掉刚刚开始的美好前程。
他欠了欠身,轻轻握住女士们伸过来的纤纤细手,然后使劲地摇了摇男士们的手。在他看来,雅克·里瓦尔的手,皮肤干燥,但热乎乎的,他紧紧握住杜洛瓦的手以示友好;诺贝尔·德·瓦伦的手又湿又凉,只是轻轻地碰了碰他的手指便缩回去了;瓦尔特老头的手很冷,没有力气,也没有任何表示;而弗雷斯蒂埃的手很厚,非常温暖。他低声对杜洛瓦说道:
“明天下午三点钟,别忘了。”
“放心,我不会忘的。”
杜洛瓦走到楼梯前,真想跑下楼去。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让他感到欣喜若狂。他每两级台阶化作一步,往楼下冲去。走到三楼的时候,他突然从镜中看到一位行色匆匆、蹦蹦跳跳的先生迎面而来,他立即停下来,仿佛自己的冒失行为被别人当场捉住似的。
过了一会儿,他久久地盯着对面的镜子,为自己已经成为一名风度翩翩的绅士而兴奋不已。他得意地笑了,像对待那些大人物一样,对着镜中的自己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走下楼去。
走在大街上,乔治·杜洛瓦有些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很想尽情奔跑,抑或尽情遐想。他就这么漫无目的地往前走着,一边呼吸晚间清新的空气,一边憧憬美好的未来。可是,他心里总惦记着瓦尔特老头让他写文章的事情。于是,他决定马上回家开始工作。
杜洛瓦大步往回走,沿着环城大道一直走到他居住的布尔索大街。这是一幢七层高的楼房,住着二十户人家,而且都是些工人和城市平民。杜洛瓦点燃蜡绳照明,朝楼上走去。楼梯很脏,纸屑、烟头、菜渣撒满一地,让人不免感到一阵恶心,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个鬼地方,搬进富人们居住的铺着地毯、干净整洁的楼房。这里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股饭菜味、汗酸味、便槽溢出的臭味,以及从陈年污溃和破烂的墙上散发出的霉味,即使再强大的风流也无法将其吹散。
杜洛瓦的房间在六楼,面对着西部铁路公司的一条又深又长的壕沟,不远处便是离巴蒂缪尔车站不远的隧道出口。从房间内俯身往下看,如临万丈深渊。杜洛瓦打开窗户,支起胳膊靠在生锈的窗户栏杆上。
下面是阴暗幽深的通道,里面立着三盏一动不动的红色信号灯,就像猛兽的眼睛。稍远处也有几盏,再远处又有几盏。长短不一的汽笛声不时地划破夜空,有的近在咫尺,有的很远,从阿尼艾尔方向传来,几乎听不清楚。汽笛如同人们的喊声一样,抑扬顿挫。其中,有一声汽笛由远及近,那哀怨的鸣声越来越响,很快便看到一束强烈的黄光,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声朝这边奔驰而来。转眼间,一长串车厢冲入隧道。
过了一会儿,杜洛瓦对自己说道:“好了,该开始工作了!”他把台灯摆到桌子上,正准备动笔的时候,才发现家里只有一叠信纸。
算了,就用这些信纸写吧。杜洛瓦摊开信纸,用笔尖蘸了点墨水,在信纸的顶头写了几个漂亮的大字:
《非洲服役散记》
然后,他开始思考该如何动笔。
他用手托着脸颊,目不转睛地盯着摊在面前的那张白纸,始终无法下笔。
怎么回事?他为什么怎么也想不起刚才在弗雷斯蒂埃家里说过的那些趣闻和经历呢?突然,他想:“我应该从出发那天写起。”于是他写道:“那是一八七四年五月十五日左右,在经历了灾难性的一年后,资源耗尽的法国正处于休养生息之中·”
写到这里,他突然停了下来,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才能引出登船出发时的情景、海上旅行的见闻以及初到非洲时的激动之情。
考虑了差不多十分钟之后,杜洛瓦决定把这一段开场白留到明天再写。现在先介绍一下阿尔及尔的情况。
他在纸上写道:“阿尔及尔是一座洁白的城市……”接着又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他努力回忆着,脑海里出现了这座美丽明亮的城市。大片低矮的平房就像瀑布一样飞泻而下,一直从山顶延伸到海边,但是杜洛瓦却找不到一个完整的句子来描写他脑海里的这番景象以及他内心的感受。
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杜洛瓦终于再次落笔:“这座城市的部分地区住着阿拉伯人……”接着,他放下笔,站了起来。
杜洛瓦的身边摆着一张小铁床,铁床中央已经被他的身体压得塌陷了下去。他瞥见床上随处扔着平时穿的几件衣服,皱皱巴巴,胡乱地揉成一团,简直就像太平间里那些等着人们认领的破烂衣服。在一把麦秸编的椅子上,放着他唯一的一顶丝质礼帽,帽口朝上,像在等待别人的施舍。
墙上贴着灰底蓝花的墙纸,但是已经污溃斑斑,由于年代已久,早已说不清它们的来历,有的可能是被人们压碎的蚊蝇或者残留下的油污,还有的是沾有发蜡的手指印或从洗脸盆里溅出的污水印。在巴黎,这种廉价的带家具出租的房子都是这么寒酸、破烂。一股对贫穷生活的愤怒从杜洛瓦心底油然升起。他告诉自己,明天一定要搬离这里,摆脱这种贫困潦倒的生活。
一股工作的欲望突然抓住了他,他重新坐到桌前,开始酝酿如何描述阿尔及尔这座独特而又迷人的城市。这里是非洲的门户,居住着四处流浪的阿拉伯人和不为人知的黑人。这块神秘而又辽阔的土地等待着人们去认识和开发。迄今为止,人们对非洲的了解还仅限于公园里的那些动物。这些动物仿佛是为人类各种各样充满神奇色彩的童话故事而创造出来的。比如鸵鸟一野鸡的变异品种,羚羊一奇特的山羊,体形颀长、惹人发笑的长颈鹿,笨重的骆驼,巨大的河马,丑陋的犀牛,还有人类可怕的兄弟大猩猩。
杜洛瓦隐约觉得已经有了一些模糊的想法。他也许可以将它们口述出来,至于写成文章,他就一筹莫展了。杜洛瓦为自己的力不从心而感到烦躁不已,他又一次站起来,手心冒汗,血直往太阳穴窜。
这时,他的目光无意落在看门人晚上送来的一张洗衣收费单上。顿时,他感到十分绝望。转眼间,内心的喜悦、自信和对未来的憧憬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完了,一切都完了。他什么事也做不了,简直一无是处。他是那么的空虚、无能,注定不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杜洛瓦转身来到窗口,倚窗而立。正在这时,一列火车呼啸着从隧道里钻出来。它沿着铁路,穿过田野、平原,向海边驶去。杜洛瓦不由地想起了他的父母。
要知道,他们家离铁轨只有十几公里的距离,所以这列火车一定会经过他父母身边。杜洛瓦仿佛又看见了那幢小房子,它位于冈特罗村村口的山坡上,俯视着整座卢昂城和无边无际的塞纳河河谷。
杜洛瓦的父母开了一家小酒馆,取名为“风光酒店”。每逢星期天,住在卢昂郊区的一些有钱人家就来此进餐。两位老人一心希望他们的儿子能够出人头地,于是送他去上中学。杜洛瓦虽然完成了学业,却没有通过毕业会考。最后,他决定去服兵役,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当上军官,上校甚至将军。可是五年的服役期刚刚过了一半,他就开始对单调乏味的军中生活感到厌倦,梦想到巴黎碰碰运气。
父母已经对他不抱任何幻想,只是希望能够把他留在身边。可是他却不顾父母的恳求,服役期一满,便来到巴黎。这一次,他希望自己能够混出点名堂。他隐约感到自己会一举成名,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机会,他也不清楚;他只知道,自己一定会把握时机。
当年在骑兵团的时候,杜洛瓦曾经广受欢迎,甚至还与上流社会的一些姑娘太太们发生过几段风流韵事。他曾经诱骗一位税务官的女儿,后者打算抛弃一切追随他;他还勾引过一位诉讼代理人的太太,这位夫人被抛弃后差点跑去投河自尽。
他的战友们总是这样评价他:“机灵,诡计多端,遇事沉着冷静,总有办法应付。”事实上,他也决心做一个机灵、诡计多端,沉着冷静的人。
在非洲的几年,他的军营生活虽然单调,但是也会经常做一些偷鸡摸狗、欺诈抢掠、目无法纪的事情。他们一边接受军中流行的荣誉观、爱国精神教育,一边耳闻军官们的好大喜功以及在下级官兵中间流传的侠义故事。诺曼底人单纯的天性早已在杜洛瓦的身上消失殆尽,随之而来的是那些三教九流、乱七八糟的思想。
不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顾一切往上爬的欲望。
不知不觉地,杜洛瓦开始想入非非,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这么做。他梦想自己能够有一段艳遇,让他一步登天。他幻想自己和一位银行家或者一位贵族的女儿在街上邂逅,对方对他一见钟情,并且嫁给了他,从此他就可以平步青云。
正在这时,传来一阵尖锐的汽笛声。一个火车头,就像一只从洞穴里窜出的肥兔,从隧道里驶了出来,沿着铁轨,全速驶向车库。汽笛声和火车的“轰隆”声把杜洛瓦从遐想中拉了回来。
可是没过多久,那终日缠绕着他的、幸福而又朦胧的幻想再次涌向心头。他向夜空抛去一个飞吻,这是寄予梦中情人的一吻,也是寄予未来好运的一吻。然后,他关上窗户,一边脱衣服一边喃喃自语道:
“不管怎样,明天情况肯定会有所好转的。今天晚上思路不够清晰,也许是因为喝了太多酒吧!在这种状态下,谁能好好工作呢?”
杜洛瓦上床关了灯,很快就酣然入睡了。
第二天,他醒得很早。当人们心里充满希望或者忧虑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反应。杜洛瓦猛地从床上跳起,走过去打开窗户,想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铁路另一侧,位于对面罗马大街上的房屋,在晨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像是涂了一层白色的油彩。透过青色的薄雾,可以隐约看到右方远处的阿尔让特山丘、萨罗瓦高地以及俄尔日芒磨坊。淡淡的晨雾就像一层轻纱,在遥远的天际随风飘动。
杜洛瓦看着远处的田野,喃喃说道:“天气这么好,那边的风景一定很美。”接着,他想到自己必须马上动手写文章。于是,他掏出十个苏递给看门人的儿子,打发他去办公室帮他请个病假。
随后,他坐到桌前,拿起笔,蘸了些墨水,双手托着脸颊,思考着如何下笔,可是仍然一无所获。
不过,他并不气馁,心想:“任何行业都需要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我对写作毫无经验,刚开始的时候必须有人指点才行。我不如去找弗雷斯蒂埃。这篇文章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于是,杜洛瓦穿好衣服出门了。
当他走到大街上的时候,才发现时间尚早。他的朋友昨天应该睡得很晚,这个时候去他家不太合适。于是杜洛瓦沿着环城大道,慢慢地闲逛。
时间刚过九点,他走进蒙梭公园。刚刚洒了水的公园里,空气湿润清新。
他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又开始想入非非。一位年轻英俊的男人在他面前来回踱步,显然正在等候某位女士。
很快,一个戴着面纱的女人出现了。她行色匆匆,一走过来便握住那个男人的手,然后挽起他的胳膊离开了。
一股对爱情的渴望立即占据了杜洛瓦的心。他多么希望也能够拥有一份与众不同、温柔甜美的爱情啊!他站起身,继续向弗雷斯蒂埃家走去,心想:这家伙运气可真好!
当他走到楼下时,正好碰见他的朋友从里面走出来。
“咦?你怎么会在这儿?这个时候找我,有什么事吗?”
杜洛瓦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他的朋友。看样子,对方正准备出门。他只好结结巴巴地说道:
“嗯……嗯……瓦尔特先生要求我写的那篇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文章,我实在不知该如何动笔。你也知道,做什么事都得需要经验,而我以前从来没有写过文章。我想我一定会很快适应的,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下笔。我有很多好的想法,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出来。”
说到这里,他欲言又止。弗雷斯蒂埃露出狡黠的笑容,说道:
“我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