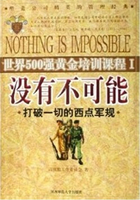杜洛瓦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满脸涨得通红。他感到对方正在从头到脚打量他,审视他。
他本想说几句表示歉意的话,为自己的这身打扮做些解释。但他终究还是什么也没说,因为实在不敢触及这个尴尬的话题。
杜洛瓦在她指给他的一把扶手椅上坐了下来,椅子的天鹅绒坐垫柔软而有弹性,一坐上去就立刻往下陷,但很快又将他托住。椅子的靠背和扶手里也塞了垫料。杜洛瓦仿佛觉得自己开始了一种崭新而又迷人的生活,拥有许多美妙的东西,成了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终于摆脱了以前的窘境,他得救了。他向弗雷斯蒂埃夫人看过去,对方的目光始终没有从他身上移开过。
她穿了一件浅蓝色开司米连衣裙,完美地衬托出她那苗条的身材和丰满的胸部她的手臂和颈部裸露着,胸前的领口和短袖袖口都镶着白色花边。金黄色的头发高高耸起,呈波浪形一直垂到脑后,形成一朵金色的浮云。
弗雷斯蒂埃夫人的注视让他渐渐地平静下来。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注视让他想起昨晚在“牧羊女游乐场”邂逅的那位姑娘。弗雷斯蒂埃夫人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看起来十分特别,鼻子生得很小巧,嘴唇却很厚,下巴处有些赘肉,这使她的脸部轮廓看起来不太规则。但她依然不失为一个迷人的女人,美丽中还带着几分俏皮。她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十分优美,而且具有独特韵味,她的一颦一笑好像不是在说明什么就是在掩饰什么。
短暂的沉默过后,弗雷斯蒂埃夫人问道:“您来巴黎很长时间了吗?”
杜洛瓦已经渐渐平静下来,他回答道:
“只有几个月,夫人。我在铁路局谋了个职位,不过弗雷斯蒂埃昨天告诉我,他能帮我进入新闻界。”
弗雷斯蒂埃夫人嫣然一笑,神情更加亲切。她压低嗓门轻声说道:“我知道。”
这时,门铃再次响起,仆人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德·玛莱尔夫人!”
来者是一位身材不高的褐发女人,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褐发小姐”。
她优雅地走进客厅,身上紧紧裹着一条样式简单的深色长裙。
乌黑的秀发上别着一朵红玫瑰,十分醒目。这朵玫瑰不仅衬托了她的美貌,而且突出了她张扬的个性,让初次见面的杜洛瓦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身穿短裙的小姑娘紧跟在她身后。弗雷斯蒂埃夫人迎上前:
“你好,克罗蒂尔德。”
“你好,玛德莱娜。”
她们互相拥抱。随后,那位小姑娘像个大人似的,一本正经地把脸颊向弗雷斯蒂埃夫人靠过去,说道:“你好,姨妈。”
弗雷斯蒂埃夫人搂着她亲了亲,然后开始介绍:
“这是乔治·杜洛瓦先生,查理的好朋友。”
“这是德·玛莱尔夫人,我的朋友,也是我的一位远亲。”
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说道:
“你们知道,今晚不是什么宴会,大家不必拘于礼节,好吗?”
年轻的男士欠了欠身,表示赞成。
这时,门又开了。一位又矮又胖的男士挽着一位身材高挑的漂亮女士走了进来。这位男士就是《法兰西生活报》的经理瓦尔特先生。他出生南方,是个犹太富商、金融家、实业家,同时还是一名国会议员。他的太太看上去雍容华贵、端庄大方,比他年轻许多。她出生巴齐尔·拉瓦罗家族,父亲是个银行家。
紧随其后的是,风度翩翩的雅克·里瓦尔和蓄着一头长发的诺贝尔·德·瓦伦。后者的衣领已经被及肩的长发裎得发亮,像打了一层蜡,白色的头屑零星地散在肩头。
他的领带随便打了个结,不像是赴宴前系的。这位风流的老头迈着优雅的步子走过来,握住弗雷斯蒂埃夫人的手,在她手腕上轻轻地吻了一下,披肩长发顿时像流水一般洒落在这位年轻夫人裸露的手臂上。
弗雷斯蒂埃最后一个走进来,不断为自己的迟到向客人道歉,声称因为莫雷尔事件,才在报馆耽误了这么久。莫雷尔先生是激进派议员,最近就内阁在阿尔及利亚推行殖民统治请求拨款一事,向内阁提出质疑。
这时,仆人大声喊道:“夫人,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众人一起走进餐厅。
杜洛瓦被安排坐在德·玛莱尔夫人和她女儿之间。这让杜洛瓦感到很不安,担心自己使用刀叉和酒杯的动作不符合礼仪的要求。在他面前摆着四个玻璃杯,那个淡蓝色的应该是用来喝什么的呢?
第一道菜汤上来的时候,大家都没有说话。随后,诺贝尔·德·瓦伦问道:“你们看过关于戈蒂埃案的新闻吗?这案子倒挺有意思!”
于是,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这宗复杂的掺有勒索成分的通奸案。不过他们谈论此案的时候,完全不像在家庭内部讨论报刊新闻,倒像是医生在谈论某种疾病,农民在谈论他们种的蔬菜。在他们脸上,看不到任何气愤或惊讶的表情,他们对罪案本身并不关心,只是带着职业性的好奇探讨和研究事件发生的内在原因。他们试图找出罪犯作案的动机,挖掘出导致这场悲剧的种种思想活动,并最终判定这是某种特殊精神状况的必然产物。女士们对这种研究和探讨,也表现出相当的热情。接着,他们又以新闻贩子和论行出售“人间喜剧”的记者独有的实用眼光以及看待问题的独特方式,对最近发生的大小事件,从各个方面反复加以审察、讨论、分析,并衡量其价值,就像商贩在出售商品前,总要将其反复查看、掂量一番。
不一会儿,话题转移到一场决斗上。雅克·里瓦尔接过话头。这是一个完全属于他的话题,其他人都插不上嘴。
杜洛瓦一句话也不敢说,偶尔曝向他的邻座。德·玛莱尔夫人那浑圆的颈项让他着迷。她的耳垂下方晃动着一颗用金线吊着的钻石,闪闪发光,就像一滴晶莹的水珠,随时会滴到她的肌肤上似的。她不时地参与讨论,嘴角始终挂着一丝微笑。她的想法非常有趣,常常出人意料,就像一位阅历丰富却童心未泯的少女,看待任何问题都毫不在意,对于人们的结论她虽然稍有怀疑却不乏善意。
杜洛瓦本想恭维她几句,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于是他转而照顾德·玛莱尔夫人的女儿,为她倒饮料,收拾盘子,对她大献殷勤。小姑娘比她母亲严肃多了,她煞有介事地向杜洛瓦道谢,并对他点了点头,说道:“有劳您了,先生。”然后继续专心倾听大人们的谈话。
这顿晚餐相当丰盛,大家都吃得十分满意。瓦尔特先生一直忙着狼吞虎咽,几乎没说什么话。每上一道菜,他都要从眼镜下方看看面前的盘子。诺贝尔·德·瓦伦和他一样兴致勃勃,连菜汁都滴到了胸前的衬衣上。
弗雷斯蒂埃面带微笑,神情庄重,仔细地观察饭桌前的每一位宾客,不时还和太太交换着会心的眼神,就像两个要完成某项艰巨任务的合作伙伴,现在一切正按着他们的计划进行。
客人们的脸上都泛着红光,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高了。仆人不时在宾客们的耳边低声问道:“您要考尔通③酒还是拉罗兹堡④酒?”
杜洛瓦发现考尔通酒很合自己的胃口,每次都让仆人倒上满满一杯。他感觉一切妙不可言,一股燥热从胸口直往上窜,然后向四肢扩散,迅速遍布全身。他浑身舒坦,从生命到思想,从身体到灵魂,都得到了一种至高的享受。
他突然很想说点什么,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希望大家都能认真倾听并欣赏他的讲话,就像那些哪怕只发表只言片语也能让人回味无穷的人一样。
但是,人们的谈话一直在继续,从一件事到另一件事,哪怕是一个词、一件小事,也可以让话题从一个转到另一个。他们几乎把最近发生的事都讲了个遍,最后重新回到莫雷尔先生就阿尔及利亚殖民统治的问题向内阁提出的质疑上。
瓦尔特先生在等候上菜的间隙,给大家讲了几个笑话,他是一个怀疑论者,说话无所顾忌。弗雷斯蒂埃谈了谈明天要发表的文章。雅克·里瓦尔要求建立军人政府,把土地分配给所有在殖民地服役超过三十年的军人。
“这样一来”,他说,“就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那时,他们已经了解和热爱这块土地,并掌握了当地的语言,熟悉那些初来乍到者会遇到的所有问题。”
诺贝尔·德·瓦伦打断了他的话:
“是的……他们什么都懂,但却不懂农业生产。他们会讲阿拉伯语,却不知道怎么把甜菜移植过去,也不知道怎样种水稻。他们虽精通剑术,却对耕种施肥一窍不通。我们必须向所有人开放这片土地,精明的人将在那里获得一席之地,而弱者将被淘汰。这是社会运行的法则。”
大家都没有说话,只是报之一笑。
乔治·杜洛瓦终于开口了,这声音连他自己听了也感到十分惊讶,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自己说话似的:
“那里缺少的,是富饶的土地。真正肥沃的土地和法国一样昂贵,而且都被那些有钱的巴黎人作为投资买走。真正的移民,也就是迫于生计流亡到那的穷人,则被赶到严重缺水、寸草不生的沙漠里去了。”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杜洛瓦,这让他感到很不好意思。瓦尔特先生问道:“先生,您很了解阿尔及利亚吗?”
杜洛瓦回答道:“是的,先生。我在那里呆了两年零四个月,并在三个地区生活过。”
这时,诺贝尔·德·瓦伦已经忘记了莫雷尔事件,突然向杜洛瓦问起了当地人的风俗,这些他曾听一位军官说起过。那位军官说的是一个叫马扎布的地方,一个奇特的阿拉伯小共和国,位于撒哈拉沙漠一这个世界上最炎热的地方的中部。
杜洛瓦曾到过马扎布两次,他向众人讲述了这个神奇国度的风土人情:那里惜水如金,居民都要担任社会公务,商人诚实守信,远胜过文明国家。
借着酒劲和取悦众人的愿望,杜洛瓦侃侃而谈,讲起了军队里的趣闻、阿拉伯人的某些特征以及战斗中的惊险经历。他讲得绘声绘色,把这片终年烈日当空、光秃秃的黄土地极力渲染了一番。
女士们的目光全部集中在他身上。瓦尔特夫人慢条斯理地说道:“您可以把您的回忆写成一系列文章,一定很吸引人。”瓦尔特先生的目光从眼镜上方射进来,看着眼前这位年轻人。每次细细打量别人的时候,他总是这么做。而在看菜的时候,他的目光是从眼镜下方射出的。
弗雷斯蒂埃趁机说道:“老板,这便是我今天向您提起的乔治·杜洛瓦。我希望您能让他加入我们政治新闻部,协助我收集一些政治资料。自从马郎博走后,一直没有人帮我收集紧急的内幕资料,这给报馆带来了不少损失。”
瓦尔特先生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取下眼镜,从正面仔细打量了一番杜洛瓦。过了一会儿,他说道:“很显然,杜洛瓦先生的确才华出众。如果他愿意的话,明天下午三点我们可以就此事再谈谈。”
沉默半晌之后,他转身对这位年轻的小伙子说道:
“您先写一些阿尔及利亚随笔,谈谈您的回忆,顺便讲一下有关殖民地问题,就像刚才说的那样。这些都是热点新闻,我可以肯定,读者一定会非常喜欢。所以,您一定要快。我希望明天或者后天就能拿到您的第一篇文章。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议会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的同时,引起公众的关注。”
瓦尔特夫人带着她一贯的严肃表情,好意提醒道:“您可以用《非洲服役散记》作为题目,定能吸引读者,诺贝尔先生,您觉得呢?”
这位大器晚成的老诗人对后起之秀既厌恶又害怕,冷冷地回答道:“好当然是好。只是后面的文章能否始终保持协调一致,并不容易。这与音乐上讲究的基调是一个道理。”
弗雷斯蒂埃夫人悄悄地向杜洛瓦投去赞赏和理解的一瞥,好像在说:“你一定会成功的。”德·玛莱尔夫人好几次转过头来望着他,那颗用金线吊着的钻石耳坠不停地晃动,像一滴随时会掉落的水珠。
她女儿依然表情严肃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低头看着自己的盘子。
这时,仆人绕着桌子给每一位客人的蓝色玻璃杯里斟上约翰内斯堡葡萄酒。弗雷斯蒂埃举起酒杯,对瓦尔特先生说道:“为《法兰西生活报》的兴旺发达干杯!”
所有人都向这位笑容满脸的老板躬身致意。杜洛瓦也像取得了一场胜利似的,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此时此刻,即使是一桶酒他也能把它喝干,甚至吃下一头牛,掐死一头狮子也不是问题。他感到自己拥有非凡的力量,必胜的信心,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希望。现在,他在这些人中间已经可以应付自如了,他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用一种崭新而自信的眼神扫视了一遍桌上的宾客,然后终于大胆地和他的邻座德·玛莱尔夫人搭起讪来:
“夫人,您戴的耳环是我见过最漂亮的。”
德·玛莱尔夫人转过头来,微笑地望着他:
“在金线上方挂一颗钻石,是我的创意。这看上去就像一滴露珠,是吗?”
杜洛瓦为自己的大胆感到不安,担心会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他犹豫着说道“真的很迷人……但也要您这样的人来戴才相配。”
德·玛莱尔夫人向他投来感激的一瞥,目光如此清澈明亮仿佛能够洞穿对方的心事。
杜洛瓦刚把目光从德·玛莱尔夫人身上移开,又看见弗雷斯蒂埃夫人正朝他看过来。后者始终带着亲切的微笑,杜洛瓦觉得自己在她眼中看到了一种更加明显的愉悦、戏弄和鼓励。
饭桌上的男人手舞足蹈地说着话,个个声音洪亮。他们谈起了修建地下铁路的庞大计划。这个话题一直持续到吃完甜品。每个人对巴黎缓慢的交通都有一大堆牢骚:有轨电车诸多不便,公共马车令人讨厌,马车夫极其野蛮。
接下来,大家起身离开餐厅,准备去喝咖啡。杜洛瓦开玩笑似的向小姑娘伸出一只手,没想到对方一本正经地道了谢,并踮起脚尖将手搭在邻座的胳膊上。
走进客厅,杜洛瓦再次感到自己像是进入了一间温室花房。房间的四周都是高大的、枝繁叶茂的棕树,树干直达天花板,像喷泉一样伸向四周。
壁炉两侧放着两棵橡胶树,树干粗壮得像两根大圆柱,长长的绿色叶片重重叠叠。钢琴上摆放着两株不知名的圆形小盆景,上面开满了鲜花,一株是红色的,另一株是白色的,看上去就像人工制造的,因为太漂亮,反而给人不真实的感觉。
客厅里空气清新,伴有一种淡淡的、难以形容的香味。
杜洛瓦神情镇定,仔细地端详着这间屋子。房间并不是很大,除了各种植物外,没有任何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也没有任何鲜艳的颜色让人感觉耳目一新。但是,人们一走进这里,就好像得到了温柔的爱抚一样,顿时感到心情舒畅、悠闲安逸。
墙上挂着紫罗兰色的帷幔,由于年代已久,已经开始褪色。帷幔上用丝线绣着一朵朵小花。
门帘是用蓝灰色军用呢制成,上面用红丝线绣了一圈石竹花,一直垂到地面。大小、形状不一的椅子随意摆放在房间四周。无论是长椅,大小扶手椅,还是圆凳和墩状软座都套上了一层用路易十六时代的丝绸或印有石榴红图案的乳白色乌特勒支1天鹅绒制成的椅套。
“要来杯咖啡吗,杜洛瓦先生?”
弗雷斯蒂埃夫人为他端来满满一杯咖啡,嘴角依然挂着友好的微笑。
“好的,夫人,谢谢。”
杜洛瓦接过杯子。当他弯腰用银制的夹子在小姑娘端着的糖罐里小心翼翼地夹方糖时,年轻的女主人轻声在他耳边说道:
“去和瓦尔特夫人套套近乎。”
没等他开口,弗雷斯蒂埃夫人已经转身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