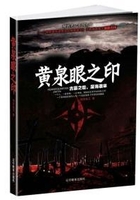薛祥顺是成都北门外万福桥南岸陈麻婆老店里面一位红锅上掌勺儿的师傅,人高高长长的,长方形的脸,有些清瘦,是一位埋倒脑壳只知道做活的“帮帮匠”(受雇于饭馆当个工人)。诚实朴素,很少言语,农历十月初一北门城隍庙会期,成都已开始冷了,而他还是一双线耳子草鞋,永远是那件油腊片的蓝布衣裳。这是20年代陈麻婆饭店薛祥顺的形象,以后几十年见他,从外形上看,好像变化不大。
我什么时候认识他,已记不确切了,但有一点还记得起来:是20年代下半期,我有几个好吃同学,经常一起去吃陈麻婆“打平合”。我们是从新东门出城,沿护城河,过猛追湾,经过一些乱墓坟的荒地,秋天芦苇成林,藕荷色的芦花像掸帚子一样随风飘动,沿着高大的城墙,那时是很完整的城墙,再经几弯儿转,到了大南海,北门大桥的十八梯,向西沿木厂就到了万福桥陈麻婆豆腐店了。
于是我们分头去割黄牛肉(成都人不吃水牛),打清油、打酒、买油米子花生。牛肉、清油直接交到厨上,在牛肉里加上老姜,切碎。向薛祥顺师傅说明几个人吃好多豆腐,他就按你的吩咐做他红锅上的安排。
麻婆豆腐店里双间铺子,方桌长板凳,与一般饭店一样,很简陋。从这里过万福桥向北走,是与去新繁、彭县的路相接,虽是小路,往来人多,也是鸡公车的往来道路。
每次我都要看薛祥顺师傅做麻婆豆腐,看它的全过程,我也回家试验,我的作料比他的更齐全,但没有一次做的所谓“麻婆豆腐”达到薛祥顺的水平。为什么?火候二字也。火候二字可以写本书,况前人也叙述不少。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就今天国营陈麻婆豆腐店做出来的麻婆豆腐,也不同于过去薛祥顺的亲手做法了。那时是黄牛肉(音dú)豆腐,现在用的是猪肉,大异其趣,那种黄牛肉出来的香味消失了!解放后,1957年它迁到北门大桥下簸箕街右手边,打的招牌是“公私合营陈麻婆老饭店”。8月搬到梁家巷二道桥,以后迁到西玉龙街(请李劼人、余兴公写招牌)。任你东迁西搬,豆腐没有用黄牛肉,等于失掉灵魂。解放以来,去吃麻婆的人无从比较,猪肉也了三十几年,人们照吃不误,麻、辣、烫、酥、嫩,虽是大锅做法,仍然可口,不管怎样,没有别的可以代替,坐下就吃,来得爽快利落,价廉物美,况它保持麻婆豆腐的基本要素,仍然展示出川味川菜的特点特色。
文学上有比较文学,品味上无比较品味学,这个差异对进馆子去吃饭的人来说问题不大,甚至没有问题,无从比较。但是站在烹饪技艺上看来,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
薛师傅豆腐的先后程序我看的时间较久,至今尚能清楚记忆:他将清油倒入锅内煎熟(不是熟透),然后下牛肉,待到干烂酥时,下豆豉。当初成都口同嗜豆豉最好,但他没有用,陈麻婆是私人饭馆,没有那么讲究;下的辣椒面,也是买的粗放制作那一种,连辣椒面把子一齐舂在里面,——只放辣椒面,不放豆瓣,这是他用料的特点。解放后加了豆瓣,正如走马街聋子焦,解放后加了点豆瓣,连名字也改成了“烧饼”了。我在成都生长,儿时看川戏起从海报上、报纸上、文字上看到的康子林,解放后有人要标新立异,硬写成康“芷”林,大概也算是成都“烧饼”派吧?
然后下豆腐:摊在手上,切成方块,倒入油煎肉滚、热气腾腾的锅内,微微用铲子铲几下调匀,搀少许汤水,最后用那个油浸气熏的竹编锅盖盖着,在岚炭烈火下熟后,揭开锅盖,看火候定局:或再一下,或铲几下就起锅,一份四远驰名的麻婆豆腐就端上桌子了。
为什么它的好吃又超过今天陈麻婆豆腐店呢?主要原因它是小锅单炒,那些大锅“大伙庄稼”自不能与小灶相比;其次是在吃麻婆的人,清油要自己去买,有经验的顾客,总是多买清油,豆腐以油多而出色出味,这是常识了。虽说是常识,也有那种莫里哀的“悭吝人”,处处打小算盘,少打了清油,巧妇难为无米炊,你能怪薛祥顺么?“食不厌精”,在于精到,要动脑筋,不在于山珍海味。
从万福桥头的陈麻婆到国营陈麻婆饭店,几十年来,不断在变,但万变不离其宗,所以它有生命力。日本有一种罐头,也叫“麻婆豆腐”,70年代在成都市场出现过。打开罐头,下面用火点燃,上面的所谓麻婆豆腐可以热吃。罐头本身具备热吃,玩意儿很新鲜;打的名牌,又可号召,会动脑筋,会做生意。但是,完全不是麻婆那个味道,无以名之,以后就再也不见了。也许它还可以赚得没有吃过陈麻婆豆腐的人几文钱,如斯而已。烹饪饮食,作为一种艺术看,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虚假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在求真、做人上,使人难忘的是薛祥顺师傅。最使人难忘的是,20年代我在万福桥看见他在红锅上用的一把小铲子,见方两寸多,被他经年累月炒呀铲呀!使用得只剩下2/3了,铁棒磨成绣花针,绳锯木断。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薛师傅啊,你不知度过多少难挨的生活与时日?在秋风飒飒冻裂皮肤的寒冷的日子里,你那双破烂的线耳子草鞋,单薄的蓝布裤子,清瘦的脸孔,逝者如斯,万福桥下的流水——
解放了,你的手艺传授给下一代。在西玉龙街陈麻婆饭店又见到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一个永远沉默寡言,埋头实干的人,值得尊敬的好师傅。我每次吃完时,都想去招呼他,但总看见他太忙!油烟呛着他那清瘦的脸,我实在不好再去给他添加一丝儿麻烦了。我们也会过面,是在他休班时的茶铺里头,他向我谈了他的身世,他把他的照片送我。
困难三年中,我很少进馆子。一则没钱,二则怕见熟人。彼此都弄得很尴尬了,在那朝不虑夕的日子,何苦去给人添加麻烦。有一天下午4点钟左右,我同一位老友进到陈麻婆饭店,那时候是馆子“吊腰”的时刻,人较少,凑巧我们彼此看到了,他招呼我进到后面一间窄窄的屋子里去,很快地给我炒一大份鱼香圆子来,困难三年中哪去找什么鱼做圆子啊?拈一块进嘴,却原是土豆做的鱼圆子,加上家常鱼香味,在那样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薛师傅不说一句话,就为我们弄了这一份好菜来,感激得难以言语形容了!扬琴里的《辞剑浣纱》、《伍员渡泸》,川戏里《漂母赠饭》等情节也浮现出来,“呜呼,士穷乃见节义”等句子也脱口而出。
薛师傅1973年病逝。离开我们三十个年头了。停笔默思,他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