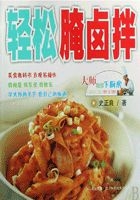“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在古拉格,食物短缺,年轻的女人们总是待遇好一些,原因不言自明。劳改营的领导不给犯人吃饭,于是犯人们吃腐烂的死马,吃地衣和苔藓,甚至吃机器的润滑油。只要是能吃的,都可以下肚。而如果想叫一个人背叛自己的灵魂,在这种情况下也简单异常——只需要给他一顿饱饭。一个叫巴比奇的犯人,在一桌子热腾腾的红菜汤和煎牛肉饼面前,哆嗦着写下 24 个人的名字,结果可想而知,他如动物一般猛餐一顿,那 24 个被他出卖的人,被枪决。
在认识王琪博之前,我并不知道有一碗饭叫做“血泡饭”,这是一句重庆俗语,用以形容那些打打杀杀的生涯。王琪博江湖人称“王七婆”,瘦的像一把刀,重庆人,写诗,画画,从来不看书,身手敏捷,年轻时有过打打杀杀的生涯。他曾经数次在死亡边缘游走,别人赌博,他赌命。最后总是他赢,艰难着活到 21 世纪。他献上头颅,头颅里盛放着一捧“血泡饭”,以此果腹,敬献给这个神奇的世界。我跟他一起喝酒聊天,总会想问问他那个世界的故事,平时我们在阳光下行走,他在黑白边缘,一手执黑,一手执白,两枚棋子都在血水里浸泡。
他喜欢吃火锅,嗜辣,身体被这个世界开刃,永远都是亮晶晶。他恍惚其次,那些血泡饭的往事似乎已经过去多年,不再提起。
五
有一段时间,作家狗子喜欢在喝高了的饭局上,问别人“什么是爱情”,这是个无解的问题。而我喜欢问别人“如果你生命还有一天,你想吃什么”。醉酒的饭桌上往往喧闹,这样的问题不会给热闹的餐桌带来一点冷场,往往是更喧闹。有人为了这最后一顿饭举起了酒杯,集体走一个。这个问题似乎有解,得到的回复都是一些简单的吃食,诸如一碗炸酱面,一碗豆汁之类的。
也有人愿意跟我一样追问相似的问题,BBC 做过一个纪录片,叫《50 Things to Eat Before You Die》,死之前要吃的 50 种食物,其中分门别类,有牛排、龙虾,泰国菜、中国菜,冰激凌,也有鳄鱼肉、鹿肉、天竺鼠之类的蹊跷物。不同的人在镜头里细细描述着那些食物,这哪里是食物,其实是把生命的灰尘寄居在那些微小的食物之中。
也有人专门出过类似的书,摄影师 Melanie Dunea 写过一本书,向世界著名的厨师询问:你最后的晚餐想吃什么?回答很简单,一种是与幸福回忆相关的家常菜,一种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料理的顶级食材。比如,母亲亲手做的巧克力,或者父亲亲手做的冰激凌,味蕾总是受到回忆支配,过去的美味,无法重现,就像你年轻时深爱过的女孩子,十几年后如果再次相逢,也往往狼狈不堪,你已经微胖秃顶,她已经身材变形,市侩庸俗。
关于最著名的最后的晚餐,被达 . 芬奇画成了一幅画,耶稣与门徒一起吃下最后的晚餐。那是逾越节的晚宴,杀好了羔羊,吃苦菜,无酵饼,葡萄酒也应该是无酵的,这是逾越节的规矩。
后来这件事成就了教会的两大圣礼之一:圣餐礼。
对于我们这些庸常的人来说,也从中获得了许多好处:
葡萄酒。在法国,葡萄酒最早都是教会酿造的,一千多年的过程之中,教士们种植葡萄,酿制葡萄酒,作为耶稣的血,在圣餐礼上饮用。
相比而言,中国的皇帝们,最后的晚餐也是极尽奢侈,翻看《膳底档》,可以查找出许多蛛丝马迹。嘉庆四年的大年初一,乾隆已经是风烛残年,即便如此,他那一天的菜单也是丰富异常:燕窝肥鸡丝热锅一品,燕窝烧鸭子热锅一品,肥鸡油煸白菜热锅一品,羊肚片一品,托汤鸡一品,炒鸡蛋一品,蒸肥鸡鹿尾一品,烧狍子肉一品,象眼小馒头一品,白糖油糕一品,白面丝糕糜子米面糕一品,年糕一品,小菜五品, 咸肉一碟,攒盘肉二品,野鸡粥一品,燕窝八鲜热锅一品。
我猜测乾隆皇帝不过是在床上看着这些珍馐美味罢了。两天之后,那一年正月初三的早上,乾隆驾崩。
六
十几年前,陆幼青写过一本《死亡日记》,他记录下面对死亡的种种坦然,颇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大度。其中也会提到吃,他本是一个吃货,然而在最后的日子里,“想起来的美食几乎跟饭店无关,全是菜名,甚至有不少是我在外地吃的,留下深刻印象的。开个玩笑,我现在如果开张菜单,御膳房也没辙。前两天,忽然念及上海大壶春的生煎馒头,觉得比较有可行性,便由妻驾车巴巴地赶了去,如愿以偿,但只吃了 4 个,也觉得就是如此了。”
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光里,美食早已经不是食物,而是一种对世界的回忆,以及念想。哪里是充饥解馋,无非是yesterday once more,在旧日重现的光景里,想念着那时候的人和事,吃食仅仅是一粒明晃晃的纽扣,悬挂其上。
看关于侯宝林的传记,提及侯宝林临终的日子里,他最想吃的是冰激凌。那时候北京已经是冬天,市面上已经少有冰激凌出售,儿女跑了大半个北京城,买到了一个冰激凌球,侯先生在病床之上,只是欣慰地看看,却已经无力吃下。我猜想在冰激凌慢慢融化的空当,侯宝林回想起的只是少年时代的光景。那时他 12 岁,在天桥撂地摆摊卖艺,每到夏天,最能感染少年侯宝林的就是小贩一声声“买冰核儿”的叫卖。他那时的心愿便是以后挣多了钱,天天吃冰激凌。
许多人年少时都会有如此奢望,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灌肠,北方农家做法,用的是真正的猪大肠灌上肉馅,而是不现在常见的肠衣。肉馅里面掺上了淀粉、葱花各种香料,表皮肥腻,一咬一嘴油。这是我小时候关于美食的至高想象,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吃。而且最好吃的方式是偷嘴吃,妈妈买来灌肠,放在桌子上,它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像是静置的神物。等不到晚饭的时候,切成一片片摆放在盘子里,我总是偷偷地,掰下一小节,迅速吃下,大口咀嚼,整个口腔被塞满得充盈。
过半小时,我会再一次看着那静静的灌肠,发呆,然后忍不住又去偷偷掰下一节,食物的诱惑呀,往往在吃饭的时候,我已经偷吃大半。那时我的心愿就是:要是有吃不完的灌肠,吃死了我也认。
许多人都是如此,秦朝宰相李斯被处腰斩,临死之前对他的儿子说:“吾欲与汝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不可得了,自己明明知道是奢望,却还是想努力地回头张望。能望到什么呢?不过是一片白茫茫。
有一本书叫《让日子多一点生命》,讲的是德国米其林厨师培希特的故事,他是当地临终关怀机构的厨师,他所面对的都是风烛残年者,没有胃口,等待死亡的苹果砸落到自己头上。
为这些濒死者做饭,超高的厨艺派不上用场,高级的食材也没有市场,他们只是想吃这辈子印象最深的食物,犹如陆幼青的生煎,侯宝林的冰激凌,以及我小时候的灌肠,这吃的完全只是回忆。
这本书中记录了一个人,他想吃牛排,但肿瘤挤压食道让他无法下咽,他只能在嘴中咀嚼几口,品尝一下味道,然后再吐出。还有一个人,味觉已经丧失,而主厨就为他做色彩鲜艳的菜式,而她竟然有一天在一份汤中尝出了芹菜味道而兴奋不已。而主厨当然没有放芹菜,一直到死都为她保持着这个美味的谎言。
尽管是个名厨,他却没有老主顾,死亡纷至沓来,今天还聊天的客人,明天就成了一缕烟。每天迎来送往的不是吃客,而是生命。有人问主厨在临终关怀机构工作会不会后悔?培希特说,那些高级餐厅的昂贵食物,只不过是给客人用来炫耀的,并非真正的美味。直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天,你才会清楚自己最爱的食物是什么。
七
我只是试图寻找美食的背面。透过食物这扇窗户,朝外面张望,可能漆黑一片,可能有点点星光,而此刻,外面正在下雨,一场小雨。食物从来不是食物本身,而是生活与经验。人类的美食史,也是人类的饥饿史,在人类历史的缝隙中,下着小雨,有点恍惚,以至于看不清楚。
没有过多久,许多事情就已经湮没了,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代食品”了,才几十年的光景,这看上去就像是个笑话。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人们已经吃不到粮食,于是吃糠,吃野菜、树皮,连这些都没有吃的时候,国家号召“代食品”,实行“低指标”“瓜菜代”,克服困难,度过灾荒。代食品有许多种:小麦根粉、玉米秆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其中最有名的是小球藻。
小球藻其实就是蓝藻,当时报纸上发表文章,说何必吃鱼肉蛋禽,食物不过是蛋白质,小球藻就富含蛋白质,并且在水里极易繁殖,简单易行,取之不尽。于是有关部门下令大搞小球藻,许多地方都成立了小球藻小组,专门研究小球藻。在那个年代,许多的事情都是作为政策下达的,诸如合理密植、深翻土地、瓜菜代、大炼钢铁,增量做饭法。1960 年 7 月 6 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文中还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酱等食品,清香可口;有人用小球藻粉哺育婴儿,效果跟奶粉不相上下。
一声令下,全国各地都流行培育小球藻,做小球藻的关键在于采集小球藻的培养液,最常见的方法是用人畜粪尿稀释,并且以 1%~2% 稀释人尿为最佳。
可以想象其味道:绿色的浑浊的一碗粥,里面有刺鼻的尿臊味道。在此之前,这些东西一般用来做喂猪的猪食,终于有一天,它摆上了饥饿的餐桌。
几十年之后,小球藻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它摇身一变,成为有助健康的保健品,抗衰老,降血脂,然而知道那段代食品历史的人们,对此不过一笑而之。
还是有许多事情被遗忘了。我爷爷坟前的柳树快 50岁了,粗壮茂密,我每年清明都会去上坟,看柳色氤氲。
奶奶已经与爷爷合葬,相隔 40 多年之后,重新相逢。奶奶临死前几天,早已经失去了知觉,凭借着葡萄糖和营养液维持心跳。有一天,她忽然清醒,回光返照,与所有人问好,也认识所有家人,似乎胃口也见好,想吃一点面条。面条做得极为软烂,她挣扎着吃了一口。几天之后,她在睡梦中离世。
卡夫卡写过一部小说——《饥饿艺术家》,我是因为这篇小说喜欢上了卡夫卡,他讲了一个人表演饥饿的事故,最后终于饿死。饥饿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而所谓的美食,也不过是手段,目的是死亡。世界上哪里有什么美食可言,都是在死亡的大山前,说说笑笑,等待着它的降临。美食虚幻无比,死亡才真实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