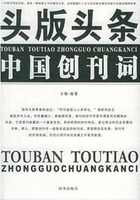从早上开始,天气一直阴沉得可怕,每一次呼吸,都有满满地凉意冲刺肺腑,就好像此时他的心情,只觉彻骨地冷。
当云层终于承受不住早冬的寒气,纷纷扬扬地下起细碎的雪时,在街上赶路的人们都下意识地抬起头来,望向天空,感叹今冬的雪来得是这样的早。
幽幽地,那双眼睛的主人轻叹了一口气,他告诉自己,既然决定了,就要做下去,哪怕心会痛死。
星宓的视线从窗外调回,无意识地盯着面前的茶碗,心情沮丧极了。
她知道她和懿祯之间一定出了问题,从她看到懿祯不告而别去承德的那一刻起,她就知道了,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问题出在哪里?
现在的懿祯就像个闷葫芦,不止将她拒在心门之外,甚至连人都是拒之千里的。
屡次邀他来府里相聚,他都不肯,所以星宓才选了他们曾经一起来过几次的待月楼,可是,如果今天他再不来……
星宓的鼻头直犯酸,如果今天懿祯再不来,她要怎么办?
昨日在宫门外的“毫言壮语”——说懿祯再不来见她,她就要向太后老祖宗请安,可是,现在想来,她该以什么名目恳请太后做主?
星宓苦笑,以弃妇吗?他们之间根本就还没有过海誓山盟,连皇上赐婚都只是嘴上说说,甚至她的内心里也是抗拒着嫁进皇宫的,所以,她凭什么去指责懿祯的不是?
所以,懿祯啊懿祯,我该拿你怎么办?而你,又想拿我怎么办呢?
终于,有人从屋外挑了帘子,终于,有个高瘦的身影缓缓地进了雅间,终于,星宓见着了阔别了四个多月的懿祯。
懿祯站在门口,他望着星宓,如果是在以前,他一定会问上一句,“我的小星宓,秋猎好玩么?”然后星宓就会像一只美丽的小鹿一般蹦到他的身边来,摇着他的手臂,兴高采烈地说开来,“懿祯啊懿祯,我告诉你,草原是那么那么的美,草原的夜空,星星是那么那么的亮,草原上的牛群、羊群是那么那么的庞大,就像天上的云……懿祯啊懿祯,我告诉你……”
可是,你知道吗?星宓,每一次你对我说着那些我也无比向往,却永远不可能去经历的事物时,我的心里都会情不自禁地涌现出几许落寞啊。
我是多么想与你一同去畅游天下,在草原上策马驰骋,一起陪你去看海的那一边有些什么样的人,与我们又有着什么不同……
现在,你的身边又有了一个靖月,他是那么的优秀,最重要的,他健康的要人嫉妒,九王爷那天还特地提起,靖月会在来年参加科举,九王爷对他栽培的用心我又岂会察觉不出?所以,星宓,我放你自由,只希望你能幸福。
打帘的小铁子对翠儿使了个眼色,翠儿立即意会,回身关了窗子,默默地随小铁子退出了雅间。
星宓站起来,慢慢地走向懿祯。
懿祯知道星宓在生气,所以一心等待着她的暴发。
但是,没有。
星宓是那么的平静,她只是望着他,目光中流转着凄惶、无助和委屈,晶莹剔透,懿祯从没有看过这个样子的星宓,令他整颗心都揪疼了起来。
当星宓站定在懿祯的面前时,她张开双臂,缓缓地,倾身抱紧了他。
星宓将头轻轻地靠在懿祯的胸前,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静静地慰贴着。
而懿祯则是一动不动地任她依偎,两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苦楚,一个是不能说,另一个是不知从何说起。
“懿祯,”许久之后,星宓的声音才从懿祯的胸口传来,闷闷的,带着抽泣和难以抑制地颤抖,“你不要我了,是不是?”
懿祯本以为,他对她刻意地冷漠,足以令星宓对他大发脾气,并且已*下决心,做好了与星宓大吵一架,直至决裂地准备……却从没有想过,星宓是以这么可怜兮兮,这么委曲求全,这么不知所措地模样,来到他的面前,*着下唇,强忍着哭意地问他——“懿祯,你不要我了,是不是?”
我要,我要,我发疯般地想要你!
有那么一刻,懿祯几乎就想这么抱紧星宓,大声地告诉她,他是有多么想她……但是,当话冲到口边,却被他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他不能,因为他爱星宓,胜过爱自己。
懿祯抬起双手,在空中停了停,才轻轻落下,拍了拍星宓的背,温和地不带一丝情绪地说:“星宓,别这样。”然后,他扶着星宓的肩,将她从自己的怀里推开。
星宓抬头,泪眼朦胧中,她看向他,不知为什么,此时的懿祯,令她觉得陌生。
“星宓,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承德吗?”懿祯开始诉说他早已想好的台词,他以淡漠地目光注视着星宓的眼睛,他告诉自己,不准心软,只是背在身后的手,指甲狠狠地嵌入了掌心——只有痛才能够令他清醒。
星宓呆呆地望着他,她是想知道这答案的,从四个多月前,看到懿祯坐在辇车中去承德的路上,她就想知道了,可是,现在直觉却告诉她,不要听。
“你一定听说了,从遥堡镇回来,太后曾经想请皇上为我们赐婚的事。”懿祯不管她要不要听,自顾自地说起来。
星宓傻傻地点头,吸了吸鼻子,将泛滥地泪水逼回去。
“那件事是我压下来的,太后原本不肯同意,却架不住我屡次恳请她老???家改变心意。”说到这里,懿祯顿了一下,问星宓,“你知道为什么我执意要这么做吗?”
星宓傻傻地摇头,于是懿祯继续说下去,但是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避开了星宓的眼睛,他说:“因为我忽然意识到,我不能娶你,我不愿意你成为我的妻子,不愿意在未来的生命中,都与你在一起。”
星宓的眼睛蓦然睁大,不敢置信地瞪着懿祯,她微张着双唇,她想大喊出声,她想说他骗人,但是,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哪怕一个音节,因为她感觉她的整个喉咙都在颤抖,仿佛哑了,忽然之间失了声,唯有胸口处,有什么东西正在碎裂,噼噼啪啪地,痛得她大口喘气。
“星宓,我喜欢你,这一点你不用怀疑。但是,我们之间是哪一种喜欢呢?”懿祯走到窗边,轻轻将窗子推开一些,令屋外清冷的空气进入,硬着心肠说下去,“我们从小认识,一直青梅竹马地在一起,仿佛喜欢对方,在意对方,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却谁都没有想过真正的男女之爱是个什么模样。直到靖月的出现,他作出追求你的姿态,你们两个总是形影不离地在一起,我却没有太多醋意,我在意的只是,他会不会欺负你,有没有对你不好,直到那时我才猛然明白,我对你的感觉,就好像一个哥哥在担心自己心爱的妹妹。”
说到这里,懿祯逼自己回头,面对星宓,他要清清楚楚地告诉她,“所以,我们之间不是爱情。爱情是轰轰烈烈的,爱情是非卿不可的,爱情是自私专横的,爱情是绝不允许他人介入的……”
懿祯盯着星宓的眼睛,再次斩钉截铁地强调:“我们之间,不是爱情。”
我们之间不是爱情……我们之间不是爱情……我们之间不是爱情……
这句话在星宓的脑中炸开来,轰轰隆隆地像闷雷,令她愣在那里,瞪着懿祯,不知所措。
自小时候相识以来,星宓就很听懿祯的话,虽然懿祯从不对她说教,但是就算她再淘气任性,脾气再倔强,有时连九王爷夫妇都治不住她的时候,懿祯却能够轻易地让她乖乖妥协,从一匹小野马变成一只温顺的小绵羊。
所以,只要是懿祯说出的话,对于星宓来说,都是很有分量的,更何况懿祯说得是这么的斩钉截铁,毫无疑义。
所以,她忘了问自己,就算懿祯只拿她当妹妹看待,那么,她又拿懿祯当什么呢?爱情从来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但是,星宓还太小,她只有十五岁,当被她奉为神祇般的懿祯这么告诉她的时候,她便相信了,至少她是相信了,懿祯对于她,不是爱情。
雪,静静地下着。
并且越下越大,从细碎的雪粒转变成纷纷扬扬地大片大片的白色花朵。
走在大街上,星宓伸手接住几片晶莹,看着那六角琼花的美丽,默默地哀悼她的爱情,不,懿祯说他们之间并不是爱情的……那么,她该哀悼什么呢?
泪,悄悄地*脸颊。
心,连喘一口气都在疼。
懿祯,我忘了问你,当你意识到我们之间不是爱情的时候?心痛了吗?如果你也和我一样,那么,你又是如何治愈的?
翠儿亦步亦趋地陪在星宓的身边,伸手想要为主子打伞,却被星宓推开了。
一辆王府的马车默默地跟在她们的身后不远处,老车夫熟练地驾驭着马车,有时会悄眼瞧瞧这主仆二人,一脸好奇与担忧,而马儿也仿佛感受到了气氛的不寻常似的,耷拉着脑袋,只是喷气慢行着。
雪天的大街上,行人本就稀少,偶有两三个人也只是匆匆赶路,谁也不会对谁多送去半分关注。
但是,星宓所不知道的是,在她们的后面,还有主仆二人在远远地跟随着。
同样的悲伤,一条街的两端,就这样无法抑制地蔓延。
直到看着星宓走进九王府,懿祯才停住脚步,静静地,望着星宓消失的地方——那两扇漆红色的大门,在街的拐角处站了许久。
九王府内。
“格格,格格,就让翠儿陪着您吧,格格……”星宓的房门外,翠儿焦急地拍着门,带着哭腔地求着门里的星宓,因为前一刻,在星宓前脚刚踏进房门时,星宓就回身将她给推了出来,并且把门一关,从里面上了闩。
接着,星宓的哭声便从屋内传了出来,惊天动地地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哭泣,让即使并不知原由的人听到,都忍不住心生哽咽。
“格格……呜呜……”翠儿在门外急得抹眼泪儿,从她到府里当差以来还从没见星宓这么哭过……懿祯贝勒爷不是最疼格格的吗?可是他究竟对格格说了些什么呀?格格怎么会难过成这样啊?
星宓哭了很久,伏在卧榻上,仿佛要把满心满肺的痛,满心满肺的委屈都借由哭泣来发泄一般地毫无顾忌。
从孩提时,星宓就很不屑于这个样子完全不顾形象地嚎啕大哭,曾经,她看过同龄的孩子因为心爱的玩具被坏孩子抢去,而坐在地上咧开嘴巴,大声的哭泣,她就觉得那形象实在是丑极了。
但是现在她才知道,当心爱的东西从手边溜走时,她所能做的,竟只有哭泣。
“星宓啊?额娘的心肝儿,你快将门开开,让额娘看看你呀……”闻讯赶来的福晋也拍着门,冲屋里喊着,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还有几个儿媳妇、一大帮丫环、老妈子也都聚在了星宓的门前,急得团团转。
大家听着星宓的哭声,全都红了眼眶,纷纷问翠儿,星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于是翠儿就向大家说了星宓与懿祯见面的经过,但具体为了什么,她也不知道。
福晋听了翠儿的话,心里大概猜到几分,亦不免难过,本来就是一对儿装着彼此的小情人儿,现在却得硬生生地分开,放谁身上不是痛断了肝肠?唉,这是造的什么孽呀?
“这是在闹什么呢?”刚刚从水务司回来的九王爷站定在院子里,厉声喝问,他的身后是第五子德克锦和去了水军大营实地学习作战技术的靖月。
辨出哭声是由星宓的房内传来,靖月首先冲到门口,手扶在门框上,强忍住破门而入地欲望,眉头皱得死紧,星宓怎么了?他所认识的星宓从来都不是个会放声大哭的女孩子。
福晋来到九王爷面前,小声的说了些什么,九王爷才倏然意会地点了点头,不郁地面色缓了下来,却又腾升起一抹愁,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对福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