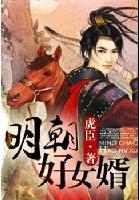又明年,齐伐郑,郑不得已而从齐。从这时起,郑就成为立于天下之中的一只风信鸡了,哪里刮来的风大,它就转向那里。因而,这时朝齐暮楚,后来朝晋暮楚。郑国的忧和喜,都从这天下之中而来。所忧者,大国竞逐,天下云扰;所喜者,巨贾齐集,百货通流。
动荡加富裕,这是郑人典型的生活。对郑国的君臣来说,利重于义,权术重于公理。
公元前648年———成王二十四年,楚灭黄。两年后,楚灭英。
英别称英氏,是一个偃姓的小国,故址在今安徽金寨、霍山两地之间。还有姬姓的蒋、应两个小国,族姓不明的樊国,以及蓼(缪)国,大概都在成王中期被楚国灭掉了。蒋,故址在今河南固始西北;蓼(缪),故址在今固始东北;樊,故址在今河南信阳。应,故址在今河南鲁山东。
公元前645年———成王二十七年,楚败徐于娄林(在今安徽泗县东)。
这样,三年之内,楚人从淮水上游进取中游,从淮水中游袭击下游,速度之快出乎中原诸侯意料。这时的成王同他的臣僚配合默契,用兵如神。娄林之役,齐又纠合了一支号称八国的多国部队,蹈袭楚师围许救郑的故智,采取围厉救徐的战略。当时有两个厉国:
西边的一个在今湖北随州,姜姓;东边的一个在淮北,其氏姓和故址都不详,同鲁国是姻亲,这时已成为楚国的附庸。八国联军所围的,当然是淮北的厉国。深通围甲救乙之道的成王不为所动,终于取得娄林之捷,而八国联军也随之解散了。
出方城而北上是文王确立的战略方针,成王奉行不替;沿淮水而东下是成王自己确立的战略方针,与出方城而北上并行不悖。楚人北上的意图和意义是容易认识的:投入文明世界的主流,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一举两得。至于楚人东下的意图和意义,就不那么容易认识了。淮水在文明世界和政治舞台的边缘,似乎无足轻重。假如说,楚人东下所追求的只是广土众民,那么,楚国的西面和南面都没有强敌,楚人为什么不像对淮水流域那么热衷呢?楚人东下总是有口实的,无非某国对楚国不友好或者不尊重之类,都是官样文章。隐藏在这些口实后面的动机,是要力求垄断长江中游的有色金属并且力争侵夺长江下游的有色金属。简而言之,楚人东下是为铜而战。楚人从东下得到的实惠,比从北上得到的实惠更大。北方的诸侯当然也懂得这个道理,否则就不会有八国联军了。
上文曾说到,淮汉之间是一个十字路口,无论从民族成分来看还是从文化因素来看,都是这样。在楚人占领以前,这个地区的文化景观五花八门,但占优势的是随、息、蒋等国的周文化。楚人进入淮汉之间,获益匪浅,主要得之于文明程度如鹤立鸡群的随国。
小国的文化对楚国也不是全无影响的,如河南光山黄君孟夫妇合葬墓是已知最早有封土的竖穴土坑墓,其封土形制对后来楚墓的封土形制似有导向作用。淮水中游和下游的文化景观与淮汉之间不同,以徐、舒为主体的淮夷文化占优势。徐在淮北而偏东,舒在淮南而偏西,彼此族类相近,文化相似。徐人贵族文化素养在长江下游是最高的,其铜器铭文结体娟秀而用韵精严。舒人的文化素养虽不及徐人,但他们的铸造技艺则不让除人。舒墓所出铜器中的牺形鼎、平盖扁鼓腹鼎、异形盉等独具特色,所出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则与越文化相通。楚人进入淮水中游,政治上与徐、舒是敌国,文化上却与徐、舒有异曲同工之妙,楚人的创造才能在竞争和交流中受到刺激和鼓舞,从此,楚文化才作为南方文化的表率而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风格。
《史记·齐太公世家》说:“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所谓“荆蛮”是广义的,楚蛮、扬越、淮夷等一股脑儿都算在里面。楚人“收荆蛮有之”,则楚人本非荆蛮;成王“夷狄自置”,则成王本非夷狄:这都其理自明。在管仲和其他许多中原人士看来,齐是“中国”即中原或华夏的盟主,楚是夷狄的大憝。然而,曾几何时,齐的盟主地位就一去不复返了。
公元前643年,管仲和齐桓公相继去世。凡倚重人治的,人亡则政息。其明年,齐国大乱,宋、曹、卫、郑合兵伐齐。是年,郑文公朝于楚成王,楚成王送给郑文公一批铜,刚送掉就后悔,而不便收回,就和郑文公盟誓,让郑文公保证不用来铸造兵器。这使我们想到,现代有些国家出售核反应堆给别国,要别国“保证和平用途”。古往今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郑文公回国后,用这些铜铸了三口钟。这时,楚国的铜产量已跃居列国的首位。有了这样的经济优势,楚国的发达和昌盛就可想而知了。
公元前640年———成王三十二年,随国串通汉东的小国背叛楚国。这是汉东诸国试图挽回往昔的光荣的最后一次尝试,结局还是失败。令尹子文一出兵,它们就求和了。成王和令尹子文以罕见的大度处理了楚随关系,一度飘荡在汉东上空的阴霾迅即消散,随侯保持了自己的安富尊荣,随人保持了自己的宗庙和制度,只是随国成为楚国忠顺的附庸近三个世纪。允许在自己的腹地保留一个在内政上高度自主的国中之国,如果不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一定不会有如此超卓的见识和如此恢弘的气度。
这时,成王踌躇满志了。环顾四周,国内和国外都没有他的敌手了。然而,偏偏有一个宋襄公出来硬充霸主,这在成王看来实在是匪夷所思,他赫然震怒了……(第三节会盟,交战,燕飨齐桓公死后,宋襄公忘乎所以,居然想继齐桓公而为霸主。宋襄公其人志大才疏,以为霸主不一定要有强兵和奇才,只要能几次邀集诸侯会盟,就算是霸主了。
公元前639年———成王三十三年,春,宋襄公邀请楚成王和齐孝公会盟于宋邑鹿上(在今安徽阜阳南)。《史记·宋微子世家》记宋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宋襄公置若罔闻。同年秋,宋襄公邀请楚、陈、蔡、郑、许、曹诸国的国君到宋的孟邑(在今河南睢县)会盟。当时的俗话说:“一之谓甚,其可再乎?”楚成王大怒,他觉得宋襄公太不识相,已经主持了一次不该由他主持的盟会,怎么还想再来主持一次呢?当时的盟会有两种:一种是乘车之会,与会的诸侯只能带乘车去;还有一种是兵车之会,与会的诸侯都要带一定数量的兵车去。这次是乘车之会,但楚成王带兵车去了。
在会上,楚成王授意随行将士把宋襄公捉住,押回楚国去,宋人一筹莫展。同年冬,楚、鲁、陈、蔡、郑、宋等国在宋的亳邑(即“薄”邑,在今河南商丘北)会盟,楚成王才释放了宋襄公。
公元前638年———成王三十四年,春,郑文公再次朝见楚成王。
宋襄公不自量力,以宋、卫、许、滕四国联军伐郑。是年秋,楚师伐宋救郑。宋师解郑围,撤到泓水附近(在今河南柘城北)。时已入冬,楚宋战于泓水,史称“泓之战”。楚师在泓水南,宋师在泓水北。楚师北渡泓水,宋大司马公孙固主张待楚师半渡而击之,宋襄公以为这样乘人之危不合作战的惯例,拒不采纳。楚师渡过泓水后,正在布阵,公孙固要求出击,宋襄公仍不接受,理由还是不可乘人之危。待楚师布阵完毕,宋襄公才击鼓进兵,焉知一败涂地,宋襄公腿上也中了箭。宋襄公的迂腐和愚钝,实属罕见。公孙固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不足为奇。论者有这样的一种意见,以为只要宋襄公采纳了公孙固的主张,宋师就会打败楚师。实则未必然,因为杰出的兵家善于出奇制胜,有时不辞作背水之战。秦末汉初的韩信和东晋的谢石,都曾创立背水作战获胜的范例。
楚师在泓之战中获胜后,成王乘兴到郑国访问。这时的楚郑关系极为热络,彼此又是盟友,又是姻亲。郑文公的夫人芈氏见兄弟成王奏凯而来,觉得十分风光,便带着郑文公的另一位夫人姜氏,出都相迎。成王喜不自胜,派乐尹师缙把楚师俘获的宋人,以及从战死的宋人头上割下的耳朵,给两位夫人过目。派乐尹办这事,是因为同时要奏乐以助兴。但这样的做法在中原人士看来,未免出格了。《左传》引“君子”曰:“非礼也!”成王和芈氏都安之若素,可见楚人对男女之别还不像中原人士那么一本正经。其明日,郑文公在宫中为楚成王举行燕飨之礼,备极隆重。据《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所记,“九献,庭实旅百,加笾豆六品”,这是最高的礼宾规格。
“九献”,即主宾酬酢九次。“庭实旅百”,即陈于庭中的礼品以百计。
“加笾豆六品”,即外加六件盛着果品或野味的笾豆。当夜,宴毕,楚成王回到城外的营帐里去,郑文公献给楚成王两位姬姓少女作妾,由芈氏送到楚营。郑大夫叔詹觉得太不像话,竟在背后诅咒楚成王不得好死。
到宋邑会盟,到郑都访问,这些都使成王增长见识,拓开思路。
楚国与中原诸国相比,除礼制外,几乎都领先了。成王对礼制建设深为关注,他要把楚国建设得“郁郁乎文哉”。
这时的成王,虽尚无霸主之名,而已有霸主之实。齐已中衰,晋有内乱,宋创巨痛深,郑俯首帖耳,诸侯莫能与楚争胜,所以说成王有霸主之实。至于成王无霸主之名,则是因为中原诸侯对楚人的民族歧视心理尚未褪尽。
公元前637年———成王三十五年,秋,司马成得臣伐陈,取其焦、夷两邑,又帮助受陈欺凌而不得不迁都的姬姓顿国营建了新都。
顿在今河南项城,旧都在北而新都在西。
成氏也是若敖的后人,得臣字子玉。令尹子文年事已高,想养老了,见子玉有功,便推荐他接班。成王从其请,命子玉为令尹。
是年冬,晋公子重耳访问楚国。重耳是在18年前因晋国公室内乱而出走的,那时只有17岁。出走之后,他先在狄国住了11年多,后在卫、齐、曹、宋、郑诸国住了6年多。狄、齐、宋三国待他以上宾之礼,卫、曹、郑三国对他都未能以礼相待。到了楚国,成王待之以诸侯之礼,重耳受宠若惊。成王飨重耳,九献,庭实旅百,这大概是向郑国学来的,《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宴会将结束时,成王问重耳:“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穀?”重耳答道:“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成王执意问重耳:“虽然,何以报我?”论财富,当时晋不如楚,重耳的答词是得体的。成王坦然承认楚比晋富,但仍要重耳说出报答的办法来,这是给重耳出了一道难题。重耳答道:
“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避)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执櫜鞬,以与君周旋。”这是一席精彩的对话,可以写进中国外交史和世界外交史中去。只用不卑不亢、亦柔亦刚之类的评语是不够的,问答双方都把话说到了边缘,重耳的答词则是自谦与自尊高难度的结合。这位还过着流亡生涯的晋公子,已显露出雄主的气象。令尹子玉建议成王杀死重耳,成王不许。子玉又建议留重耳的舅父兼谋主狐偃为人质,成王亦不许。
此后不久,秦穆公派使者到楚国来迎重耳,楚成王派使者奉厚币送重耳到秦国。其明年,秦穆公以武力送重耳回晋国。晋惠公夷吾也是秦穆公扶立的,在位14年死,继位的晋怀公子圉不合秦穆公意,因而秦穆公扶立重耳。重耳杀晋怀公而自立,是为晋文公。
秦穆公是一位很有政治野心的明主,平素留意选贤养士,推诚礼贤下士。晋灭虞,获其大夫百里傒,以为秦穆公夫人的媵臣。百里傒逃亡到楚国的宛邑,被守边的楚国将士捉住。秦穆公听说百里傒是贤人,派人探听到他的下落,要把他接回秦国去,但怕楚人不放。于是,派使者到宛邑,不说百里傒是贤人,只说他是逃亡的媵臣,用了五张羖羊皮即黑色公羊皮,就把他赎了回来。秦穆公随即任之以政,人们给百里傒起了个外号叫“五羖大夫”。
(第四节令尹子玉
公元前635年———成王三十七年,秋,秦、晋伐鄀。鄀是介乎秦楚之间的一个小国,早已成为楚国的附庸。鄀都商密,故址在今河南淅川西境。秦、晋与楚,在上一年里还玉帛相通,这时突然干戈相向了。秦是伐鄀的主谋和主力,晋只起着张掎角之势的作用。
即位才2年的晋文公,为了报答秦穆公,不惜背弃楚成王。其实,晋文公并不真要报答秦穆公,只是无法拒绝秦穆公要他出兵相助的要求罢了。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它决定着战争与和平。
楚国在方城内外有申、息两个大县,申公和息公是守卫国门的封疆大吏。这次秦、晋伐鄀,楚人起初不甚在意,以为只是寻常的边境冲突,令尹和司马都还在郢都,只派申公斗克和息公屈御寇以申、息之师去戍守商密。秦师抢在楚师到达商密以前,沿着丹水的大湾绕过商密。到了靠近析邑(在今河南西峡)的地方,把自己的役徒捆绑起来,冒充析人,押着朝西走。在暮色的掩护下,秦师包围了商密。入夜,秦人燃起许多火炬,在火光中杀牲取血,伪装与申公、息公盟誓。鄀人从城上见到这般情景,以为自己被楚国出卖给秦国了。一传十,十传百,无不信以为真。于是,鄀人向秦师请降。秦师随即东进,突袭正在途中的楚师。申公、息公疏于戒备,都成了秦人的俘虏。秦师怕楚师的大军追来,匆匆离开商密,回秦国去了。令尹子玉闻变大惊,当即发重兵追秦师,未能追上。子玉不自安,为了以功补过,引兵伐陈,同时把正在楚国避难的顿子护送到顿城,才收兵回国。
析之战是秦、楚两国初次交锋,秦之胜在于诈,楚之败在于骄。
楚国丧失的兵员不算多,可是两位县公被俘对自己的国间形象有损。假如楚人从初次与秦人交锋起就注意总结经验,以诈制诈,此后是不会重蹈覆辙的。无奈楚人计不出此,对秦人总是宁信其诚而不信其诈。乃至323年之后,在离商密不远的丹阳,吃了更大的败仗。
公元前634年———成王三十八年,齐一再伐鲁,鲁不胜其扰,鲁僖公命公子遂和臧文仲向楚求援。臧文仲多谋善言,对子玉说齐、宋两国“不臣”,自请为楚做伐齐和伐宋的向导。子玉被臧文仲说动了,但他要先去处理另一件大事———灭夔。
夔是楚的别封之国。始君为熊渠次子熊挚,故址在今湖北秭归,土著是巴人。夔子已经巴化,而且认为楚国歧视夔国的先君,于是拒不祭祀祝融和鬻熊。《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楚国派使者去责问夔子,夔子竟说:“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这虽是牢骚,但分明自外于楚国了。楚国不能容忍夔子公然闹分裂,搞独立,决定予以严惩。是年秋,令尹子玉和司马子西(斗宜申)引兵灭夔,夔子被押解到郢都去。从此,夔国就不再存在了。
灭夔后,子玉可以腾出手来去惩罚齐和宋了。这时,成王显出了倦于国事的迹象,由子玉执政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