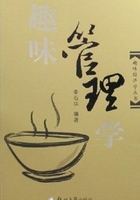现在和过去不同了,因为是全球化带来工商业的发展,这个使农村多余的人口可以进入城市,可以进入一个新的生产体系,当新的生产体系在整个经济中占的比重超过一定数额,就诞生了一个新型社会,它就是工商社会。这个社会中人们处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中,各有各的利益。
所谓社会“断裂”与我所说的“脱序”还是有所差别的。我说的“脱序”是指一部分人脱离主流的社会秩序的控制;孙先生说的“断裂”大约是指不同阶层群体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别越拉越大。其实“断裂”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断裂”是不可避免的,例如资本家和工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官员和民众,以及不同的民族职业之间,我们都眼睁睁地看到它们之间的利益是如何从差别不大,发展到差别极大的。这其中有的是经济发展使然的,有的是用政治手段谋取的。利益差别推动了利益群体的形成。谁的利益都要靠自己去争取,谁也别指望别人代表自己,正像自己的银行存折不能由他人代取一样。重要的是利益群体之间如何在合法的条件下通过互相博弈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样才能使社会“裂而不断”,使之处于一个共同体中。我们常说的法制社会,就是指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博弈的社会,在遵守法律下博弈,在博弈中使得断裂有所敉平,从而求得社会稳定,这才是真正的稳定。真正的稳定是动态的稳定,不是静态的稳定。如果不是博弈而是抢夺,是革命,是暴力,蔑视法律,毁灭安定时期的经济、文化、人口的积累,这是追求静态稳定的结果。
14.如何穿越历史迷雾?换句话说,在追寻现代化的历程中,应该怎样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当代社会治理良方?从历史的人治到现代的法治,是不是还可以寄望于某种德治?法制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法治硬制度辅以德治软制度是不是走向民主、和谐社会的可能的理想路径?
总的说来,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不适用于当前社会的转型。中国是个文化资源特别丰厚的国家,然而,我们传统的政治文化是宗法和皇权(皇权本质上也是从宗法家长制延伸出来的)的产物,它的经济背景是农业文明。虽然说中华民族的农业文明是地球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发展得最完善、最细密的,但它基本上不适用于未来的工商社会。例如儒家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它是注重处理伦理关系的。然而它所倡导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所处理的五伦关系都是熟人社会的问题,而工商社会所面临的大量的是陌生人的问题,是见过一两次再也见不到的人,这是“第六伦”的问题。对于萍水相逢的人如何对待、如何约束,出现问题如何处理,这些都在儒家思考之外。儒家注重人治,不重法治,如果让儒家治理一个一两万人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小国,其效果可能不错。
它用不着什么法治,大家都有亲戚关系,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讲道德、讲团结就可以了。正像治理家庭(包括家族)不必完全依靠家庭公约(建国初,治国不重法治,治家却要求家家订立“家庭公约”)一样。其实从春秋到战国,已经走到了陌生社会,儒家不为统治者所用其根子在此。秦大一统之后,儒家以不适用不被重视。然而中国古代是小政府、大社会的(生产力低下,大政府也养活不起),民间社会多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儒家讲究亲情、仁爱,其思想内容较适用于民间社会。因此,尽管到了大一统社会,聪明的统治者还是打儒家招牌,以博取民间社会的认同。后来的儒者,也尽量修正原始儒家不适合大一统和皇权制度的思想,以适应皇权专制的需要。“德治”实际上只是人治别名,人治的理由就是把统治者都看成圣人,都是有德之人,只有在这群有道德的人的统治下,人们才会过好日子。
如果实施民主,把一群流氓坏蛋选了上来,人民就要遭殃。在讲德治的人们看来,用“法律”统治,人人都懂得“法”了,则限制了统治者道德的发扬,再说法律那么烦琐谁记得住,用法治实际上给了律师讼棍金饭碗。古代说的“法”(是惩治人民,使之不敢违法的手段),还不是现代社会的法(现代法律是界定人们的权利与义务的,是调节社会关系的),还受到儒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君子德风,小人德草”,只要统治者道德高尚,民众的品德也会水涨船高,那么整个社会就安定了。然而,所有的政治实践都说明,道德是自律,是不可靠的,没有制度化的约束,对“好统治者”的期待,不仅是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往往落空。最近小国不丹由国王主持的民主化,国王也向人民讲述了这个道理。法律是强制人们遵守的,道德是要靠宗教、哲学和与之相关的修养来实现的。道德要靠舆论监督,它在熟人社会才能发挥较大的作用,至于陌生社会是要靠法律协调的。
法律只能解决人们犯不犯法的问题,法律公开,以及执行法律的过程中透明公正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保障。但是社会的和谐的根本还在于经济的发展,人们吃穿不愁,贫富差距不大,在物质保障的基础上,人们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有一定的精神和心灵生活,从而激发人的善性,这样,社会才会和谐起来。实现民主制度也是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因为和谐是建筑在差别、多元基础上的,而民主是承认多元的,而威权和极权都是从里到外强制一统的。
谈到历史经验,我认为有两条是特别应予注意的。一是社会善恶都是由人性的善恶引申出来的,如果承认作为人类总体的人性是不可能彻底改变的,那么我们就不要期待有个十全十美的社会出现,也不会有永久覆盖全人类的丑恶。儒家在社会追求上是聪明的,他们视大同社会为理想社会,但大同只是批评社会弊病的标尺,不把它当做实现理想的蓝图,历代儒者亦只以小康为追求目标,只有康有为那样的妄人,才张扬要在人间实现大同。他的追求幸亏没有实现,要实现了就是波尔布特式的共产主义。其二是中庸。这是孔子再三强调而中国人又很难做到的。因为小生产眼光和心胸、知识水准低下都容易造成狭隘和极端,历来给国家人们伤害最大的就是极端主义。而且不管左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把全社会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15.另外,我还注意到您的文论、随笔集《发现另一个中国》,您提出中国历史“有一个贱视民命的传统”的论断,比如有权者的“草菅人命”,无权者的“杀无赦”。您不妨对这个残酷的传统稍作演绎,作为对游民文化的某种背书。
上古,人类只承认自己和自己亲属是人,对于战后的俘虏、奴隶等是不承认他们人的地位的。从殷墟大量的殉葬便可得见,直到墨子还说“杀盗人非杀人也”。只是到了孔子才把同类意识告诉民众。所谓“仁”的精义也就在于认识到自己是人,他人也是人。然而“孔子西行不到秦”,秦统一中国实行的是“与民为敌”的法家路线。民众在法家眼中只是耕种和打仗的活工具,除此,他们没有存在的价值。每个人在法家政治家的心目中都是需要提防的坏蛋,不提防就会制造混乱,夺取君主的位置。到了汉武帝时期,虽然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其本质仍是外儒内法,儒家只是个好看的招牌罢了。其实不管尊奉什么学说,只要实行专制统治,就必然是敌视人、蔑视人的。皇权专制确立了,不管有多么好听的名目与制度(例如死刑要三审,最后由皇帝勾名、秋后问斩等)都不能掩盖制度本身对于生命的漠视。在后来形成的游民文化中,对于他人生命漠视,对于自己生命的贱视达到极端。生命对于他们就是苦难,可留恋处甚少,在这种状态下形成了他们“活着干,死了算”的生命观。希望通过这次地震巨大的灾难,人们能够有所反思,重视和爱护生命。
流民、游民与社会动荡
此篇发表于笑蜀、蒋兆勇主编的《公民社会评论》第1辑,发表时题目为《公民社会才能把无根变为有根——王学泰访谈录》。杨子云女士是该刊特约记者,于2009年3月到舍下采访。
流民狂潮使中国文化短命
记者:您是研究流民问题的专家,我注意到您对流民和游民有不同的定义,根据您的理解,什么是游民?什么是流民?流民和游民又是什么关系?他们产生的共同的文化根源是什么?
王学泰:凡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没有固定的谋生手段,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的手段取取得生活资料的人,都可视为游民。他重要的特点在于“游”。他处在社会最底层,只在动荡时代才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所以他不理会秩序,反而欢迎冲突,甚至欢迎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
而我说的流民,是指离开故土,但可能没有脱离社会正常秩序的人。比如,大规模的天灾人祸都会导致大批农民脱离自己的土地,少则成百上千,多则数万甚至数十万,在有领导能力的“渠魁”“渠帅”的带领下就食于富庶地区,许多人是整个家族和宗族做大规模的迁移,家族的宗法秩序没有被破坏,只不过是举族或全家换了一个地方罢了。这样的流民就不同于完全脱序了的游民。但流民没有被安置好就极可能变成游民,他们脱离了“流”,进入了城市,成了混迹社会底层、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游民;或者闯荡江湖、冲州撞府过着漂泊不定的游民生活。
记者:可见,在您的概念中,流民和游民是紧密相关的,他们之间是一个水涨船高的关系。
王学泰: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有个前提,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组织方式是宗法社会,从经济、经营角度来说是小农社会,人一生基本上就像一棵树似的长在某地,一动不动地生活在他的家族、宗族之中。中国的统治者,最希望老百姓不动,这样他才有安全感。农业社会基本上是个静态的社会,专制统治适于统治管理这样的社会。古代的中国除了是小农社会外,其社会自发的基层组织又是宗法制度。在宗法制度的网络中,统治者依靠强大的宗法网络,把每个人都编织进去。这个网络就是秦晖所说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对自己的成员是既保护又控制。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
记者:宗法统治似乎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治乱之间,似乎往往还能休养生息个百来年,这是什么原因?中国历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轻易不乱,一乱就山河变色。而在这些山河变色的大乱中,造反的主力都是流民。朱元璋的军队、李自成的军队,都以流民为主。
王学泰:应该看到,中国古代的皇权专制社会和宗法社会是同构的,每一个家族都是一个小国。所以说一个好的皇权专制社会,它就比较不太管社会上的事,是让你自己自治,宗法自治。在中国古代,一个好的王朝能维持二三百年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它统治成本很低,它不必对农民过度剥夺。但这种稳定是静态的稳定,是以人口不发展、没有天灾人祸为基础的,但我们的历史总是50年一小乱,200年一大乱。这些动乱的作用是什么呢?说起来很残酷,就是消灭人口。通过战乱屠戮人口,每次战乱都把人口降到一半。然后一个新的朝代建立起来了,人口比较少了,每个人都能有一小块土地了,重新建立小农制度,还有在小农制度上的宗法体系,这个社会也就基本稳定了。社会随着人口的发展,过200年以后又开始这样的治乱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