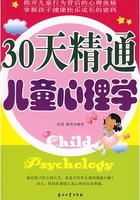吃完晚饭我们回房歇息,但是珍妮还没有松懈下来。性爱已经成了她和我爸妈之间的一颗隐形炸弹。不过这也不能怪珍妮。结婚之前,这事曾经是我俩备受责难的原因,曾经被看做是让家族蒙羞的龌龊秘密。而如今却让我们在爸妈的床上做爱,四周还有圣灵、天使还有教皇在看着;而且,我那做神父的舅舅就在和我们一墙之隔的房间里休息!珍妮钻进被窝,攥着被褥的一角,睡得离我老远。爸妈睡的是加大号的双人床,她紧贴着一边的床沿,我俩中间恨不得还能睡下六七个人。我从床的另一边悄悄地挪过去,靠近她,把腿搭在她的腿上。“别碰我。”她又重复了一次,那口气仿佛在说:别得寸进尺了。
尽管如此,我想我还是要采取点措施来缓解一下家里的紧张气氛。我坐起来,开始上下左右地摇晃身体。先是轻轻地、慢慢地越来越用力。床架被我弄得咯吱作响,弹簧也开始发出 “噔噔 ”的声音。接着,那串巨大的念珠开始敲击床头,“嗒——嗒——嗒——嗒……”珍妮也应该觉得我的做法相当搞笑。在我爸妈这间充满了宗教氛围的房间里,我们这对新婚夫妇并没有巫山云雨却弄出很大的声响让别人以为我俩正男欢女爱、如胶似漆。真是太搞笑了!我期待着珍妮随时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可是她始终也没有笑,甚至没有偷偷地笑或是看我一眼。出乎我意料的,她立马下了床,那速度就像是被东西烫着了一样。于是,我也赶紧下床,好说歹说地劝了她半个小时,让她放弃了半夜就回佛罗里达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最后终于把她哄回了床上。那晚我俩睡得井水不犯河水,两人之间至少隔了一米宽。
第二天早上,匆匆和家人告别之后,我们俩就开车上路了。车子的后座和后备箱塞满了新婚礼物。直到我们快到乔治亚州的时候,珍妮才算是消了气。她生气不单单是因为我搞的那个假装做爱的声音,更主要的是因为在她和我妈产生分歧的时候,我站在了妈妈那边,而没有向着她。我郑重向她保证,她再也不用睡我爸妈的床了。
婚后一回到佛罗里达,我们就开始四处寻觅一处属于我们俩的爱巢。以前租住的小屋其实也不错,但是现在毕竟不同于往日了,我们渴望找到一个地方安定下来。婚姻带给我们彼此的不仅仅是一种安全感和持久性,更让我们觉得踏实。之前我和珍妮一直坚信,我们根本不需要一纸婚书来约束彼此,婚礼只不过是个形式,然而等到真的结婚了,我们却都很惊讶婚姻竟然给我俩带来如此巨大的转变,当然是往好的方向转变。从相识到现在,我们俩头一回意识到,对方不会离开自己了,不会因为新的工作机会或者奖学金而独自跑掉了。这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两个人共同的生活。就算是用它作抵押去银行贷三十年的按揭贷款也不会觉得害怕了。
在一个街区外一条更漂亮的街道上,我们发现了一间待售的小公寓。跟我们的出租小屋不同的是,这间小公寓有一片精心护理的茂盛的草坪,周围还种着许多热带植物。当我和珍妮有一回晚上散步,途中一眼看到这间公寓时,珍妮深吸了一口气:“这儿太完美了,”她甚至都没往里面看一眼就下了结论,“必须把绿色的漆换掉,不过无论如何,真不错。”
几周后,我和珍妮带着房产契约和前门钥匙走出了银行—— 直奔我们的新家:丘吉尔路345号。车刚一驶到门前的车道上,珍妮就跳下来,拿着钥匙朝大门冲过去。
“噢,不!等等!先别进去!等等我!”我在她后面喊道。我想让事情更浪漫一点。我在门口抓住她,从她手里抢过钥匙,捅进锁眼,开了门。然后,一下把毫无防备的珍妮搂进怀里,把她抱了起来。她发出一声快乐的惊叫。
“你这个坏蛋!”她一边嚷着一边用手抱住我的脖子,“你想干嘛?”“你马上就知道了,”我告诉她,“这是我们迈进新家的第一步,也是迈进新生活的第一步。”我一边说着一边抱着她穿过门廊。进了门,我们俩都安静了下来,静静地陶醉着。
“现在可以把我放下来了吧,”珍妮说道,“别伤着你自己。”
几个月过去了,我们把这个小公寓彻底变成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风格。不仅重新粉刷了墙面,挂上了海地艺术品,还卷起了粗毛地毯,露出了底下闪着光泽的橡木地板。我和珍妮种了个小花园,还带回家一只活泼好动的小拉布拉多寻回犬,并取名马利。马利很快赢得了我们的喜爱,尽管每天都要闯祸。从卧室的窗户向外望去,能看到一片栀子花丛和一棵巨大的巴西胡椒树,有很多野鹦鹉在树上筑巢。每天早晨,我们都在鸟语花香中醒来,生活真是再惬意不过了。
然而和父母之间的矛盾仍然困扰着我。我佯装婚前所有的不和睦都随着天主教婚礼仪式的进行而消失,然而伤痕却日益加深。珍妮始终忘不了我父母的主观臆断,尤其是我母亲曾经情绪化地预言我们的婚姻注定走向失败。以他们的道德标准,他们骄矜、有着一种优越感,他们一直祈祷自己的儿子能找到一位优秀的天主教妻子,而像珍妮这种没有明确的信仰的人是劣等的,根本不符合标准。珍妮深信,我的父母责怪她让我远离了自己的信仰。“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你的滑铁卢。”她不止一次地这么说过。
我的父母也不好受。我迟来的诚实、我对他们价值观的反抗、珍妮对他们信仰的那种掩饰不住的蔑视以及我对这种蔑视的默许,使他们深深地受伤了。他们关于天主教义的那些中古世纪的解释,包括相信真的有守护天使盘旋在我们肩头以防止被撒旦的使者们伤害,在我和珍妮看来就是一些可笑的迷信说法。区别只在于我是从小听着这些长大的,所以并不以为然。而珍妮则不同了,她丝毫不能掩饰对这些荒唐说法的惊奇。对她而言,这都是些吓唬人的把戏,和往肩膀上撒盐保佑好运的做法没什么两样。对于我父母五花八门的教义解释,她是又好奇、又迷惑,通常是做个鬼脸奉承两句。但是我知道,我父母把这理解为嘲笑。在他们眼里,她的不舒服就是不敬。
我还记得和珍妮交往没多久之后,她第一次去我父母家的情景。妈妈把她堵在厨房里,然后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贴着手写的标签的小玻璃瓶。噢,不要,我心想:“她怎么把圣水拿出来了!”我眼瞅着她把瓶盖打开,走近珍妮。快放下啊,妈妈,快把它放回围裙里。你太不了解这个女孩了。连一句解释的话都没有,妈妈就用瓶里的圣水浇湿珍妮的拇指,并在珍妮的前额上划了个十字,然后叨念着“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爸爸则赞许地看着这一幕。就像他们做的其他事情一样,这次也是出于善意的。他们想以这种方式来祝福我们家未来的新成员,希望主能满意我们的结合。即使我妈妈骑上扫帚脚一蹬就飞走了,珍妮也不会感到更震惊了。“都是一些守旧的天主教徒才会那样做。”这是我后来才告诉她的,不过那个时刻为以后的许多事情定下了基调。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在我意志坚定的妻子的帮助下,我终于彻底从父母的影响下脱离出来了。从此不必再撒谎,也不会再混淆事实了。我现在无可争辩地自由了,正式地成为“非职业天主教徒”了。但是自由的获得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好像我和我父母之间横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玻璃墙。我仍然能透过玻璃看到他们、听到他们,但是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看到和听到。我们避免谈及宗教、政治或者像堕胎、同性恋者的权利这样的社会问题——任何一个热点话题都有可能暴露出我们之间价值观上的尖锐分歧。他们不问,我也不提。他们再也不会滔滔不绝地讲述教堂里最近组织的祷告活动,也不再拷问我有没有做周日弥撒。他们所保持的信仰和我对这一信仰的放弃,成了我们之间交谈的禁忌话题。即便阴影总是萦绕在我们彼此的心头,让我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压抑,我们还是假装无视它的存在。
最主要的一点,我想他们已经意识到遇到了劲敌——珍妮,他们要么不吭声,要么就得冒着彻底失去我的危险。如果我妈妈是小拿破仑,那么珍妮一定是她的滑铁卢。妈妈似乎明白自己赢不了这场战争——在不失去她儿子这片领地的前提下。
很快就有了另一件他们不想冒险失去的即将来临的战利品。珍妮怀孕了。一想到快要有一个孙子了,他们就兴奋得无以言表。当珍妮第一次怀孕以流产告终,他们和我们一样悲痛,尽管他们把它归因于上帝的神秘计划。很快,珍妮又怀孕了,然后在1992年5月,我们把小帕特里克·约瑟夫·格罗根从医院带回了家。我们为他选取了和珍妮的父亲相同的中间名,同时我也很自豪地使我的父母相信我是在遵循他们“玛丽和约瑟夫”的取名传统。一周后,珍妮的父母来和我们住了十天,这期间我们过得非常轻松愉快。我的岳母包揽了全部的家务活,每天都是我去上班,珍妮和父母带着孩子出去溜达——超市、日式花园,甚至还去过海滩,在那儿珍妮会坐在阴凉处为我们刚出生的儿子哺乳。
珍妮的父母走之后过了两天,我的父母从亚特兰大以外的一个露营地打来电话,他们前一天就驾车到了那儿。现在正在来探望我们夫妻和孙子的路上,但是他们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去科尼尔斯的一个农场朝圣。科尼尔斯是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东面的一个小镇。传说圣女玛丽显灵的事就是那个农场的主人报告的。天主教教会并不赞同这种所谓的“亲眼所见”,然而这个农场主妇的话却足以糊弄我的爸爸妈妈。
“圣母告诉我们,如果想要有希望就要祷告。”妈妈说,然后她把电话递给了爸爸。这时我更明白他们前往所谓的奇迹发生地做朝圣之旅的原因了。爸爸肯定有事情要宣布。帕特里克出生那天,爸爸的医生检查出他的前列腺长了肿瘤。从我家一回去,他就得安排做放射治疗。他跟我保证说,医生有信心把他的病治好。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我问道。
“你第一个孩子才刚刚出生,”他说,“我不想扫你的兴。”
“我不想让你们瞒着我,爸爸,”我说,“无论是什么事,不管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一定要告诉我,好吗?”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爸爸说。
第二天晚上,当他们好不容易停好他们的旅行车下来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看起来都苍老了很多,比我几个月前见到的他们更孱弱。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愉快地驾驶着那辆“流动的家”——雪佛兰小卡车游遍了整个国家和墨西哥。不是观光就是串亲,或者去圣地朝拜。但是现如今我看到的却是他们紧张的神情和疲惫的身影。他们七十六岁了,行动日渐不便,长时间的奔波劳碌已经是他们所不能承受的。我悲哀地意识到,他们的旅行生涯即将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从两年前我和珍妮决定同居到现在,这是我父母第一次来看望我们。我希望别出什么岔子。然而他们刚一踏进家门我就感觉到了珍妮的警惕性在激增。每当我妈妈摇动孩子的摇篮或者温声细语地逗孩子,珍妮都会像母鸡护着小鸡一样守在一边,显得相当不安。晚饭后,她把我堵在了厨房。
“听着,”她低声说道,“我可不想让你妈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实施什么秘密的家庭洗礼。”我觉得她的担心实在很荒谬,但是也不是没有根据。在我妈妈还是中学女生的时候,她就曾经为她看护的那些非天主教小孩做秘密洗礼。就是在长大以后,她也觉得自己当初做的很对,还兴致勃勃地讲给我们听。她从小就被灌输了一种理念,即普通的天主教徒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以实施紧急洗礼。在她看来,这是在拯救那些孩子,使他们彻底远离地狱边境,即天堂和地狱之间的永久等待室。修女们曾经告诫过我们,那儿是全世界数百万的异教婴儿的最终归宿。珍妮也听过这个故事,既然有了自己的孩子,她一想到自己的婆婆有可能背着自己对孩子实施秘密宗教仪式就烦躁不安。
“没人会给帕特里克做秘密洗礼的。”我安慰她说,但我敢说她根本不信。她是不会让帕特里克离开她视线一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