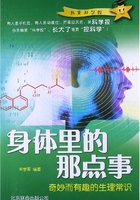母亲说:“是你和叶子让我变得怯懦、自私。”
“你总算有了一个完整的家,能和亲生父母一起生活了。你每天起床、穿衣,在屋檐下刷牙、洗脸,坐在小桌边吃饭……只要你在屋里,我的视线就没离开过你。你那变长了的脸颊,变宽了的嘴巴,越来越顸的嗓音,越来越深沉的目光,那一头越来越像你父亲的硬蓬蓬的头发,耳轮和嘴唇上白乎乎的茸毛……让我压抑不住爱怜的心情。在你拿上书准备出门的时候,我拉着你的手,把你拉到我面前,用严厉的目光审视你,把你的裤腰提展,给你扣上敞开的第二颗纽扣(我知道出了门你会把它再解开)。其实那会儿我很想把你搂在怀里,在你脸颊上亲一口。知道吗?儿子,你那疙疙瘩瘩长着紫红青春痘的脸蛋对我是一种诱惑,让我很难抵御。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多么离不开你。是你和叶子让我变得懦弱、自私。让我感到害怕,感到自己的软弱。我不再那样高傲,不再那样目空一切,自命不凡。如果说从前我曾经有过远大的抱负、宏伟的理想,现在我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你和叶子才是我人生的真正意义。
“如果不是你站在我面前,垂下头,眼里包着泪水,我是不会答应你娘到咱家来的。我不想让她再搅和到家里来。说我自私也好,缺德也好,我都不在乎。只要让你有个父亲,有个完整的家,我什么都不在乎。
“她在我眼前一出现,一股妒火就冲上我的头顶,我咬紧牙关才能面对她。她站在廊檐下,手里提着一个布帕,里面兜着十几个鸡蛋,臂弯里挽着小包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像从前一样,脸上带着笑,一副宽厚的样子让我浑身发冷。不知是害怕、嫉妒,还是羞愤、烦乱,只觉得嘴唇发干,喉咙发堵。我扭头看你一眼。我看出你和她串通好了,她到这儿来肯定和你商量过。
“春如,我来给你招呼孩子吧。给你做个饭,收拾个家务……反正我一个人,挣不挣工分无所谓,农忙时候回去,队里给点口粮就行了。
“我一时猜不透她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你看着我,你的眼神紧张,眼窝发红。我张着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你用手指碰了碰我的手,我的心一下子软下来,脸上现出笑容,说出的话连我自己也感到意外。
“兰姐你能来,真是太好了。文昌早说让我请个保姆。长安上了高中,课程更紧。叶子在幼儿园,我下班晚一点就没人去接她。把这个家交给你,我和文昌都放心。……虽说不是外人,我也不能让你白劳动,我会按月给你……
“你又用手指碰了碰我。我打住话头接过她手里的包袱,把她迎进屋。
“她把包袱一放下就拿起笤帚干活。她的身影在屋里转,你在她身后跟着。她一边干活一边和你说话,你俩那亲热样子让我没法忍受。当时我就后悔了。刚才不该那样软弱,你用手指碰我一下我就爽快答应了。人一进来,想送走就没那么容易。
“我站在屋里看着她的背影,看着这间房子。这是你爸和我结婚时租下的。从前是货栈。临街一面安着栅板门,透过门缝,能看见街上闪过的人影。从这儿往下是码头,曾经是全城最热闹的地方。现在河水一年年退去,河里没了船,码头已经荒废,昔日的商行都关了门,窄窄的街筒冷冷清清,店铺都成了住家户。我选中这处房,因为它带着阁楼;还因为它让我想起1947年随着大军进城的情景。我背着背包,扛着步枪,斜披着子弹袋,走过浮桥,沿着石砌的埠头往上走。踏上故乡县城,看到街两厢的商行,我周身热血沸腾,眼睛灼灼放光。那时这间商行门头上挂着‘和盛杂货’的横匾,门口石阶上站着两个看热闹的伙计。而今牌匾没了,屋檐下还留着挂匾的铁钉。钉子粗大,翘起的钉盖像两片树叶。没想到它现在会成为我们一家安身的地方。”
母亲没说这处房子隔壁就是永康商行。以我的想象,她对这处房子的感情,跟隔壁的院子不无关系。在母亲心里,永康商行是她少女时代的一个梦,在她的人生中有着抹不去的神秘色彩。如果不是阴差阳错和父亲相识,一同走过流亡年月,她本会成为那座院落的少奶奶、女主人的。和城里大多数商户一样,两家相邻的店铺屋顶连着屋顶,山墙挨着山墙。我不知道从前的永康是什么模样,现在这里只是一个大杂院。临街住着一对孤寡老人——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永康昔日的主人。他们佝偻着身子坐在木椅里。栅板门窄长的门扇掩着黑黢黢的屋子,门前常有一片混着米粒、面屑的污水。这座院子像县城大多数宅院一样被政府改造过,它已经不再属于原来的主人。从旁边的过道进去,两进院落住着六七户人家。油毛毡搭建的厨棚贴在厢房窗下,把院子分割成一些小旮旯。低头躲开碰在脸上的晾衣绳和电线,走进院子深处,听到轰轰隆隆的机器声。街道轧花厂占据着这座院子最大的一栋房子。前廊和门窗已经拆去,棉絮、灰尘覆盖着房梁和墙壁,窗户上挂起灰黑的絮条。几个捂着口罩的人在里面忙活。从这座大杂院走过,我没法想象它昔日的光景。现在母亲就住在曾经是未婚夫家的隔壁,不知道她心中会有怎样的感慨?
“打量这间房子,看着你和叶子的两张小床,我心里更后悔。房子虽然不大,四口人住得很安稳。我和你爸在楼上,你和叶子在楼下,她来了,把她安置在哪儿?好端端的一个家,添一个人事儿就多了。
“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没等我说话,你娘把包袱拿起来,走到厦屋门口,探头向里望着说,我在这儿支个铺吧。
“这半间厦屋是货栈的套房,我们搬来后,在里面支起锅灶,放些柴火,用它做了厨房。
“让你住这儿哪儿行啊?
“里面宽绰着呢。把柴草收拾到过道里,支个床,不耽误做饭。
“我在心里感叹,兰姐到底是兰姐,她做什么事都这么有纹有路。”
黄昏临近,天空聚起厚厚的乌云。一阵雷声响过,大雨刷刷落下来,一会儿工夫,雨水在街筒里漫流,阶下水沟里响起淙淙的水声。
和母亲结婚后,父亲把户口转回县城,在菜园里干活。摆脱了娘的管束,他现在心情很开朗,气色也很好。他脖子周围经常套一副垫肩,脚上穿着胶底解放鞋,担着粪桶忽悠忽悠穿过闹市,一边走一边神气地喊着,借光!借光!他不但能随便翻弄自己的书,想读什么读什么,还弄了几个笔记本,时常伏在小桌上,记下他研究渔业养殖、蔬菜生产和政治经济学的心得。他还到寄卖店去买了一台旧收音机。雕花木壳,镀铜旋钮,虽然夹杂着嘶嘶啦啦的杂音,可那是一台真正的电子管收音机,不但有中波,还有短波。摆上这么个物件,屋里顿时显出了品位。父亲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脱掉脚上的解放鞋,换上木拖,咔嗒咔嗒,走到后门口,把带着人粪臭味的鞋子放在屋檐下,让它吹吹风。然后转身走到桌边,打开收音机,哇啦哇啦的音乐声一响,家里热闹起来,暗淡的光线立马变得明亮。
随着一阵嘭嘭的雨声,栅板门猛然推开。父亲吧唧吧唧跺着脚,把头上的草帽摘下,在门口甩甩水,再把身上的油布解下来,向门外噌噌抖。当他转过身正想说话的时候,看见娘站在屋里,他愣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像木雕似的凝固了。
娘用嗔怪的神气看着他,不客气地说,你眼睛瞪那么大干啥?不认识我了?
“兰姐想来给咱们招呼孩子,操持家务。
“你爸坐在小凳上,换上木拖。你娘把他脱下的湿鞋掂到门外,给他打来一盆水,泡上毛巾,把香皂拿过来,放在他面前,叉手站在那儿看他洗。
“我偷眼看你,你嘴角露出一点称心的笑意。我心里又是一阵翻腾。
“你可以说我狭隘,说我不通人情,可自从她来到咱家,我的心情就没法平静。我得承认,兰姐做饭、做家务比我强。无论多么简单的饭,她总能把它做得很精细。她擀的面条又筋又长,放几棵青菜,吃起来很有味道。每顿饭还要摆几碟小菜。调辣椒,调芝麻叶,小葱拌豆腐,从乡下带来的酸腊菜、咸红薯梗、干萝卜丝……她做饭很精心,手里做着针线,小闹钟摆放在身边,把按时按点开饭当作她的责任。我不用再到学校食堂去,你也可以每天回家。你跨进家门,饭已经摆在桌上。你回家晚了,她会给你盛上两碗,一碗让你吃,另一碗摆在面前晾着。
“早晨我还在洗漱,她已经给叶子洗完了脸。她坐在椅子里,叶子坐在她面前小凳上。她理着叶子的头发,操着梳子一边跟她说话一边给她梳头。叶子摆弄着自己的手指,嘴里哼哼唧唧唱歌。下午四点半,她准时到幼儿园去接她。叶子蹦蹦跳跳走,她在后面喊,看路!小乖!看着路!
“说实话,如果把她当保姆看,她是个难得的好保姆。有她在,我省了很多心,家里也比从前干净、整齐,井井有条。可她把家务做得越好,对你和你爸越周到,对叶子越亲,我心里越不舒服。
“我忍不住对你爸说,看起来兰姐才像这个家的主人,我倒像客人了。
“他哼一声,冷嘲热讽地说,不是你叫她在这儿的吗?
“还不都是因为你那儿子!我不留她,长安还不恨死我?
“那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她喜欢孩子,和孩子在一起她高兴。孩子也喜欢她。有她招呼,咱们都省心。你也不那么累了。
“其实我心里明白,她到城里来,于大家都好。她一个人在乡下孤孤零零,不要说你放不下,我和你爸也会觉得于心不忍。可我真的太自私了,有时候脑子里会闪出一个念头,觉得兰姐这人很可怕。她的心很宽,手段很厉害,我斗不过她。你本来就是她养大,和她感情很深,叶子现在也正慢慢地被她俘虏,你爸和我,在她面前是两个忘恩负义的人,永远没法挺起胸膛和她说话。往后的日子还长,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一直忍受下去。”
娘到城里来我当然高兴。虽然她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可有她在,这个家让我感到温暖。
娘问我,和那女孩儿还来往吗?我摇摇头。想她吗?我笑了一下。娘拿手在我头上抚一下。娃儿,人有时候就得忍住点。忍一下就过去了。
其实我一直在忍,不忍有什么办法?我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忍”字。可这个字反而成了一个符号,仿佛它就是张丽娅的化身,看见它我就会想起她。
我回忆起父亲和我坐在河边的情景。那时我们刚搬进这座房子。打扫收拾了半天,把床支好,东西放好,擦干净桌凳,父亲拿上一条毛巾说,咱们下河去。在河里游过一阵,擦干身子,穿好衣服,父亲和我并排坐在河岸上。河里有几只水鸟,一边啄食一边机灵地看人。一缕细烟在父亲腮边缭绕,随着他的声音飘动。
安,我年轻时也相信爱是无条件的,可现在我知道爱情是无情的,一场错误的爱情会让你付出一生的代价。最可怕的是,爱让人头脑发昏,错不错当时你根本不知道。他扭头看着我的脸,轻轻吐出一口烟雾。儿子,有很多事情你长大了才会明白,可等你明白,已经晚了。
父亲的话像火盆里的柴末,在我心里慢慢燃烧。他吐出的烟雾熏痛了我的眼睛,让我憋闷难受。
不要恨你妈妈,也别恨那女孩儿的爸爸。做父母的哪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你知道张丽娅的家庭吧?我从年轻起就反对门当户对,现在也不羡慕权势、地位。可你爸我现在说不起大话。你妈妈很任性,她一定要我们结婚,想让你有个有爸爸的家。可我怕我这个做爸爸的不能给你添什么光彩,只会给你抹黑。如果你真爱那女孩,就只能自己争气。
从那天起我开始记日记。我给自己订了一个本子。我在封皮背后写了一个“忍”字,还在扉页上抄写了保尔·柯察金那段著名的语录:“……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又读了《牛虻》、《青年近卫军》、《绞刑架下的报告》……在我的日记里,除了读书心得,学习、考试,发愤的心情,每篇日记结尾我还会记上一个阿拉伯数字。如果母亲偷看我的日记,她会以为这个数字是我记下的难题或是体育锻炼的积分,她不会想到它的真正含意。谁也猜不透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只有我自己知道。每天记下这个数字,我都会有一种安慰,因为拥有一个别人猜不透的秘密而暗暗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