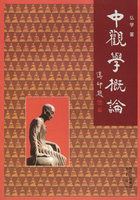父亲沿着镇外的大路走到河边,渡口上的船刚摆过来。正是秋忙季节,赶集、进城的人不多,不等船上的人下完,他一步跨上去。船老大说,天黑了,该收船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船工不情愿地说,这会儿谁还过河呀?他把烟收起来,脱了鞋,卷起裤腿就往河里跳。船夫说,你看,我也没说不摆呀,你这个人!
过了河,还有二十多里路。走到马武镇,学校的晚自习还没下课。一弯月亮升上来,昏暗的灯光从教室窗口透出来。校园里很安静。他沿着碎砖铺成的甬路,一座房子一座房子查看。灯光下晃动着一堆一堆脑袋,每盏灯下围聚着几个学生,专心专意做作业。
有个学生穿过操场向教室走。他迎上去问,同学,请问曾超老师在哪儿?
曾老师住那儿,那不,她门口有棵大杨树。
他穿过操场,走到杨树下,站在她的住室门口。
这是一座砖根脚的土瓦房。屋檐不高,房门窄小。透过格子窗上的白纸,能看见灯下的人影。门没关,他看见她在灯下用心地批改学生作业。他走近去,在开着的门上敲了一下,直愣愣地杵在门框里。
煤油灯在风里忽闪了一下,母亲抬起头来。她手里拿着改作业的红笔,面前摆着一摞本子。一刹那的惊愕之后,她从木椅上站起来。他们面对面呆在那儿,互相打量着对方。
过了一会儿,母亲说,是你——你复员了?
他点了一下头。
从兴隆铺来的吧?
他又点了一下头。
母亲把桌面上的东西往一起收拢,父亲吭吭哧哧说,今天下午兰姐才跟我说你在这儿……明天我就要回县里去……
我去找一下曲师傅,叫他给你做饭。学校里有伙房,很方便的。
不,不用。我来看看你,一会儿就走。
叫他给你烧碗茶吧。
不,真的不用。
可是她已经走出屋去。
他站在她的屋子里,环顾她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屋子很小,顶棚和墙壁糊着报纸。挂在绳子上的衣物让他感到熟悉、亲切。靠后墙是她的床,床上挂着蚊帐,枕边放了几本书。床头的单桌上放着她的柳条箱。他一眼就认出了她的琴盒,装在一个蓝布套里,上边有一些灰尘,看来好久没动过了。靠前窗是她的办公桌,桌面上堆满学生的作业本。刚刚放下的蘸笔,插在红墨水瓶口上。
他顺手从她枕边拿起一本书,凑着灯翻看。
她端来一碗荷包蛋,把桌上的本子推过一边,让他坐在那张木椅上,自己坐在床边。他侧过身子,面对着她。碗里的热气在他面前缭绕,煤油灯在他背后泛出暗黄的光。
你在读《教育诗》?
一位同事的,睡觉前翻翻。
还好吧?
还好。
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
那就什么也别说吧。
我结婚了。
她平静地说,是吗?那不错。
有了一个女孩。
她又说了一个噢,那不错。
她叫刘英。是部队首长介绍的。
我见过她。你忘了?咱们在招待所住的时候她去看你。
噢——是的。
她走后你跟我说过,你们一起从松谷峰撤退,她救了你,你是她的入党介绍人。
那时候我还没什么想法。
是的。我知道。我对她的印象不错。咱们还留她一起吃饭,你忘了?
他慢慢吃荷包蛋,喝鸡蛋水。这比吃饭好。他的确感到渴了。想要见到她的急切心情被一种隔膜的感觉冲淡,他感到很别扭,很难过。坐得这么近,却像陌生人,说话这么困难。
下课铃响了,学生们嗡嗡叫嚷着从教室里奔出来。校园里一片喧闹,像蜂巢炸了窝。
一个男教师闯进来,手里举着一本书,嘴里叫着曾超,你不是想看莱蒙托夫诗选吗?看见桌边坐着一个生人,他站下来,扭回头打量他。
这是我表哥。刚从部队复员回来。到学校来看看我。
哦,哦——他点着头打量这个生人。
父亲有点不自在。他站起来说,不早了,我走吧。
二三十里路,还要过河。要不……
那男人立即附和说,是啊,天这么晚了。
父亲说,没事儿。对一个军人,这算得了什么?
她把他送到学校园外。他说,他是谁?
刚从师范分来的俄语老师。
她陪他往前走了几步。他站下来,拉起她的手,在黑暗中看着她。当他想要拥抱她的时候,她扭转身子说,不,别这样。文昌。
对不起,春如。
他的喉咙里有点哽咽。
我知道家里发生了很多事,可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像往常一样,每天背上书包蹦蹦跳跳去上学,回到家来,就到厨房去找吃的。两天没见到叔叔,我问娘,叔叔到哪儿去了?娘说,出远门去做活了。娘的脸阴沉沉的,我对西屋的三口人越来越不耐烦。我眼睛斜看着西屋的门帘说,他们怎么还不走啊?娘在我头上拍了一巴掌。小小孩子,不许这样刻薄。
那天晚上我感到奇怪,我和娘已经睡下了,那女孩还一直哭。
“那女人抱着女孩站在东屋的帘子外说,兰姐,他今晚不回来了?
“回来恐怕也很晚了。
“她站在门口不走,那女孩不停地哭。
“我穿上衣服走出去。妞妞为啥闹这么凶啊?
“她爸也不回来……
“我看她是有点害怕。盛刚死,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在一个生地方。
“要不,你和妞妞到我屋里来吧。
“那行吗?
“我这张床大。你要不嫌,咱们一起睡。你和妞妞睡这头儿,我跟长安睡那头儿。咱们挤挤,热闹些。
“我揪着你的耳朵把你弄醒,叫你抱着枕头到床那头去,把位置腾给妞妞。我把桌上的灯一直点着。妞妞望着灯玩了一阵,拱进她妈怀里,吃着奶睡着了。
“一张床睡了两个大人,两个孩子,孩子比大人更占地方。我把腿伸到床沿上,刚闭上眼,就看见盛在房梁上吊着,两腿一悠一悠。我冷惊地醒过来,再没睡着。
“桌上的灯整夜点着。我心里挂念那个浑货,不知道他今夜回不回来。半夜三更,河上没了渡船,他得绕到南河湾趟水,这个浑货千万别出什么差错。
“天快明的时候听到院里有响动,我披上衣服走出来。院里察看了一遍,没见人。走进厨房,脚下绊了一下。低头一看,文昌歪在灶门口柴堆上。
“我把灶台上的灯点亮,这个浑货迷迷糊糊睁开眼看着我。
“看你的裤子湿成啥样了,还不进屋去换换。
“他在柴堆上坐起来,手搭在膝边,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
“我在锅里添上水,放上箅子,馏上馍,把小板凳拉过来,坐在灶门口,点着一把柴,塞进灶底。
“我做饭,他坐在柴草上抽烟。
“见到林姑娘心里不是味儿,是吧?
“他一口一口抽烟,烟雾绕着他的脸,飘到屋顶上。
“算了,昌,这都是命。既然跟这个结了婚,就把那个忘了吧。
“你决定要回肖王集?
“我是为了狗娃,为了我的长安。盛这个狠心的,他一走,这院子还有啥留恋?
“我想把长安带到城里去上学,你看行吗?
“我扭回头看着他的脸。你的意思我明白。可狗娃还小,他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再过两年吧,等他大一点,再让他到城里去读书。
“刘英起来了。看见文昌,她把脸板着,垂下眼睛不看他。吃早饭的时候两人谁也不理谁。
“吃完饭,刘英一个人到屋里去收拾东西,文昌坐在廊檐下抽烟。女孩儿醒了,她把孩子抱起来,一边撩起衣服喂奶,一边冲着院里说,今天到底走不走?文昌说,兰姐要回肖王集商量搬家的事,咱们再住两天,等她回来再走。
“那女人站起来说,行,不管你走不走,今天我是一定得走了。你瞧你的朋友,走你的亲戚,把我们娘儿俩扔在这儿,谁管?
“看着那女人和他生气,我心里很不舒服。我说,昌,你回吧。这儿的事你就别管了。反正这么多年你也没管过。
“你去肖王集,谁给长安做饭?
“你不用操心,饿不着他。”
那女人走后,我和父亲亲近多了。娘趁星期日到肖王集去,父亲带我玩了一整天。他说,这屋里最好玩的地方你去过吗?我转着脑袋四下看,你是不是想捉迷藏?
我要跟你捉迷藏你肯定找不着。
父亲很少露出笑容,他笑眯眯的样子让我心里很甜蜜。他看着我的脸,摸着我的头,叹息了一声说,反正这房子要扒了。
父亲拿一把手电筒,带我走到床前,把地上的灰土扫去,抠起一块方砖,向上一提,脚下露出黑乎乎的地道。马家几代人的秘密暴露在我面前。
我不知道我就出生在这间隐蔽在夹墙中间的屋子里,不知道父亲在这张积满尘土的床上辗转反侧,逃避民团的抓捕;母亲在这张床上孕育我的生命。
父亲望着桌上的油灯,脸上充满忧思。我说,爹,这儿是谁的本子?父亲把本子拿起来,一页一页翻动。我伸长脖颈看着那些书页,上面写满了英文,我只能从父亲的脸上猜测那些字的意思。父亲被笔记本上的文字吸引,我把小院里的花盆打破他才把本子放下走出来。
父亲搬起屋檐下那块石头,露出又一个洞口。我们走进一条很长的地道。黑暗尽头,是一片坟地。荒草茂密,树木在风中摇摆。我跳起脚大喊,爹——怎么会走到这儿了?这不是咱家的坟地吗?
父亲在坟地里徘徊,野草在他脚下拂动。我不知道叔叔就长眠在一堆新鲜的黄土里,他的坟上没有幡杆,只有一些零碎的鞭炮纸屑。
父亲肃穆的神情打动了我。我走过去,和他并排坐着。杂草丛生的坟头像苍绿色的波浪在阳光下起伏。一只田鼠跑过来,抽搐着鼻子,倏地一下转身跑掉了。那一刻,八岁的我好像听到了亡灵的呼吸,感觉到他们的脚步,心像小鸟一样向着很远很远的地方飞去,直到变成一个黑点。那是我对死亡的遐想,对死亡的感知。此后每当我一个人静静待着时,我都会想起和父亲并排坐在坟地里的情景。人坐在坟地里,就会感悟到灵魂,感悟到生与死的寂静和辽远。那一刻的感觉深入到我的心灵里,培育了我的多愁善感。当我戴上红袖章手拿红宝书,在汹涌澎湃的人流里高呼着口号行进的时候,我心里就会背诵着小红书上的一句名言——“人总是要死的。”无论他多么生动活泼,意气风发,激情澎湃,无论他多么辉煌、荣耀,不可一世,最终都会化为虚无,融入飘渺,变成无边无际的宁静。这种遐想可能就产生在八岁的那个上午,和父亲一起坐在坟园里的那一刻。
和父亲并肩坐在坟园里,看着远处的田地、树木和庄稼,他身上的气味显得格外亲切,他的声音也显得格外柔和。
他把我的手拉过去,放在自己手里,看着我的脸说:想不想到前苏联去读书?
我好奇地扭过头看着他。对于一个八岁的小学生,前苏联是那么遥远,那么神圣,我不敢想象真能到那儿去。
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我惊奇地瞪大了眼睛。照片上的父亲,一身军装,挺胸抬头,站在一个广场上。他背后是一座方形、平顶建筑,远处映衬着塔楼,塔楼尖顶上高擎着一颗红星。父亲说,这就是红场,这儿就是克里姆林宫。
父亲在地上画了四个符号,СССР,三个像左耳朵,一个像右耳朵。这就是前苏联。父亲教我读这几个字母,爱塞塞塞尔——最后那个尔音要颤着舌头才能发出来。很难读,但是很有趣。
你长大了,要到这儿去读书。
送我去前苏联留学,一直是父亲的心愿,也是我童年最美好的憧憬。
娘从肖王集回来后,我们就开始扒房子。马家的百年老屋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变成了一片废墟。那片地基看上去那样狭小,没法想象它曾容纳着三间阔大的堂屋。走在砖瓦、木料之间,我心里涌起一种忧伤,隐隐地明白了父亲为什么带我下地道、游暗室。房子扒掉后,地道口被填死,暗室被拆除,马家的秘密从此销声匿迹,在岁月中湮没,再也无处凭吊。
“开始搬运木料的前一天,老五叔搬了一把小凳,坐在厨房门口。
“我在灶前做饭,他抽着烟袋慢悠悠地说,兰姑娘,你走了,我咋办?
“我的心酸了一下。
“我能不能跟你去?虽说我老了,犁地、种庄稼,还能帮你干。
“我眼里涌出了泪水。
“五叔,我正等你说这句话呢。真要离开兴隆铺,我真舍不下五叔。你愿意跟我去,我太高兴了。往后我们娘儿俩和你也都能有个照应。
“我到农会去,跟工作队的人商量。分马家财产时,老五叔分到一条牛腿。他愿意把他分的地和房子退出来,我也拿出厨房、柴屋和一盘碾,把另外的三条牛腿换回来,我们三口人就有了一头牛,到了肖王集,也好找人互助,种地就不作难了。
“事儿办得很顺利。老五叔高高兴兴牵回了那头牛。马上把它套在车上,往肖王集拉东西。”
拉砖瓦、木料用了三天时间。最后一天搬家。
父亲帮助把粮食、被褥、箱子、柜子装上车,老五爷用粗大的草绳把车上的东西捆绑好,吆着牲口走出兴隆铺。
父亲一直跟着车走到河边。他把我抱到车上,久久地站在那儿,看着我们走下河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