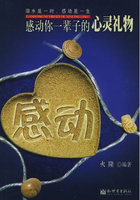“他把脸板得更紧,我复员回县里来工作了,这叫我在县里咋工作?叫我给组织咋交代?
“哟,官帽还没戴上,就怕耽搁你的前程了?
“他楞着眼鼓着鼻子呼哧呼哧喘气,脸上露出当年的横劲儿,不可理喻!真是不可理喻!
“我嗤一下笑出了声。
“吃过饭,刘英抱着小妞在阴凉里玩,那个浑货躲在屋里。隔着门帘,我看见他拿着钢笔趴在桌上写。他不出门,我也坐在屋里不出门,看他的脸色,我对他不放心。这不讲理的,谁知道他会干出啥荒唐事来?
“半下午的时候,他拿着一顶草帽走出来。
“你去哪儿?
“我到吊庄去。
“想找段姨夫啊?
“他没吭声。
“那时候老爷子拿他没办法,现在我对他又有什么法子?我和他已经离了婚,他想怎么我也管不着。”
“太阳一落,地里的热气就消散了。我背着一包刚摘的棉花往家走,在大门口碰上马锁。我说,你找文昌玩哪?他说,我在这儿坐了一大阵了。工作队老王找你,叫你到村长家去一趟。
“一进村长家,老王开门见山就说,肖芝兰,把你家的地再说说吧。
“我家六亩地,我和马长安两口人。
“不是说你,是说马文盛家。
“我和马文昌离婚了,马家的事我不管。
“群众评议会上,不是你拿的文书吗?说马家河滩里那二十五亩地卖给了段根柱。
“谁都知道文盛脑子不好使,我不替他说,大伙咋评议?
“马政委昨天向工作队汇报了,他说家里隐瞒了土地,那张卖地文约是假的。
“我笑了笑。说假嘛——也不假。那是老爷子生前交代的。老爷子说段姨夫辛辛苦苦在那块地里耕种了一二十年,没少给马家出力,文昌一走,家里就三四口人,要那么多地也没用,不如给根柱算了。老爷子过世后,办丧事没钱,我把那块地当给了段姨夫,后来没钱赎,就归段根柱了。只是文书写得晚了两年,也不是有意欺骗政府。
“马文昌同志写的报告很详细,马家不光土地多,还有长工、佃户,剥削性质很清楚嘛。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啊,王同志。老爷子年纪大了,昌在外面读书,盛年幼,别说几十亩,就是三亩五亩,自己也没能力种,不租出去咋办?说老五叔是马家长工那更是说不过去。他孤寡无靠,老爷子收留了他,他在马家能白吃饭?
“老王咧嘴笑了笑,你这个肖芝兰,还挺有板眼的。不管咋说,恐怕马家的成分得重划了。
“你放心吧王同志,我跟马文昌离过婚了,你们想给他划啥成分,和我不相干。”
娘从村长家出来天已经黑了,镇子里炊烟四起,农家院里亮起灯火,大人在家门口喊叫孩子回家。
“拐过巷口,那个不讲理的站在路边。看见我走过来,他迎上来说,他们没难为你吧?我没理他。他跟在我身后,一直走到大门口。兰姐——我是党员,复员军人,我应该如实向组织汇报家庭情况。
“我站下脚,看着他的脸,谁也没拦住不让你汇报呀。
“他们没难为你吧?
“我转头向天上看看说,太阳不是打西边出来了吧?马文昌还会顾惜我?我不是好好的吗?回家照样能给马政委做饭,洗衣服。这是你们马家的事,跟我不相干,你想当地主谁也没办法。可你想过文盛没有?他从小在地里干活,没吃过啥,没穿过啥,没享过一天福,为了你那顶官帽,现在得替你当地主分子,只要你良心过得去,我无所谓。大不了我带着狗娃回我的娘家肖王集,到那儿我是贫农,把我狗娃的名字改成肖长安,离你们马家远点。说着说着,眼泪从我眼里涌出来,七岁来到马家,现在说出这样的话,心里实在是不忍。我擤了一把鼻涕,掏出帕子擦脸。
“文昌,这都是你逼的。你不为文盛想,我得为我的狗娃想。我这个当娘的,不能叫他背着地主羔子的黑锅长大。
“他站在黑影里一声不吭地听着。”
那是一个星期六,我放学很早,村里开会的时候,我正和几个小朋友在打麦场上玩蒙眼过路。秋天的天空像深不见底的湖水,湛蓝湛蓝地罩在头顶上,月亮从林梢升起,繁星满天,银河像一缕透明的云彩从东南向西北弯过去。小宝蒙着眼,我伸出胳膊向天上指点着从他面前走过去。二毛说,指星星的过去了。
村长陪着两个人来了,他在打麦场上放了几把椅子,让他们坐下。大人们从村里纷纷乱乱凑过来。有人坐在小凳上,有人脱下鞋垫在屁股下。娘来了,叔叔也来了。叔叔把我拉在他身边,让我靠着他的腿。大会刚开始我就枕着叔叔的腿睡着了。娘把我抱过去,搂在她怀里。
会议结束时我迷迷糊糊醒过来,人们正在呼呼隆隆散去,有人嘭嘭地拍着屁股上的灰土。叔叔说,我背着他吧,娘把我扶到叔叔背上,我两手搭着叔叔的脖子。我不知道会场上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这个村民大会对我家的意义。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就是这次村民大会,把马文盛宣布为地主分子,宣布马家的土地、房屋、财产要分给贫雇农。
工作组对叔叔不错,他们只让他去修公路,做义务工,没让他参加清算斗争大会。
“第二天,文盛说,兰姐,前院的房子都得腾吗?
“分给人家了,早点腾出来好让别人住。后院的草屋结实着哩,也不漏雨。你一个人,要那么宽绰的房子干啥?
“牛没了,车也没了,犁地、收庄稼咋办?
“牛不是有老五叔一条牛腿吗?他会帮你的。
“你真打算回肖王集,不管我了?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眼泪。不是还有五叔吗?
“盛掉转脸不看我。
“文盛,你哥吃着公家饭,他得守公家规矩,你别怨恨他。
“他没哭,只在鼻子里哼哧哼哧抽气。
“腾房子时文盛很平静,什么话也没说。文昌帮他搬东西,收拾屋子。
“这间草房从前是柴屋,老爷子在世时,里面堆放着木柴、木炭,冬天烤火用的豆秸和一些没处放的杂物。打开门,几只鸡咯咯嗒嗒叫着飞出来,柴草窝里留着几个鸡蛋。小屋的山墙上露着一个三角形的大窟窿,五叔用秫秆把它插好,抹上黄泥,把那扇破门钉了两块木板,让它能勉强关上。
“搬完家,文昌说,兰姐你下午早点回来,晚上咱们和盛一起吃顿饭,明天我和刘英就回县城了。”
“太阳刚落山,我从地里回来。文昌到街上去买了烧鸡、卤豆腐皮,亏他还记得文盛小时候喜欢吃鸡杂碎,特意给他买了一包。
“他在东街的作坊里打了二斤烧酒,我炒了几个菜端过来,在草屋门口树阴下摆一张小桌,一家人围在盛的新家门口吃饭。
“盛,从前咱家剥削了乡亲们,现在咱是替老辈人还债,把剥削人民的东西归还给人民。
“刘英插上说,你哥是党员干部,他要带头执行党的政策。
“文昌端起杯说,来,为了马家的新生,干一杯!
“盛嗞一下把杯里的酒喝干了。他一声不吭,也不抬眼看人,只管拿筷子夹菜往嘴里填。”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马家聚在一起吃饭人数最多的一次。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兴隆铺的烧鸡、鸡肝、鸡心、鸡肠,太好吃了。叔叔不断往我碗里夹,弄得我不好意思。小女孩呀呀叫着,在她妈妈怀里蹬腿乱蹦,父亲不断回头去哄她,惹得我心里很讨厌。叔叔闷头喝酒。娘说,盛,你少喝点,明天还得到马武镇去修路。老五爷脸红红的,筷子在手里不当家,夹起的菜没到嘴里就抖落在桌子上。
“鸡叫二遍我起来烧火,给文盛烙馍,让他带着去修路。给文昌他们煮咸鸡蛋、咸鸭蛋,让他们带回城里。说不定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他们做饭,心里不是滋味。
“饭做好了,天色大亮了,老五叔已经下地,文昌、文盛还没起床。这弟兄俩昨晚都喝多了。
“我把烙好的馍装进布兜,在里面放了一骨朵大蒜,提上到后院去。
“小屋的门还没开,我站在门外喊,盛——快起来!再不起来就耽误点名了。头一次出义务工,千万别让人家说你故意拖拉,心里不满。
“叫了一阵,屋里没动静。我走近去,用手一推,门开了。迎面看见盛像一条鱼似的吊在房梁上。房梁很低,盛的脚勉强离地,绳子套在脖子里。我把布兜扔在地上,跑过去抱着他的腿往上着喊,盛——你咋能这样啊——盛——
“盛的腿像两根棍子,身子像一截树桩,我费了很大劲才把他放下来,脸上有点余温,鼻子里一点气息也没了。
“我走回堂屋,站在西屋门帘外说,昌,你快到后院去看看吧!
“昌在屋里摸索着说,咋了?有啥事?
“我嘴唇打着哆嗦,眼泪顺脸往下流。你兄弟死了。
“盛出什么事了?
“你兄弟死了。你去看看吧。
“刘英在屋里说,怎么会……呢?昨晚不是好好的吗?怎么……
“我坐在堂屋椅子里,眼泪哗哗往下流,我举起巴掌默默在脸上擦,一声也没哭出来。
“昌去忙他兄弟的事,我坐在那儿一直没动,直到装殓完,我也没去看一眼。
“下葬的时候,我到坟地去。墓坑挖好了,我照着文盛的棺材踢了几脚。盛——你个没良心的!我把你从小伺候大,天天给你做饭、洗衣,怕你热着,怕你凉着,在外面怕你受外人欺负……你就这样报答我?你们马家男人都这么狠心吗?
“眼泪把我噎得说不出话。我拿手在脸上一把一把擦,可还是一声也没哭出来。”
太阳像烧红的鏊子,慢慢向西边的岗坡坠,晚霞扯起一条条镶边的彩带,一直漫到头顶。娘站在坟园边的柏树下,看着五爷他们把坟头慢慢堆起来。帮忙的亲戚、邻居扛着铁锨一个个走散,只剩下父亲一个人拿着铁锨在坟头上拍土。
坟园里冷清下来,一群乌鸦叫着往林子里飞。父亲走过去,站在娘身边说,兰姐,走吧。
“我走到盛的坟边坐下,看着新堆起的黄土,眼泪擦不及地往下流,心里像打开了涌泉,酸痛一阵阵往上翻。
“盛,你为啥这般绝情绝义?为啥这么死脑筋?昨天还好端端的,今天就埋到地下再也见不到了。你叫我好后悔呀!不该对你说要回肖王集,不该叫你昨天搬家,要是迟上十天半月,你这个傻娃儿就不会这么想不开了。照顾你二十五年,叫我咋割舍得了?
“文昌弯下腰来搀我,我把他的手推开,坐在那儿没动。
“你们马家这弟兄俩——没一个好东西!
“他站在那儿不吭声。
“我蹲坐在地上,手指着老太爷坟前的石碑,几年前,你是从这儿出去的,对吧?你临走把我的银货拿走了,你走后没过十天,爷爷就不在了。那时候你在哪儿?你知道我在家作了多少难?受了多少磨难?马家的天塌了,我这个妇道人家给你顶住。你知道吗?爷爷刚过五七,你那相好的女孩就来了。她带着身孕,在你藏身的暗室里住了一年。我心上像扎了一把刀,还得给她端吃端喝,伺候她坐月子,给孩子擦屎倒尿。她走的时候我当了河滩里十亩地给她做路费。……你们都是咋报答我的?阎王爷为啥造你个害人精,叫你在这世上祸害人!害了一个女人不够,还害第二个?
“他站在那儿一声不吭,任我数落。
“我扭回头瞪着他说,你个没良心的,几年前怎么走的?几年后又怎么回来的?难道你不想问问林姑娘,她现在在哪儿?她为了你跟家里闹翻,半道上一个人逃出来,为你受了那么多苦,你个负心汉,娶了媳妇忘了旧情!她是狗娃的亲妈,给你生育了马家的后代!你回来就不想问问她现在啥样?
“这浑货愣住了。
“我本当不跟你讲,坐在这坟园里我实在是千头万绪,又气又恨,忍不下这口气。
“兰姐,你知道她的情况吗?她现在在哪儿?
“他把身子屈下来,就着草坡坐在我旁边。本来我想把什么狠话都说出来,狠狠刺刺他。可看他那失颜变色的样子,我又生出了怜惜。盛已经埋进了土里,这浑货他还系连着我的心。别看人模狗样当了政委,当了志愿军英雄,可这会儿他那副可怜相还是叫我心疼。一个亲人也没了,在这世上,还有谁会真心疼你?那个外地带回来的婆娘指望得住吗?
“我眼里的泪水又流出来,悲伤又涌上来。昌啊昌,你个浑货,啥时候你才能懂事儿啊?
“兰姐,她在哪儿?你能跟我说说吗?
“林姑娘她就在马武镇中学。
“你见她了?
“她来看过长安。
“她……还好吗?
“孤身一人,年龄也不小了,连个对象也没有,心里啥样,你去想吧。
“他走到坟园边,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着了,站在那儿抽。
“离开坟园走上大路,他把肩上的铁锨递给我。你回家吧,我到马武镇去一趟。
“现在去?
“对刘英说,我去看一个战友。
“天黑了。昌!
“没关系。明天我得回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