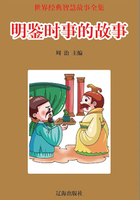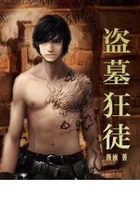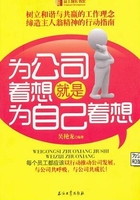清晨,张克城被小翠带到鹓办公室旁的小客厅,还没进门,就见一个身材高大的女子起身迎着他,憨憨地一笑,做了一个请进的手势,把他让进了沙发里。不一会儿,过道传来一阵咚咚的脚步声,张克城听出是鹓的脚步声,立即站起身来迎候着。菊花见他起身,也站起来恭立着。鹓还没进门便咯咯地笑着说:“嗨,真是两大金刚啦,好威武哇。”她在沙发上坐下来,对站着的两个人说:“坐吧。张克城,她叫任菊花,是选来陪美仙上昆明读书的。明天,你们陪美仙出发,你们的职责是把她安全地送到昆明。”说完,站起身来,直视着他俩。张克城和任菊花也连忙站起身来,恭敬地答应道:“听太太吩咐,我们将竭尽全力保证三小姐的安全。”鹓会心地一笑,说:“我与老爷商量,你们先从重庆坐船,走水路到宜宾,上岸后走陆路从四川筠连到云南盐津,路上千万要小心谨慎。美仙的外公钱老爷子有给云南王龙云的信函,揣在美仙身上。
你们去准备吧,船票已经买好,明天早晨七点开船,盛金银开车送你们到朝天门码头,去吧。”从重庆到宜宾的都是小船,没有头等舱,一等舱也是四人间的舱室。张克城刚把美仙领进舱室,迎面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提着布袋挎着包袱对号走进舱室,问:“我们同舱?”美仙坐在铺沿上说:“对,我们同舱。我们三个是一家人。请问你到……”还没等邵美仙问完,妇人接口道:“我到宜宾,家住云南盐津。我堂哥在重庆当兵,是团长。我们盐津很苦,我的男人是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的孱头。但他却怂恿我来向他堂哥借钱。唉,一路上好辛苦啊。”妇人捋了捋盖在额头的短发,向耳旁一抿,又问:“你们要到哪里去?看你们都是有钱人家的贵人,我们还住一起。嗨,我那个堂哥哟,硬要给我买一等舱,还不是四个人睡一间的房,花那么多的钱。这些钱我们家要吃半年的啦。”美仙见她是个没有文化的心直口快的妇人,安心了许多,便说她到昆明去读大学,要路过盐津。妇人欢喜地说:“嗨,我们同船又同路呢。到了盐津,在我家去住两天。
我们穷乡僻壤,虽然没有你们家富贵,但我男人的老爹还是一个保长呢,方圆几十里的地方,他都镇得住——啊,我姓龚,就叫我龚嫂吧。”张克城见她们聊得热闹,就在舱门外,一会儿站立,一会儿徘徊,像巡逻一般保护着邵美仙。任菊花在进门的铺位上坐着,仔细地观察妇人绣着花边的衣袂。轮船启动了,底舱传来突突的机器吼声。随着一阵剧烈的晃动,轮船调转船头,向朝天门码头左边的长江逆水而上。挤上船的多是小商小贩和外出寻找工作无望而两手空空回乡的农民。还有不少顺水放筏的漂工和交割了木材返回山里去的伐木人。他们赤手空拳,没有行李,用一块粗布垫在甲板上,或坐或卧,悠悠地吸着自卷的叶子烟。饿了,不去餐厅吃饭,只将随身自带的廉价的白烧饼,就着一杯白开水充饥和解渴。待船一开动,他们就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地讲起了在重庆逛窑子开洋荤的种种艳遇和传奇,以寻求精神上的乐趣,消磨时光。美仙对小船的颠簸和舱室的简陋并不介意,一有空闲便坐在甲板或过道上,观看四川人的穿戴与打扮,听人们演绎自己的人生传奇。
船到宜宾,已是落日时分。张克城在船上便订了码头上临江的翠屏居客店。龚嫂下船后,陪着美仙去看了房间,见套间小巧而布置华丽,她连连咂着嘴,说:“嗨,你们住一晚上的房钱,够我们买半条水牯牛呢。好,你们睡吧,龟尾驿坡前的马车站旁边,有我一家亲戚,我把马车给你们定好,明早晨我来喊你们。我在亲戚家里住,明早我们一道去盐津啊。”美仙谢过她,叫菊花把龚嫂送出了客店。天刚蒙蒙放亮,江边便热闹了起来,有担柴的挑盐的,推车卖米的,赶猪牵牛的,卖叮叮糖和盐脆花生的。行人摩肩接踵地拥挤在不大的码头上,或过渡上舟,或进出小城,或登船远行。吆喝声,车铃声,此起彼伏,热闹异常。在清静的环境里长大的邵美仙,从来没有见过小城如此的热闹,她早早地就被窗外的吆喝声吵醒。她裹着棉袍,推开窗,踮着脚尖伏在窗口,只见半边临江的街道人潮涌动,后街的人也熙来攘往,没有半点抗战的气氛和战时的恐惧。在这里,她深深地感受到了后方的安恬和舒畅了。她抬头远眺,见昨天刚开过来的沪渝轮,又满载客人向下游的重庆起锚开拔。不一会儿,那船便在春天早晨的江雾中,若隐江天了。
正在美仙入神地欣赏这春江早忙图的时刻,客室的门便被咚咚地敲响。张克城开门,只见龚嫂气急咻咻地在门外嚷道:“你们快点儿,马车都要开出驿站了。我们得早走,晚饭前才能赶到盐津,不然的话,过了这村便没有那店,要打麻黑,歇岩窝哟。为了俭省点,我们四个人包了一辆车。我知道你们是贵人,特别选了辆新车好马,包你们满意。”任菊花听见吵闹声,也早早地起了床,为美仙端来了梳洗的热水。不一会儿,妈子在客室摆好豆浆、油条、煎饺、包子、花生浆稀饭、煮鸡蛋和包盐蛋,还有几碟小菜,都是些五香豆腐干、水煮花生米、凉拌韭菜芽、涪陵榨菜、内江豆腐乳、蜀南泡竹笋之类的素食和一盘阆中产的张飞牛肉。美仙来到客室,轻轻招呼过龚嫂,叫她进来吃饭。龚嫂推让了两句,便坐进餐桌前的椅子里,见有如此丰盛的早餐,她立即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美仙见她左手拿着包子,右手筷子上夹着牛肉,嘴里嚼着五香豆腐干,眼睛还直直地盯着包盐蛋,那首尾繁忙的穷吃相,逗得她“哧哧”地掩嘴浅笑了几声。她忙给张克城说:“快叫妈子端一甑子干饭来。
”不一会儿,妈子端来一个小木桶样的甑子,里面蒸熟的是金裹银玉米混着大米煮熟的干饭,揭开盖子,里面还飘散出一股股木头甑子和米饭的清香。四人匆匆吃过早饭,便来到真武山下的龟尾驿马车站。车把势是个二十八九岁的长脸大胡子,他嘴里叼着自卷的叶子烟,眼睛微微凹陷,直鼻梁,大嘴巴,面部棱角分明,头戴一顶向上翻卷的小草帽,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耿直的小伙子。他在绣花边的黑色棉袍腰上束着一根牛筋带,斜插一把尺多长的刀鞘,鞘里那略带弯形的长刀,像日本兵的战刀。他伺候四个乘客坐在有布垫的车座上,神色冷峻,跨上车头,鞭子一甩,那两匹枣红马便迈动嘚嘚的步子,载着邵美仙等四人,顺金沙江的小马路,走进了崇山峻岭的宜盐小道。小道被雨天的车轮轧成泥泞,天晴后,形成了道道深浅不一的辙印,坚硬的辙痕把马车荡得晃晃悠悠磕磕绊绊。美仙自觉仿佛又坐进幼儿时的摇篮里,摇晃得浑身怪舒坦怪惬意的。她好奇地推开马车棚的帘子。只见小路蜿蜒,万山嫩绿,一团团的迎春花放开灿烂的花瓣,在向她呵呵地笑着。美仙陶醉了。她眼睛里闪着陶醉和惊喜的目光。马车缓缓地摇进一个关口,便进入头顶只能望见一线天的峡谷地带。
美仙将手臂伸出车外,一股股刺骨的冷风伴着细小的水雾拂过她的肌肤,让她感觉惬意而舒爽。她眯缝着两眼,如醉如痴地感受着大自然给人的美妙。突然,马车一顿,紧急的刹车和马的嘶鸣使邵美仙前仰后合地颠簸了两下,差点儿将她甩出车外。她睁大双目,忽见山路上车轮前方,离马蹄不足五丈远的地方,突兀地伸起两根小水桶般粗的,像乌木一样黑中带青,黄绿花纹的东西在闪动。车夫失色的大叫一声:“糟了,这个瘟孽又出现了。”他轻轻地扽了扽缰绳,枣红马屏住气,它跃起前蹄,忽然又着地。似乎它懂得了主人的意思,悄无声息地往后退了几步,马车停住了。车夫惶恐的脸色顿时放松了下来。他咂了两口叶子烟,粗犷地叹息一声,车转脸来,向着身后的人冷峻地说道:“前边有两条蟒蛇,是刚出洞或刚爬出老林的菜蟒。春天来了,它们在蟒缠交。
我们这一带的猎人说,看见蟒缠交的人,不死也要脱层皮。嗨,我今年就不知道怎么过了哟。哎,话又说回来,不管有啥险恶和厄运,总还是要一天天地过下去,总还是要走这条险道才能挣钱去养家糊口的啊。”龚嫂立即接过话头,不惊不诧地说:“唉,老哥嘞,你不要相信这些迷信人的鬼话,这都是算命先生骗人的鬼话。我们云南的蟒蛇多得很,若我有刀有枪,我还敢去杀它两条蟒蛇来给你们炒着或炖起吃呢,把一只老公鸡或老母鸡杀了与蟒蛇炖在一起,熬过半天,那叫龙凤汤的汤汁才好喝呢,又养人,又爽口,味道鲜得美死人哪!”龚嫂的一席话语,把压在美仙他们心头的恐惧和阴霾一扫而光,他们都长长地叹息着出了一口气。美仙从恐骇中醒来,惊叹地转动大眼珠,盯着寡瘦脸的龚嫂,哧哧地笑着说:“看不出来你还这么胆大,真不简单哪。
”“那有啥稀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生长在大山沟里的人,特别是我们云南天气又热和,天天都要同豺狼虎豹,毒蛇虫蝎打交道,我们把这些瘟牲都看惯了,就不害怕了。嗨,人家有些有本事的人,还专门养蟒蛇,同它们说话呢,叫它们出洞爬树守门,它都要听话。其实,养蟒蛇比养猪养羊还方便。这东西牙齿里没有毒,不咬人,只是它长大的身子看起来令人胆寒害怕。你别看它尖头小眼吐着舌头蠕动爬行,全身又麻花麻花冰凉冰凉的样子,其实它很可爱,很好看呢。”看见前边滚动相缠的巨蟒那恐怖的形象和听着龚嫂对蟒蛇外表体型的描述,美仙胆战心惊的胸背上陡地沁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她瞪大着惊骇的双眼,与没事儿一样的龚嫂对视了一下后,轻声说:“嗬,龚嫂,见你个头不高,人又干瘦,却有如此的胆量,我好佩服你哪。”龚嫂没有答话,只是得意地干笑了两声。
缠交的蟒蛇终于精疲力竭地离开,慢慢地蜷伏于山脚下的溪流里去了。小溪突然有了两个庞然大物的堵截,溪水陡地涨了起来,漫上马车路的小道。马车夫见水涨起来了,急急提动缰绳,挥动马鞭,枣红马跃起前蹄,仍然心有余悸地迟疑了一刹那,嗅了嗅前方已无可怕的寒冷气味,才踏实前蹄,马车慢慢地启动了。离开了蟒缠交的湿地,车夫才大起胆子夸耀:“若今天只有一条蟒而又是回宜宾,我肯定用我的马刀将那瘟牲劈为几段,拿到街上去卖个好价钱嘞。”龚嫂笑了笑,说:“看你胆小如鼠的样子,还夸海口,还说能劈蟒蛇?你们四川人没见过蟒,一旦滚进江河,都说那是龙在现身呢。连跪拜都来不及,还敢买你的蟒肉?”说完,她哈哈地笑出了声来。张克城见龚嫂不仅胆子大而且人又逗趣,便一扫了他对偏僻山里人没有知识的偏见,主动搭话道:“龚嫂太幽默了,说的话把人的肚子都要笑疼,有你在一块儿,我们赶再远的路都不寂寞了。”龚嫂见这个牛高马大的男人都拍她的马屁,在马车里乐得俨如是车的主宰者,就眉飞色舞地夸起了他们云南人的种种英雄事例和盐津街上的奇男怪女。马车越往前走,颠簸得越觉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