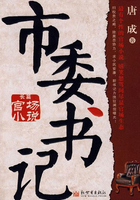“他问我是不是霍克,我说是。他就说,艾赫利先生有一封信给我,还让我马上看看,信上面还有艾赫利先生的签名。大致内容是说,桶子的事情他已和布洛顿先生沟通过了,没有问题,菲利克斯先生可以直接将桶子领走。他还说,公司有责任将货顺利送到货主手中,要我陪着菲利克斯先生把货送达。这件事办成之后,再去回复董事问话。
“看完信后,我也没多想就答应了。菲利克斯先生早就准备好了马车,我召集了几位工人帮忙把桶子吊到了马车上。那辆车上还有两名男子,一个身体健壮,长着红头发,另一个是矮个子、黑皮肤的马车夫。从码头驶出后,马车向右转上了里曼道,后来的街道我就不熟悉了。
“走了大约有一英里,那个红头发的男子想喝点儿小酒,但菲利克斯拒绝了他,说等办完事再喝。奇怪的是菲利克斯很快又改变了主意,于是我们停在了一家酒吧前。那个矮个车夫叫华迪,菲利克斯问他是否可以就地停车时,他拒绝了。于是,菲利克斯提议,让我们三人先去喝,车夫在原地看守,菲利克斯喝完后就出来换车夫。于是,我们三人先进去了,要了四瓶酒并结了账。菲利克斯喝完就要出去替换车夫,让我们等着华迪。他一走,那个红发男子立刻向我倾过身来低声说:‘嘿,兄弟,那个桶子很奇怪,老板到底拿它做什么?五比一,我跟你打赌,他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说:‘是这样吗?我不太清楚!’可是,其实我心里也是那样想的。但一想到艾赫利先生的那封信,又无法怀疑,他不会把有问题的事说成没问题的。
“‘喂,如果我们运气够好,’红发男子又说,‘也许有两三镑可以赚。怎么样?’
“‘怎么赚?’我问。
“‘这你还不明白?’他说,‘就是那个桶子呀,如果真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老板肯定不希望被人发现!所以,我们就告诉他,要保守秘密可以,但要花点儿钱贿赂我们!这不就成了!’
“听他这么说,我还以为这人也知道桶子里藏有死尸。要真是这样,我倒想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转念一想,或许这家伙早就和菲利克斯串通好了,他这样说,只是想探探我的口风,看我对这件事了解多少。所以,我就先装糊涂,然后看时机的变化而采取行动。
“于是,我跟他建议道:‘让华迪也跟我们一起吧?’
“红发男子立刻说:‘不行!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华迪的酒还放在那儿,没有动过。怎么他还不进来?真是让人想不通!
“‘啤酒不喝,放在那里会越来越苦的。’我说,‘那家伙不是要喝酒吗?怎么还不进来?’
“听我这么一说,红发男子站起身来说:‘我去看看,他搞什么鬼呢?’
“我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和红发男子一起走出了酒馆。那辆装桶子的马车已经没有了踪影。我又朝远处望去,除了马车,菲利克斯和马车夫也不知去向了。
“红发男子气愤地咒骂起来:‘该死!他们把我们甩了!快,我们追过去!可能他们还没走远,转个弯就看见了!你往这边,我去那边。’
“这时,我明白自己被骗了。心想也许这三个人根本就是一伙的,他们想要甩开我,但是顾虑到我会怀疑,所以以喝酒为借口,设下了圈套。那个红发男子在酒馆里说的那些鬼话,只是为了拖住我,好让他们有时间溜走。可是既然已经跑了两个,我不能让这个也跑了!
“于是我跟他说:‘老兄,那可不行!我们还是一块儿走吧!’说着,我赶紧去抓住了那个红发男子的胳膊,催着他快追。我们都走到街角了,还是没有找到马车。看来他们是彻底把我们给甩了!
“那个家伙不断地骂骂咧咧,甚至在大街上就大叫起来:‘我还没拿到工钱呢!’
“我想探听出他从哪来,是谁雇的他,可是这个家伙守口如瓶,就是不肯透露。他越是这么神秘,我就越要跟紧他。无论如何,他是要回去的,只要跟着他,我就可以查出他的地址和职业,顺藤摸瓜就能查出菲利克斯的底细。三番五次他试图摆脱我,但都失败了,于是变得气急败坏起来。
“我们在大街小巷里溜达了近三个小时,将近五点时,又去喝了几杯啤酒。喝完酒后,离开酒吧,我们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要往哪里走。这时,那个家伙摇摇晃晃地突然撞到我身上来,而我没有预料到他会这样,差点撞倒一位老太太。我不得不赶忙去扶老太太,可就这一转眼的工夫,这家伙就已跑得无影无踪了。马上我就穿过马路,到另外一条街去找。后来又回到酒馆去找,已经完全找不着那家伙的踪影了。我觉得今天真是太窝囊了,别提有多懊恼。最后,我决定去总公司找艾赫利先生报告,之后,布洛顿先生把我带到这里。”
霍克讲述完后,谁也没有再说话。在讲述的过程中,班利警官一如既往地沉思着,他审慎地将布洛顿先生的报案和霍克的汇报做对比、联系,将不容置疑的事实挑出来,而把当事人的主观想法尽量分离出来,然后,又不断地思考着一些特别的关联之处。虽然没有任何理由让班利警官怀疑这两人,但是如果他们所言属实,那么,桶子的存在和后来被领走的事就是真的了。但还有一点让他心存怀疑,那就是真的有一具死尸装在桶子里吗?现在看来,能证明这一点的证据还不充足。
“布洛顿先生说,有具死尸装在那只桶子里,霍克,你也认为那是死尸吗?”
“是的!有一只女性的手臂立在桶里,我们都看到了。”
“也许那只是件雕刻品!桶子的标签上不是也写明里面装的是‘雕刻品’吗?”
“不!起初的时候,布洛顿也这么说,但又仔细查看之后,他才认同了我的说法,那绝不是雕刻品,的确是死尸的肢体!”
不管怎么说,两人都非常坚决地认为,那个肢体是一具死尸上的。可是他们并没有确实可信的证据,只是“一看就知道,那是具死尸”。警官也只好半信半疑。突然,他又想,医学院的学生经常会搞恶作剧,也许那桶子里只有一只手臂或一只手。
他又问霍克:“在布鲁库奇号上,菲利克斯不是交给你一封信吗?还在你那里吗?”
“在。”霍克说着,拿出信,交给了警官。这张信纸的顶端印有公司的正式名称,公司基层职员都会用它。信是这样写的:
圣卡特林码头,布鲁库奇号,霍克先生:
寄给菲利克斯先生的桶子的事情,我和布洛顿、菲利克斯已经洽谈过了。现在已确认,桶子的确是属于菲利克斯先生的。布洛顿与你的约定也已经作废,所以请你立刻安排交货。
接到信后,尽快把桶子交给菲利克斯先生。
将货物交与收件人是本公司应负的责任。劳烦你代表公司随同客户将货送走,完成工作后复命。
I&C海运公司
常务董事 X·艾赫利
X·X代笔
1912年4月5日
单看字母X,很难琢磨出它其中的含义,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它象征着某人的某种地位。信中签名的笔迹的确属于同一个人,“艾赫利”格外显眼。
“这封信的信纸是用贵公司专用的,”警官对布洛顿说,“信顶端上印的就是贵公司的名称,这是错不了的吧?”
“信纸是没错。”布洛顿回答说,“不过,这封信的内容肯定是假的。”
“虽然我也这么认为,但你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原因很简单!首先,我们职员之间是不用这种信纸联络的,用的是比较便宜的备忘录。其次,我们公司并不用手写,全都是打字打上去的。再次,公司并不采用这种签署方式。”
“说得有理!这个证据的确有力。伪造这封信的人对贵公司并不了解,他肯定不知道董事姓名的英文缩写,也不清楚职员彼此联络的习惯方式。他所知道的,就只是‘艾赫利’这个名字。根据你先前的讲述推测,菲利克斯似乎的确只知道这么点儿。”
“但是他怎么会有公司的信纸呢?”
班利警官微笑这说:“这个好办,从贵公司的办公室主任那儿得到的。”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他跟威尔要了信纸和信封,说要给艾赫利先生留言。然后,他留下了信封,却把信纸带走了。”
“正是这样。当初艾赫利先生说信封里什么也没有时,我就猜到他会使这么一招,所以,我想一定要比他先到码头。不过,麻烦你再描述一下桶子上贴的标签。”
“那是一张长约四英寸,宽约六英寸的厚纸做成的,纸的四角被大头针固定好了。在标签的上半部分印的是德比耶鲁公司的名称和广告,下方偏右有一处长约两英寸,宽约三英寸的地方,写着收件人的名字。写名字的空栏有一圈黑色粗线的边框,可以看出来这一栏是沿着粗线挖走了中间的部分,从而留出空间,后用厚纸粘贴在此。所以,收件人的名字‘菲利克斯’并不是写在原先的标签上的,而是写在了加贴的那张纸上。”
“这样做很奇怪,不是吗?”
“我本来想也许德比耶鲁公司的标签一时用完了,为了应急才重复使用旧标签的。”
班利心不在焉地回答着,这些问题在他的脑子里来回地盘旋。如果桶子里装的真是雕刻品的话,他这样说也不无道理。但是,如果是死尸,那原因就不是这么简单了。他继续思索着,目前有一个结论,就是他相信这只桶子绝不是德比耶鲁公司要运送出去的货物。如果真是那样,那么桶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时,他又假定了另外一种情况。也许德比耶鲁公司曾寄出了内装雕刻品的桶子给嫌犯,而嫌犯还没来得及归还桶子就杀了人。处理死尸的时候,那只空桶子就派上了用场,于是就任由它被寄送到很远的地方。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凶手使用的标签是从哪里得来的呢?说不定玩的也是菲利克斯这一招金蝉脱壳。为了在海关那儿蒙混过关,他是故意留下德比耶鲁公司的印刷字样,然后在书写收件人的地方做了假。想来想去,班利警官觉得这样解释是最合理的,此外,找不到其他的说法。
时间不早了,他对两位客人说:“两位专程过来提供线索,真是太感谢了。能把你们的住处告诉我吗?今天晚上,这件事只能先告一段落了。”
看来今晚想要好好睡觉是不可能的了,班利警官再次回到家里,可是九点半的时候,警察厅便又将他召了回去。警察厅接到电话,有个人希望能马上和他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