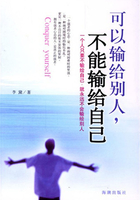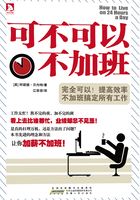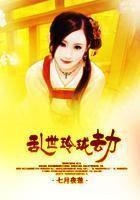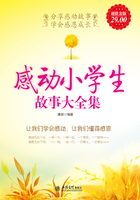正视我们的本性
上节课中,我们认识了自尊的三个阶段。我们知道,依赖性自尊是最初的阶段,也是我们大部分人正在经历的阶段;独立性自尊属于第二个阶段,我们可以比较客观地认识自己;而无条件自尊有点近乎“圣人”,也是自尊的最高境界。但是,这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只要独立性自尊,或者只要无条件自尊?既然依赖性自尊会让我们迷失,是不是就要坚决与这种心理划清界限?
沙哈尔老师的答案是:你越是想要否认依赖性自尊,它越发会黏住你。因为,别人表扬我们时我们就高兴,别人否定我们时我们就伤心,这是人之常情,是人性中的一部分。我们越是压抑人性,人性就反扑的更厉害。我们在面临重大场合时,越是告诉自己别紧张,结果往往是更紧张。但是当我们决定接受自己很紧张的现实,紧张情绪对我们的控制反而减弱。中国人治水讲究疏导,要接受水性,然后引导,同样我们也要接受人的本性,然后采取合适的应对方案。
沙哈尔老师心目中有一个偶像,是他的老师沃伦·本尼斯先生。本尼斯曾在多所大学任过教,在哈佛商学院呆了三年,第一年他是访问学者,沙哈尔老师选中他的课,由此迷上了他;第二年,沙哈尔老师就成为了他的助教,在平时的交流中,越发觉得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当时他已经80岁了,但当他所到之处,周围的气氛都会活跃起来。他的笑容和举止,让周围的人如沐春风,“他仅仅是站在那里,都会让人感觉很舒服。”自然,这样的人属于极少的拥有很强的无条件自尊的一类。
沙哈尔老师对本尼斯的仰慕之情无以言表,他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那样的人。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问本尼斯:“你是怎样做到现在这样的?”他拍了拍年轻的沙哈尔的肩膀,带着平静、慈祥、鼓舞的眼神说:“我从前可不是这样的。”说完就离开了。
他并没有说:“我并不觉得自己很棒啊,谢谢你的夸奖。”他的真诚之处在于他知道自己的价值,也很自信。而且,他的回答也告诉我们:无条件自尊不是一夜之间获得的,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精力、自我有意识培养、从失败中吸取经验反复前进的缓慢过程。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学会接受自己、接纳过去,学会变得宽容大度。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谦虚其实是另外一种招摇。”也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真正的谦逊,如沙哈尔老师的偶像本尼斯先生,南非总统曼德拉却并非是为了“招摇”,他们的谦虚不用压抑自己的任何本来的愿望,是自然而然地发自内心深处的。要达到这种程度的谦,变得和本尼斯一样真诚、实在,这个过程和我们在婴孩阶段学习走路是一样的。刚出生时,我们都不会走路;然后,我们借助他人或者他物的支撑站了起来,围绕凳子,小心翼翼的迈出人生第一步;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能单独走路了,但还是很小心翼翼,不太熟练,经常跌倒、又爬起来。再过一段时间,婴儿可以很熟练的走路了,甚至开始跑动,不用再思索每一步怎么走,他已经学会了走路。我们不能从一开始就学会跑步,必须一步一步地来,没有人会不允许婴儿跌倒,所以我们也不要苛求自己一下子变成无条件自尊的人,甚至不要急于去成为那样的人。
发现一个镇定的自我
提到纳粹,没有人不感到战栗。时至今日,人们还在讨论那些参与屠杀行为的德国平民们到底有没有罪,电影《朗读者》中的女教官,也曾引发了不少人的同情之心。
沙哈尔老师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了这些人的行为:他们规规矩矩、服从权威,是因为他们需要集体的肯定;那些种族主义者倾向与外部环境进行出生地、教育背景、肤色等各种各样的比较,以此来寻求优越感。而这些正是依赖性自尊的体现。太依赖别人的看法,就会丧失自我的最基本判断。
依靠性自尊较强的人,容易受到他人言行的影响,倾向于选择别人已经走过的路,甚至用机械地辛苦工作以获得他人的肯定和赞扬,他们被限制在固定的模式中。而那些独立性自尊较强的人,喜欢跳出固定的模式,选择别人未走过的道路,这当然不是说他们从不选择别人已经走过的路,前提是如果他们真的喜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爱自己家的老人,才能推而广之,而爱他人的前提,就是爱自己,我们对待他人的行为态度可以反射出对待自我的态度。如果我们的独立性自尊较强,会变得更镇定,不用随时向别人证明自己,不需要时刻猜疑:“这个人到底喜不喜欢我?我怎样取得他的认同?”即便别人不喜欢我,不过我还能接受,因为我足够坚强、韧性十足。这样,我们会发现一个更镇定自若的自我,生活会变得更轻松,我们的人生可以用来享受存在于世的感觉,而不用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就像前面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我们需要学习的不是如何表现自己,而是如何更好地表达自己。
当我们在身体和情感上贴近他人,尤其是亲近之人的同时,依然保持自我,这种能力,就是独立。它能让你即便面对来自爱人、家人和朋友要求你妥协的压力,依然坚持自己的道路。你可以同意他人,而不感觉失去自我;可以不同意他人,而不感觉孤立和无助。这就是表达自己的最高境界,做回自己,这是独立性自尊的本质,也是无条件自尊的精髓。
当然,说起容易做起难。我们如何去实现这种成长,达到无条件自尊的境界?在这门课上我们学到了很多方法,比如写日记,瑜伽,运动,冥思,学会感恩,所有这些都帮助我们更好地实现自己,加快这个过程。
如果你想改变某个领域,首先要在行为上进行改变,比如说如果我想拥有较高自尊,行为处事方面就要感觉自己的自尊已经很高。因为自尊也是一种态度,对自我的态度。加强这种态度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改变行为,这也是榜样的力量。你想拥有沃伦·本尼斯的镇定自若、慷慨、包容;或者想拥有布拉德·皮特的俊朗和健康形象,你就先在行为上预设自己已经拥有了那些美好的品质,在这样的预设中,我们会不断的改变自己,达到理想的状态。
在如此的练习中,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那个镇定的自己。
“隐形的魔咒”
如果一个人的整个人生都是“隐形”的,没人知道他的相貌、他有怎样的品质、兴趣爱好、生活作派等等,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有多慷慨大方、多富裕、多强势、多伟大无私美好。他会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会选择怎样的工作,会决定用自己的一生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这是沙哈尔老师抛给我们的一个问题。由于我们常常希望从别人身上得到自信、勇气、目标,但是当我们在别人眼中是隐形人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生活?这个练习是帮助我们不管他人的赞扬或者肯定,确定自己想要做什么。
“研究生毕业时,我的回答是:绝不会读博,因为它不是那么有意义。但我也告诉自己,在这样一个现实的世界,我需要一个博士学位在大学任教,这也是为什么我继续攻读下去直至最终拿到学位。我在毕业前做过类似练习,当时正要决定自己未来的发展。然后我就想,如果我在一个隐形的、没人知道的世界,我会做什么呢?答案是我会教书,不想搞研究。这也是我为何放弃选择终身制教授的原因。我面临了很多压力,尤其是亲朋好友,但我明白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
什么对你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能让你不在乎他人的肯定、赞扬、欢呼或者否定、批评?你的激情在哪?你到底想干什么? 10年或者20年后,你会设想自己在干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尝试着去回答的问题。而独立性自尊较强的人,更能够明确、清晰地回答这些问题。想想自己上一次废寝忘食地投入到一件事情中是什么时候?或者,很多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曾体会“忘我”的境界了。其实,似忘我投入的经历正说明了什么对你来说很有吸引力,这会帮助你决定未来的走向。
追逐名利,名利会离你远去;远离名利,它会追逐你而来。沙哈尔老师引用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可以用韦德伯格关于自尊的解释来理解:名利其实是对自我的赞赏、自信,如果一直追逐一个又一个的赞赏,它会离我而去,就像推石头上坡。下一个赞赏到来之前,石头会滚回原地,为了再次赢得赞赏,你就必须推动石头上更陡的斜坡。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斜坡会越来越陡。反之,如果远离名利、谦逊行事,时间长了,真正的、自我产生的赞赏会翩然而至。
其实,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能够回答“隐形魔咒”下自己究竟想要过怎样一种生活的人并不多。这个简单的问题背后,是我们对“生活的意义”、“人生的乐趣”、和“自身的优点”这三个重要问题的综合回答。
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一位大学导师问自己的学生:“你每天都在做什么?”学生很自豪地回答,“我从早到晚都在做实验。”他本以为老师会表扬他,但老师只是反问了一句: “那你什么时候思考?”越是被日常的琐事包围,我们的思考能力就越少,而这时候我们的服从性就会越高。有这样一个实验:
你坐在椅子上,手放在可以启动电流电击你不认识的实验者的按钮上。电压为60伏时,对面的实验者可能没什么反应;电压从75伏,每次增加15伏,直到120伏的时,对面的实验者会说:“好痛!”这时候你向旁边的指导者征求意见,他要求你必须继续实验。然后你继续增加电压,哪怕实验者已经开始痛苦的嚎叫,可你在指导者 “必须继续实验”的要求下,通常还是会继续增加电压。实验发现,指导者一直说“必须继续实验”的情况下,63%的实验者会将电压增加到350伏。但是,如果在电压增至75伏时,实验对象说:“好痛!”旁边的指导者要求你必须继续实验,但给你15分钟的休息时间,大部分人都不会再配合指导者的“继续实验”的指令了,因为在15分钟的暂时冷静的时间里,我们可以想:“我疯了么?干嘛留在这?”甚至会报警。但如果没有15分钟的缓冲时间,一直是“必须继续实验” 的命令在你耳边环绕的话,你可能会做出残忍的举动。
这种服从的现象在现代社会很普遍,一味服从,完成别人要求的事情,没有自己的意愿。因此,想象一个“隐形的魔咒”降临在你的身上,你会要怎样的生活呢?
谎言的成本
说到谎言,恐怕成年人中没有人敢声称自己从未撒过谎。有时候,说谎也是处于维护自尊,比如别人问我:“在美国生活得很轻松吧?”尽管事实是为了适应环境和拿到学位,我每天都生活得很辛苦很勤奋,比国内的同龄人要操劳十倍,但是我可能还是会回答:“是的,你知道,美国大学就那样。”不过,沙哈尔老师却很肯定地说:“我决不说谎。”
说实话听到这话我们都觉得他这句话本身就是个谎言,但他坚持解释为什么不说谎。“我的本科论文写的就是为谎言付出的代价,我当时是哲学协会的干事,对心理学中的自尊、动机等话题都很感兴趣。根据对亚里士多德和亚当·史密斯等哲学家的著作的研究,我发现人们必须为自己的谎言付出很高的心理上、情感上的代价。作为研究谎言的专家,我知道说谎的后果,所以我从不说谎。”但是沙哈尔老师说自己为了实验,也说过谎。
一次,他和人约出去吃晚饭,对方是母亲的朋友的女儿,一位很成功的经济学家。沙哈尔老自我介绍是搞心理学的,她似乎对心理学的知识很感兴趣,随口说:“有一位很有名的心理学家某某某,你知道吧?”其实沙哈尔老师根本不知道她说的是谁,但他当时还是微笑着说:“嗯……”,然后继续对话。约会结束之后,沙哈尔老师回家细想自己的谎言,从中思考谎言的价值和成本。
我们说真话的时候,其实在给自己传递一个信息:“我的话很有价值,很重要”。而如果我们经常说假话,我们是在给自己暗示:“我不是那么好,我想变成他那个样子。我必须知道那位心理学家,否则她对我印象不好。”坚持持续一周的时间来练习诚实正直,直到行为改变了我们的态度,我们才开始重视自己说的话,和自己交流,而不是在乎别人的看法。
谎言往往源于我们不懂得说“不”,面对外在的期待时,我们总是想通过一些违心的言行得到别人的肯定和赞赏。其实,我们要学会说不,才可以简化自己的生活。
沙哈尔老师在音乐声中用一位哈佛02界毕业生论文中的话做结尾:“你真实的潜能藏在灵魂的最深处,能传递智慧、克服紧张、焦虑的情绪。我知道它在那儿,因为我以前感受过。我也相信其他人拥有潜能,因为他们总是能创造奇迹。每个人都有无与伦比的潜能,如果能找到,它就会熠熠生辉。它在那儿,每个人都拥有。如果我们寻找、培养它,它会发出万丈光芒,甚至超越自我,成为类似沃伦·本尼斯和本德拉一样的人物。他们的光辉已经照耀到其他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