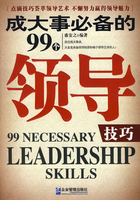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活在昙华林的那批人是幸运的。你们迈过了饥荒岁月,走在青春的大道上。你们充满朝气、拥有理想。你们是以纯洁的少年赤子之身,沐浴于马列文艺理论圣河、于其中膜拜接受灌顶。你们大都做着、或做过作家梦,梦想着诗人的桂冠,作家的华冕。你们自觉参加运动,批判美帝苏修,接受脱胎换骨般的改造,你们上未受日美英法文化的影响,下未被孔孟老庄浸淫,你们是最完整地接受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一代人……然而,残酷的事实却是:这一代人上不如胡风集团、右派文人,下不如知青团队、老三届哥儿们,你们的作家梦,真如昙华一现。你们之间,出了教授,出了官员,出了优秀教师也出了一些文人,但让你们汗颜的是:却没出一个叫得响的大作家、大诗人!当年北大学子、复旦精英……也一样全军覆没。要说老实话,当官员的也不过尔尔,当教授的也一般般,你们是当年曾经做过最绚烂的文学梦,尔后,则是遭受最彻底的毁灭的一代!当然,有机会问题,也有年龄问题,还有政策问题和其它众多的问题……回望昙华林,那么多优秀的老师,当年的辛苦,尽付之东流?那么多青年学子,当年的努力、全神马浮云?
你不知哪儿出了错。你写过有关艺术环境论、艺术群落论的文章,你也向冯牧老师请教过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但最后的结论却永远是太复杂,难说清。
你们这一代人,尤其这一代昙华林人,是多么优秀,多么敬业,多么能吃苦,多么能聆听教诲的青春一族呀!然而这一代人承受了太多的磨难,却唯独没有了“自我”,而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就是“自我”!这也许算是一种结论吧!
这是你的终生遗憾,也是你们一代人的终生遗憾!文化,是大自然的人化。在文化的五个层次里,艺术只是中间层次的存在。这种“自我”的缺失,并非要人去追求个人私欲,而是强调人生存在的映证意义!思念昙华林,即是思恋一种文化形态,思念昙华林、亦是反思一段岁月中的病态!
即便如此,青春仍然美好。即便如此,过往的岁月仍然令人怀念。在那明清风格的三层回廊加欧陆式钟搂的庭院里,你从婆娑的树影和迷茫的灯光中清晰地看到往昔,看到那身着长袍、脚趿布鞋的古典文学教授,看到那西装革履、手持斯的克的外国文学老师,看到那当时在国内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翘楚:一个以中青年为骨干、著作颇丰、影响甚大的群体。还有那教我们外语课的一对俊男靓女夫妻……你记忆中的老师们,以他们的人品、学识、智慧、风度影响着你,滋养着你,这是昙华林中永远的记忆,树影灯光中的恒远的辉煌。
你忘不了的还有那些青春伴侣!你的永远的那些不管贫贱和富贵,也无论健康或疾病都不将你放弃的铁哥儿们!他们多数来自乡村,却和你这个出自城市的不解世故的人结为朋友,他们多年来对你的帮助,就像昙华林的小溪,悄然自流,老樟树上的秋叶,飘飘坠地。连每次下乡,你笨拙得捆不好被褥,都是由他们代劳。直到多年后,每次由京外出,一清理行囊,你就想到他们的一片深情。
昙华林里有昙花吗?依稀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同学神秘地拉着我,在一个并不大的玻璃温室里看到它,在那儿了无生气地开放着。你印象里昙华林里最有代表性的植物,并不是那刹那即逝、不解风情的昙花,而是那无处不在、四季长青、挺拔高矗、蓊郁密闭的香樟。夏日里,它撑开绿色伞柄,遮挡了日炙曝晒,秋雨中它用厚实丰腴的叶片,和那雨丝沙沙交集,奏响一阕《清凉曲》。冬雪很稀罕,少见积淀,偶有厚积之处,大多在树干阴面和叶面,给整个院子,平添了几分对比浓郁的色彩。唯在春日,叶绿了,花开了,草青了,它却哑然无声,寂静依然。
然而,它却是你的最爱,在你数十年记忆中,它是昙华林中最香醇的酒,最恒远的花,现在很少能看得到像昙华林那样的香樟群落了,但在你的记忆中最深刻的香樟却是那在职工宿舍楼前,小山坡上的一株巨大的樟树。
那是一个初冬,南方的冬天,潮冷潮冷的。你和中文系的同学们拎着背包,来到钟楼前操场集中,好像是要去黄陂“社教”,系里的老师、领导,和你一道下乡的,也陆续来了,夕阳初度,北风乍起。落日处几束鳞片云,叫人看了心里发毛。这时,带队的老师告诉大家,系里留守的领导来送大家了!你的眼睛当即转向了那个小土坡,以及土坡上的虬枝直干、遗世独立的老樟树和树下站立的那个人。他穿着一袭铁灰色长呢大衣,身材修长,如玉树临风。颈脖处戴一条酒红色的围巾,手上戴着黑色真皮手套。他那时是系副主任还是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你也记不太清了。反正你只在外交场合,比如周总理会见某国元首要人之场面中才能见到类似的装束和风采。
你以为你对老师这种印象过于偏颇,而在生活中不过尔尔,但你问及很多人,都对他的温文尔雅、风流倜傥、和蔼善良的为人异口同声称是。也许,你对他所知有限,也许,你只看到事物的一面……但不管什么情况,那冬日樟树下的“惊鸿一瞥”却被你脑中的相机定格在那儿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你又和他见过几次,听过他几次讲课,文革中帮他买过烟,他被批斗期间,你还去看过他及夫人。文革后,你去北京读研究生,偶然在回鄂时还和他邂逅过。以后听说他出事了,以后就听说他去了深圳,以后听说他在深圳干得很出色,他的事迹广为传颂,以后就听说他患病去世的消息……你曾经很后悔,没有借个机会去深圳看他,也没有他一张照片。但后来一想,他是个善良的人,也是个非常能自省的人。你在他那些日子里去看他,他或许并不乐意。他在天堂有知,或许会温和的用那种略带吴侬软音的普通话,这样告诉你:就这样很好。
是的,就这样很好……
你有意没有提及众多老师和同窗的名字,是你觉得他们在你的记忆里就是一个群体。就像昙华林里的樟树群落。然而他们在你的印象里,却留下的是印象鲜明、各具特色的个体!别的不说,你在北京数十年从事的文艺批评职业生涯中,就常常在会议中、在写作时,在阅稿、交谈间,想起你的那几位教过你的文艺理论、现当代文学的老师们,因为你至今还记得他们的授课笔记。甚至清晰地记得他们在课堂上,以调侃的口吻告诫同学:文章写好后勿轻易拿出手,至少得给你老婆看看。这引起了大家的大笑:因为在座诸生是没老婆的。
然而你却不愿意、或者说不喜欢参加一些校友聚会。因为那一类活动突显了太多的势利、太多的等级观和太多的非校园情感!常常将一些莫名其妙的官员、伪文化名人(文化骗子)之类趋之为上宾,捧上高台,而将那默默奉献一生,忠实于教育事业的广大学友群体漠然置之。
师范大学不以师为范?
你不是要在这儿“惊回一枕当年梦”。你也并非在这儿声讨什么,你只是对你的昙华林倾泻你的思念。你的昙华林就是:樟树、钟楼、文华楼和师友。就是那迷离朦胧的树影灯光,就是那半个世纪不能、也未曾忘怀的岁月。你永远感恩于让你能进入昙华林的长者、使你在昙华林受益颇多的师长、和那些大有助于你的同窗!
昙华林!灯光朦胧、树影婆娑……
(丁道希,1963年入中文系。1978年在北京读研究生、工作直至退休。曾先后任中国文联研究室研究员,研究处处长,中国文联影视中心常务副主任;中联影视总经理)
寻回当年的文华楼
【杨昌庆】
文华楼被拆掉了,它毁于振兴中华、加速现代化建设的热潮中,楼龄已过“从心”之年,却未能“从心”,伤心地倒在无情的铁锤和冷酷的机械之下。
文华楼依花园山,面沙湖水。上世纪初美国人设立文华大学,文华楼便是主楼。解放后,文华大学旧址归属华中师院,文华楼仍然保持着主楼的地位。
华中师院校园不大,占二面土坡,据一片平地,建筑布局既规整有序又高低错落。平地的建筑宏伟大气,体育馆、教学楼、大礼堂,前后一字排列;山坡上的小楼别致精巧,用于阅览、办公、教研,亦前后一字排列;沿南坡而下,几座欧式民居如珠玉撒落在绿树丛中。一眼望去,只见重重叠叠楼、弯弯环环路,高高下下树。路是一色的石子小径,楼没有一座相似。
文华楼是一座四面围合的庭院。灰色、陈旧的外墙单纯得除了有几个小窗外,就像四个巨大的水泥块,使人感到稳重、坚固。由石砌的大拱门进入院内,并不觉幽暗。天井宽阔,高大的玻璃窗构成的墙面反射着阳光,既好看又明亮,削弱了围合建筑的闭塞和压迫感。
文华楼南、北面是对称的二层,一楼是教室,二楼是宿舍;东面二层,皆为宿舍;西面三层多作教室。东西南北,有走廊相通,去上课,回宿舍,均在数十步之内。西面三层以上钟楼高耸。天井中有树二株、井一口。树是中国庭院中常见的桂与梅;井水清澈,供同学洗漱、浣衣。东北角有一甬道,墙角处镶着一块刻有“1903”的石碑,标志着文华楼生命的开始。向左拐是利用楼的外墙搭建的浴室。向前数步则是厕所。再右拐,有一条短而窄的走廊直达食堂。这里还是信息中心,墙上挂着班级信箱,黑板上写满通知、启事。各种生活设施,紧密相连,结为一体。要说这儿的生活,那真是太方便了。近乎封闭的环境,影响着每一个人,容易养成恬淡闲逸,心气平和的人生态度和不急不躁、不徐不疾的生活习惯。
住在文华楼,冬天,没有寒风冻指裂肤,但也很少能晒到太阳,感觉十分阴冷;夏日,风吹不进院子,白天还有点阴凉,夜间却格外闷热。宿舍成了蒸气的浴室,蚊子的酒吧,臭虫的饭店。热得人难耐,痒得人心烦。不过,办法也还有,更深夜静时,悄悄遛出宿舍,提一桶井水,从头上淋下,在走廊上席地而卧,于是,凉爽爽浑身舒坦,乐滋滋半宿好梦。
文华楼里,同学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解读历史的发展和文艺作品,用**的日记规定自己读什么,说什么,做什么。“反修防修”、“兴无灭资”、“又红又专”、“改造思想”成了每周班会的一贯议题,组织和个人谈话的不变内容。文华楼就像一座熔炉,要把我们炼成钢铁,化作螺丝钉。
谁也说不清同学们的思想是否被“统一”了,行动是否被“革命化”了。但是,同学之间的互助友好却是具体的、真实的。如果你有事,总会有同寝室的同学帮你去食堂打饭;要是你因病缺课,总会有同学将整理好的笔记送到你的面前;一日三餐,总会有女生主动将自己定量的粮食分给男生一半;每到开学,同学总会把从家乡带来的土特产品拿出来让大家分食共享,从此,我才知道了沙洋的花生大而香,孝感的麻糖甜又脆,巴东的香肠麻且辣。
生活在文华楼,各人有各人的故事,但让人津津乐道,流传至今的当数《文华楼里看风景》。那风景就是每当午餐,楼上楼下的男生端着饭碗,或倚墙,或凭栏,满脸兴奋,目光贪婪,屏息欣赏一位女生从楼下走过。她是才女,据说是老师们的评价,口耳相传;她是美女,那是亲自目睹,眼见为实。有人说她友善、温和,让她的美丽更有魅力;有人说她矜持、高傲,使她的俊俏越具神秘。除了赞美,还是赞美,只有赞美。不管怎么说,从文华楼走过的她的确值得一看。那轻盈,那优雅,清丽端庄,娴静从容,像一缕清风徐徐吹来,又像一朵白云轻轻飘去……观景的人只顾观景,哪里知道他在欣赏美景时,也成了风景,被另外一些人欣赏着,成为人们百听不厌的故事。真是非常的有趣。
文华楼被拆掉了,它的一砖一瓦都当作垃圾而被清除,未留下一点痕迹。我希望能寻回当年的文华楼,哪怕只是几块记忆的碎片。
(杨昌庆,1961年入中文系。武汉理工大学教授。曾任武汉汽车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静静的昙华林
【周涤非】
昙华林地处武昌东北隅。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即55年到56年的那第一个学年得与昙华林朝夕相伴的。那一年多的岁月似乎应该是此生很珍贵很难得的一段时光。那时的武昌城区很小,仅褊狭的一绺,昙华林几乎已是城区的边缘地带了,记得校区院门外数步之遥就是一畦连一畦的碧绿的菜地。她与粮道街、胭脂路接壤为邻,但她既不蘸“粮道”的繁嚣,也不染“胭脂”的氤氲,实在称得上是闹市中的一方净土。栖宿昙华林一年多,实在没亲见过昙花,更不用说其“林”了,镌刻在我心中的昙华林,给我留下不泯印象的昙华林就是一个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