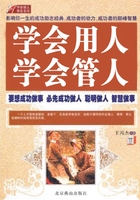一个行业每出现一位大家,这个行业便出现了一个新的标准,有了一个新的文化高度。就戏曲而言,这个标准就具体体现在一个个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之中。在楚剧历史上,高月楼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高月楼之高,功高至伟。李雅樵之成为李雅樵,是因为有一个个高人不断提携加上自己不懈努力的结果。李雅樵拜高月楼为师,并成为高月楼的上门女婿之后,老泰山的提携和亲授,加速了他在艺术上的发展。
高月楼先生是一位演戏的奇才,他在舞台上的表演情绪饱满,张弛有度,驾驭舞台节奏的能力非常强,瞬间,可以把舞台的气氛从零度推到沸点。他不是一出两出戏演得好,可以说,无论哪出戏,只要由他来演,就可以将戏演活,演得精彩纷呈,耐人寻味。他的表演兼容性极强。不仅演古人,也演今人;不仅演中国人,也演外国人;不仅演本行(即小生行)的,也演其他行的,甚至年龄跨度极大的角色。
抗战胜利,在大后方演出、阔别武汉8年的沈云陔、高月楼回到了武汉。经过短暂的休整,他所在的问艺楚剧团和在汉口正当红的年轻的关啸彬组成新的“民乐楚剧团”。1946年9月,新组合在“民乐”剧院隆重开张,大汉口的戏曲市场,出现了新格局。此时,在“美成”领衔并担任后台经理的李雅樵,遇到了空前的挑战。两个剧场相距不远,上演的剧目大同小异,演员阵容却相去甚远。新组建的“民乐”,除了老伶王沈云陔、高月楼外,又加盟了正年轻、扮相好、嗓音甜的新伶王关啸彬。这意味着“新民乐”对新老观众都有吸引力。年轻气盛的李雅樵,遇到了他从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这个时期与李雅樵合作的演员是张玉魂、花艳秋,主要班底是蔡艺飞、张云侠、雷明月、筱艳云、筱玉魂(即詹玉魂)。由于两家上演的剧目大致相同,都是《大访友》、《白扇记》、《大辞店》、《二戏楼》、《天宝图》、《九人头》等老戏。为了竞争,李甚至赤膊上阵,直接演汉剧《打鼓骂曹》、京剧《千里走单骑》、《华容道》以及济公戏。1946年的下半年,高演《七侠五义》,李演《七侠五义》,高演《征东》,李演《征西》,李雅樵甚至反串花旦,在《征西》之《三请樊梨花》里饰樊梨花。1946年12月13日《罗宾汉报》刊登的两则楚剧海报耐人寻味:
“美成”上演《薛丁山征西》(主演李雅樵),“民乐”上演《薛仁贵征东》(主演高月楼)。
李雅樵面对的是一位艺术全面、影响力远在他之上的巨匠,“美成”的票房明显敌不过“新民乐”。面对高月楼,李雅樵没有退缩,他性格里总有股“不服周”的犟劲。
1947年上半年,李转到天仙戏园演出,上演了武戏《哪吒闹海》,他饰演哪吒。这在楚剧历史上是个开先例的举动。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他和剧种内的同行比,步子迈的大得多。一方面是他年轻气盛,有一定实力;另一方面,他对门“天声”戏园,就是刘五立当家的京剧团,李雅樵没事就去看他们的戏,还请京剧武行师傅来教戏并参与演出。这种借鉴和学习,给成长中的李雅樵帮了忙。后来,李雅樵在他的《业务自传》里写道:“那时我正年轻,总想显示自己‘懂得多’,不大讲‘款’,像汉剧的《二王图》,京剧的《华容道》、《过五关》、《击鼓骂曹》这些戏我都唱。我们长期聘用京剧的武戏师傅来为我们作指导,甚至还演《哪吒闹海》这类大打出手的武戏。”
抗战胜利后,沈云陔、高月楼等一批有威望的艺术家由重庆回到武汉。李雅樵说:“看了他们的演出,我们(敌占区的楚剧同行)十分钦佩。不久,我与关啸彬便参加了他们的戏班。沈、高二位老师对我与关啸彬很器重,也肯于提携,一有机会就与我们谈戏、谈人物、谈表现手法。后来,关啸彬参师沈云陔,高老师与我则成了翁婿,关系密切,我艺术上更加获益。这段时间里,我除了演一般戏外,还演了《蔡伯喈》、《薛丁山征西》等。在《潇湘夜雨》里,高月楼老师演崔文远,我演崔通,在《包公》里,我演前面‘断太后’,他演后面‘打龙袍’。高老师演戏,舞台效果极其强烈,他善于挖戏,没戏的地方他却能找出戏来,表演非常细腻,观众非常喜爱,他对我可说是言教身传,我虽然嗓音好,却怎么也压不过他。”
1947年下半年,李雅樵、王天佑、钱德森、杨少华等合并到沈云陔所在的“新民乐”楚剧团,李雅樵开始与高月楼、沈云陔、关啸彬共事,演出《打潼关》、《征东》、《征西》、《七侠五义》等连台本戏。在《七侠五义》中饰展昭、白玉堂、包公、蒋平,在《征东》、《征西》里,饰薛仁贵、薛丁山、杨樊等角色。新组建的民乐楚剧团有130余人,阵容空前强大。为了把新的团队统一管理起来,大家公推王若愚为主席,起草了《“民乐”业务检讨委员会简章》。那一年李雅樵25岁,高月楼40岁。无论从年龄、精力还是条件,李雅樵都占先,但是,他无法超越高月楼,他面对的不是一座楼,是一座山。
高家一门演艺精英,高月楼的侄儿高少楼,也是楚剧历史上独树一帜的“千面人”。合团以后,唱全本《吴汉杀妻》,从“打潼关”一直唱到“起解”,到了“堂楼”才是高月楼出场,戏码一直是这样派。王天佑回忆道:“一次,高月楼在后台盘高少楼的伢玩,忘了化妆。李雅樵唱完了前头的戏跑过来催他说,师傅,您还不上场?高月楼说,你把‘堂楼’唱了它。李雅樵一听,不甘示弱,就把应该由高月楼唱的吴汉见王兰英的戏唱了,观众反应也蛮好,这一唱就显示了李雅樵的潜力。”这就透露了一个信息:高月楼的戏李雅樵能顶。
1948年,熊剑啸、袁璧玉离开了问艺楚剧团,当时正在唱《七侠五义》。这个戏的蒋平是熊剑啸唱的,蒋平说服白玉堂有一段嚼白,别人说不好。唱《七侠五义》,高月楼饰白玉堂,李雅樵肯定饰展昭,蒋平走了怎么唱?李雅樵就改唱武丑蒋平,结果李雅樵唱的蒋平嚼白要了个满堂好。王天佑回忆:“我还要感谢熊剑啸,李雅樵顶了熊剑啸的丑角,他演展昭的任务就落到我头上了,熊剑啸一走,把我抬高了。”
1949年2月,李雅樵与高兰珍结婚,成了高月楼的上门女婿。翁婿二人先后有近7年的时间,一起生活,一起演戏,谈天论艺,高月楼的艺术见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李的艺术观。以后,李雅樵的高明之处也证明,他用了高月楼的东西,还看不出来是高月楼的东西。李雅樵站在泰山肩上向更高处攀登。
武汉市楚剧团的老同志都记得,1954年,北京京剧团到武汉演出,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都来了,他们招待楚剧演了一场戏:裘盛戎的《坐寨盗马》,谭富英的《打棍出箱》,李多奎的《望儿楼》。楚剧招待他们的是《潇湘夜雨》。这个戏是麒麟童的戏,沈云陔、高月楼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移植成了楚剧。高月楼演《潇湘夜雨》的崔文远,沈云陔饰翠兰,李演崔通。戏中“跑伞”是个过场戏,高扮演的崔文远,在风雨中行走,拿着伞走一个高“吊毛”,到最后下场时,因无法把伞撑开,人跪在伞里一步一步挣扎前进,那个表演真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就是剧中的“联弹”,都是满堂好!幺了锣,这几位京剧大家都到后台,非常赞赏楚剧的舞台艺术,尤其对高月楼演的崔文远啧啧称羡。这里提到的“联弹”,京剧演《潇湘夜雨》是没有这种搞法的。沈云陔、高月楼在20世纪40年代移植的这出戏,记录了楚剧在表现手段上很多宝贵的经验。
周信芳看过高月楼在《九件衣》中演的申大成。看完戏,他跑到后台对沈云陔说,你们这个申大成了不得。他举个具体的例子说,申大成到夏玉婵家里去借衣服的时候,是个夜晚,桌上点了个油灯,夏玉婵去拿衣服,顺手把灯盏拿了下场。灯盏一拿下去,高月楼马上表现出台上漆黑一片的感觉,他用手到处摸板凳,坐着,等他的表姐出来。夏玉婵转来,灯一亮,他马上又感到有光亮了。周信芳说,这就是一个演员了不起的地方。后面公堂上审九件衣时申大成的表演,那也是一绝。李雅樵当时在剧中演花二。
50年代,这翁婿二人,高演《宝莲灯》的刘彦昌,李演沉香,以后李演“华岳庙”小生刘彦昌,高演“二堂”“打堂”老生刘彦昌。至于连台本戏《七侠五义》的展昭、白玉堂、包公,《征东》、《征西》的薛仁贵、薛丁山、杨樊等角,均是高、李前后轮换饰演。经年累月零距离向大师学戏,李雅樵如坐春风,大获裨益。
50年代,高月楼、李雅樵翁婿,在为楚剧创造辉煌的同时,也在完成新老两个时代的交接。
高月楼死得太早了,47岁死于胃穿孔。1955年3月的一天,高月楼白天演完《宝莲灯》的刘彦昌下来就吐血,抬到二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单。后来开了刀,胃病似乎好了。学生们去看他,他还说,我好了还要教你们戏的啊!没过几天,3月18号就走了。那时李雅樵正带队在南昌演出,接到信赶回来时,高已落了席。高先生的送葬规模,在武汉戏曲界绝无仅有。楚剧元老级的人物全体执绋送其上路,戏曲界同仁同致追悼,武汉市市民共为哀惋,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发来唁电。送葬的那天,高的灵柩途经中山大道,沿街的商店、行人自发地摆起香案设祭,鸣放鞭炮为其送行。送殡的人流,延绵十里不断。
望着为高月楼送葬的队伍,时任武汉市文化局戏改处负责人的巴南冈深有感触,他记起搞戏曲改革刚刚发生的那些故事。楚剧老本《蝴蝶杯》,田玉川有两个老婆,“戏改”为了去掉“两房老婆”的情节,全剧只唱到前面公堂就幺锣了,后面田玉川逃难的戏就删掉了。结果,观众不答应,说戏冇唱完,1700人的剧场,观众不退场。那天,高月楼和沈团长的戏演完回去了,怎么办呢?赶快派人到家里去喊二位来。高家离剧场近,听说这样的事,“蹬蹬蹬”高月楼赶到剧场,从观众席直奔舞台。见到高月楼来了,观众一个劲地拍巴掌,剧场再次沸腾起来。随后,高月楼与沈云陔加了一出《玉莲汲水》,才算满足了观众的情绪。
送殡的现场,巴南冈再也看不到高月楼了,他看到的是高月楼在观众心中的影响,观众对楚剧的热爱。
他把眼光投向了一身重孝的李雅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