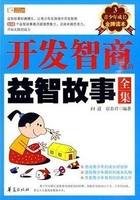安妮起床时天已经大亮了,她困惑地注视着窗口,快乐的阳光如潮水般涌入窗户。窗外,蓝色的天际中涌动着柔软如羽毛的白色。
有一会儿,她不记得自己在哪儿了,先是一阵快乐的战栗,然后就是悲伤的记忆,这是绿山墙农庄,这儿不要她,因为她是个女孩子!
但,现在是早晨,而且,窗外是怒放的樱桃,她跳下床,把窗户向上推——窗户吱吱呀呀晦涩地开了,好像很久没有打开过了,根本不用东西支撑。
安妮跪在窗口,凝望着6月的清晨,眼神闪耀着喜悦,噢,太漂亮了,真是可爱的地方,要是她真的能留下来!她可以想象她留下来的,这儿有想象的空间。
外面有一棵硕大的樱桃树,枝条轻轻地拍打着这幢房子,花长得非常茂密,根本看不见一片树叶。屋子两边都是果园,一边是苹果树,一边是樱桃树,都开满了花朵。草丛间密密地洒落着蒲公英。下面的花园里是紫色丁香花儿,芬芳的香气顺着清晨的风飘忽到了窗口。
花园下方的坡上是青葱的苜蓿,一直延伸到小溪流淌的山谷中。在那里,伤痕累累的白桦轻盈地跳出了能引出美妙联想的低矮的蕨苔丛,还有许多树林里常见的植物。再往上,就是一座毛茸茸的绿色小山上的云杉和杉树,那儿有一条小沟,还有昨天她在阳光水湖另一边看见的那座小房子的灰色山形墙。
左面看出去是座马棚,而再往远处,缓缓的绿色田野之外,是闪烁着蓝光的海洋。
安妮可爱的眼睛四处游移,她贪婪地吸取一切美景,她的一生看过了太多不可爱的东西,可怜的孩子!但是这一次,她看见了梦想中的一切美好的东西。
她就跪在那儿,迷失在美景之中,直到有一只手放到了她肩上——玛莉拉无声地来到了这个小梦想家的身边。
“该穿好衣服了。”她简略地说。
玛莉拉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和孩子相处,她的一无所知让她显得很干脆草率,但是她本不打算这样的。
安妮站起身来,深深吸了口气。
“太棒了,对吗?”她说着,向外面的世界挥手。
“一棵大树,”玛莉拉说,“花开得很好,但果实不多,小,而且有虫蛀。”
“哦,我指的不是这棵树,当然它也很可爱,非常可爱,但我指的是所有的一切,花园、果园、小溪、树林,这完整的宏大的可爱世界。难道您不喜欢这样一个清晨的世界吗?我能听见小溪一路上的欢笑。您有没有注意过小溪真是个很快乐的东西呢?它们总是在笑,甚至冬天我都能听见它们在冰下的笑声。我真开心,绿山墙附近有条小溪呢。可能您觉得反正我也待不长,根本没什么区别吧,但不是这样的,就算是我再也看不见它了,我也会很高兴地想起这儿有一条小溪的。要是没有的话,我会觉得很不舒服,这儿应该有条小溪嘛。今天早上我已经没有很绝望的情绪了,我早上从来不绝望,清晨是很美好的,对吗?但是我觉得悲哀,我希望我是您想要的孩子,我会永远留在这里,永远地,要是这样的好事能停留该多好啊。想象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当它不得不结束的时候,就是种伤害。”
“你最好还是穿好衣服下楼,别管你的想象了。”玛莉拉终于找到了插嘴的机会,“早饭做好了。洗洗脸,梳一下头发,就让窗户开着,收拾好床,手脚麻利点儿。”
安妮显然很麻利,这么多事,只是十分钟,她就下楼了,衣服整洁,头发梳成了两条小辫,脸也洗过了,完成了玛莉拉的要求,她觉得很满足。事实上,她忘记收拾床了。
“今天早晨我饿了,”她宣布说,坐在了玛莉拉替她放好的椅子上,“这世界并不是昨天晚上看见的一片荒野,我很高兴今早阳光灿烂,但其实我也很喜欢下着雨的清晨呢。什么样的早晨都很有意思,对吗?你不会知道今天都会发生什么事,这么多想象的空间。但是我很高兴今天不下雨,这样容易快乐些,阳光灿烂的日子不会承受太多苦恼,我觉得我能承受很多很多呢。看书时读到一些苦恼,然后想象自己坚强地克服了它,感觉很不错。不过,要是真的有苦恼的话,就不太好了,是吧?”
“很遗憾,还是管管你的舌头吧,”玛莉拉说,“小女孩说这么多实在是太过分了。”
于是安妮闭上了嘴,她的舌头如此顺从,以至于她的沉默弄得玛莉拉神经不安,觉得很不自然,马修也闭着嘴,这是很自然的,所以,这是顿安静的早餐。
安妮越来越心不在焉,她机械地吃着饭,大眼睛却出神地盯着外面的天空,这让玛莉拉更有点神经质了,她觉得这孩子人在桌边上,精神却已经被想象的翅膀带到了遥不可及的云端,这附近谁会喜欢这种孩子呢?
马修还是想留下她,简直不可理喻。玛莉拉觉得今天早上的他并没有改变昨天晚上的看法,他还是想要她。这就是马修——把一时稀奇古怪的想法装到脑子里,然后就是用让人惊讶的沉默来坚持——这种极端沉默的固执往往比他说出口时更为有力,而且有效。
吃完了饭,安妮回过神来,说要洗盘子。
“你会洗吗?”玛莉拉不信任地问。
“洗得还很好呢。我也会看孩子,我已经很有经验了。真可惜,您没孩子给我看。”
“我不觉得我需要人看孩子。你已经是个麻烦了,我真不知道拿你怎么办。马修真是个可笑的人。”
“我觉得他很可爱,”安妮反驳说,“他富有同情心,他不介意我说多少话,他喜欢我说话。我看见他时就觉得他跟我志趣相投。”
“你们都很古怪,不错,这就是你们的志趣相投。”玛莉拉嗤之以鼻,“你洗盘子吧,拿上热水,然后要擦干。早上我有很多事,下午还要去白沙见斯宾塞太太,你跟我一起去,然后我们看看该拿你怎么办。洗完盘子以后,上楼收拾你的床。”
安妮洗盘子很熟练,玛莉拉则用锐利的目光密切地注意她洗盘子的全过程,她的床收拾得没有这么好,因为她没有叠羽绒被子的经验,但无论如何,她还算顺利地收拾好了,玛莉拉为了摆脱她,告诉她可以出门玩儿到中午吃饭。
安妮溜到门口,脸色和眼睛都在发亮,到了门槛上,她却停了下来,绕了几圈,回到桌边坐下了,神采全熄了,就像有人在她身上洒了灭火剂一样。
“现在又怎么了?”玛莉拉问。
“我不敢出去。”安妮说,语气像一个放弃了所有尘世间欢乐的殉教士,“我在这儿没有用处,是待不长的。我要是出去了,和树、花、果园、小溪都混熟了,我就会爱上它们。现在我已经很难受了,我不想让自己更难受。我的确很想出去——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在召唤我,安妮,安妮,来吧。安妮,安妮,我们需要一个玩伴。但还是算了吧,要是注定要分开的话,还是不要去爱,对吗?让自己不去爱也很难,是吧?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要住在这儿会那么开心的缘故了。我以为我会爱上如此之多的事情,没有东西拦着我。但是短暂的梦已经结束了。现在我向命运屈服了,我不出去是因为害怕我自己再次不愿意屈服。窗台上的天竺葵叫什么名字?”
“苹果香天竺葵。”
“唉,我不是指的这种名字,我指的是您给它取的名字。您没有给它取名吗?那么我给它取吧!我叫它——让我想想,漂亮爱人,我可以叫它漂亮爱人吗?求您了!”
“上帝,我才不在乎呢。给天竺葵取名字有什么意思?”
“就算是天竺葵,我也喜欢它们有自己的名字,就像人一样,要是您只叫它天竺葵的话,您怎么知道您没有伤害它呢?要是人家光叫您女人的话,您也会不高兴。那么,我就叫它漂亮爱人吧。卧室窗户外面的那棵樱桃树,我叫她白雪王后,因为它很白。当然啦,它不会老开花的,但可以想象它总是开花嘛,对不对?”
“我从没见过这种人,”玛莉拉嘀咕着,逃跑似的到地窖里去拿土豆,“马修说得对,有意思的人,我都想知道她下面要说什么了,她也能把我给蛊惑了,她已经迷住了马修。他出门时那一眼已经又把昨天晚上说的话又说了一遍了,真希望他和别的男人都一样,有什么话都说出来,这样人家可以回答,可以争论,可以讲道理,但是,人家拿只会看不会说的人怎么办呢?”
安妮又陷入了幻想,她的手托着下巴,眼睛凝望着天际。玛莉拉从地窖回来就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直到正餐摆在桌子上。
“我想下午用马车,行吗,马修?”玛莉拉问。
马修点点头,闪着希望的光芒的眼睛看了看安妮,玛莉拉阻止了他的眼神,残忍地说:“我驾车到白沙,把这事给解决了。安妮和我一起去,斯宾塞太太可能会安排她立刻回新斯科舍,我会把你的茶准备好,挤牛奶的时候我就该到家了。”
马修还是没说话,玛莉拉觉得自己简直是在浪费口舌,没有什么事比男人不回答更让人恼火了——除非女人不想让他回答。
时间到了,马修套好车,玛莉拉和安妮准备出发了。马修打开院子门,她们缓缓地驶过去,他突然开口了,但好像并不是跟她们说话,“克里克的小杰里·布托早上来过了,我告诉他,我夏天可能要雇他干活。”
玛莉拉没有回答他,她恶狠狠地给了倒霉的马一鞭子,肥肥的马从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它愤怒地穿过小路,速度快得让人担忧。玛莉拉从马车里回过头来,看见恼人的马修靠在门上,充满渴望地注视着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