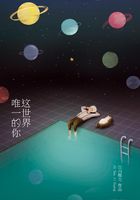孟冬十月,北风徘徊。天气肃清,繁霜霏霏。鹍鸡晨鸣,鸿雁南飞。鸷鸟潜藏,熊羆窟栖。钱镈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乡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难。锥不入地,丰籁深奥。水竭不流,冰坚可蹈。士隐者贫,勇侠轻非。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两首诗主要是以结构独立而意思连贯的四言句来写景抒情,其中“鹍鸡晨鸣,鸿雁南飞”,“水竭不流,冰坚可蹈”等诗行,虽然前后句句法相同,两两相对,但各句意思却是独立的,类似于一句一意的五言诗句。曹操四言诗中完整独立诗句的增多和复叠排沓句式的减少,有利于加大作品的意义容量,从而强化了四言诗体“文约意广”的特征。故沈德潜言:“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版,103页。
建安之后,嵇康上承曹操,为正始时期又一位四言大家。许学夷以为嵇康四言诗“得风人之致”,而其五言“或不免于矜持”。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85页。王夫之也曾说过:“中散五言,颓唐不成音理,而四言居胜。”王夫之评选,张国星校点《古诗评选》,卷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83页。后者对嵇中散五言诗未免贬抑太过,但嵇康的四言创作成就确乎是远远超出其五言、六言、楚歌体诗的。“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颜延之《五君咏》,载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上册卷二一。据《世说新语·容止》记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嵇中散生性清超峻洁,“不喜俗人”,亦不以仕宦为怀,临刑尚要“援琴而鼓”,并为“雅音于是绝”而叹惋。
这样一位从里到外都卓尔不群、超凡脱俗的“非常”之人,追求的是一种与道逍遥的艺术人生,其风采、气度大致可以折射出他的审美理想:清远、自然、峻整、绝雅。嵇康四言诗中的人物形象清雅绝俗,意境也极为幽雅旷远。在地理空间上远离尘嚣,寄身于山林草泽,或与隐者高士为伴;在心理时间上远离现世,“抗心希古”,“托好老庄”,要在诗中包含如此旷远的时空,难免篇幅增大。如《代秋胡歌诗》七章共八十四句,《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章共一百四十四句。在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中的人物形象洋溢着得道者的风采,他们或者乘良马,驾轻车,“风驰电逝”,“顾盼生姿”,“仰落惊鸿,俯引渊鱼”,或者“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或者以四海为宅,与松乔同游,抛弃了一切纷纭世故。
《世说新语·雅量》记叙了这样一则小故事:东晋桓温欲诛谢安、王坦之于宴席之间,谢安“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史载桓温“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侧,在位望者,战栗失色”,这样一位权臣却能为谢安的“旷远”所折服,岂不以中散清雅之诗更助谢公渊雅之量邪?
东晋末年,陶渊明再度使四言诗放出异彩。宋代刘克庄曾说过:“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陆士衡后,惟陶公最高,《停云》《荣木》等篇,殆突过建安矣。”刘克庄撰,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前集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近人郑宾于亦认为陶渊明“不特是五言的宗匠,也是四言的翘楚”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第二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7-58页。。
陶渊明对四言诗的一大创举是将其从冗长巨制、日趋呆滞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使它重新回到篇幅精短、表现灵活的道路上。四言“文约意广”的特点符合魏晋时人们追求的风尚,但对四言诗体的选择很快使诗人们陷入一种难堪境界:四字一句的诗体固然在句式上获得了“简约”,却难于很好地表达日益丰富的生活内容和人类感情,难于收到“意广”的效果。为了弥补因句式“简约”而带来的缺陷,诗人们有意无意地加长了诗歌篇幅。把《诗经》、曹操四言诗与嵇康、陆云四言诗进行比较,这种篇幅越来越长的发展趋势是极显然的。粗略统计,《诗经》中除了《大雅》和《颂》的一些诗歌篇幅较长外,《国风》和《小雅》的绝大部分作品篇幅都很短,《国风》绝大多数诗歌篇幅在十二句到二十四句之间,《小雅》绝大多数诗歌篇幅在三十二句到四十八句之间。
曹操的四言诗篇幅也较精短,最短的《善哉行》是二十八句,最长的《步出夏门行》四章共六十四句,与《诗经》的篇幅相近,但已有增长的趋向。发展到嵇康时,四言诗的篇幅明显增长了,如《代秋胡歌诗》七章共八十四句,《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章共一百四十四句。陆云四言诗篇幅比嵇康诗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如《答孙显世诗》十章八十句,《答兄平原诗》甚至达到了二百四十二句的长度。这种动辄近百句甚至上百句的鸿篇巨制,虽然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四言句式过于短促容量不足的缺点,却因此而出现了“文繁而意少”的毛病,使本来灵活自由的四言诗呆滞化。追求句式的简约却带来了篇幅的冗长,这一矛盾决定了四言诗在魏晋时代繁荣复兴的同时,也给四言诗的衰微敲响了丧钟。
陶诗则不同,除《命子》一篇较长,共有八十句外,其余都是较为简短的作品,如《停云》《时运》《荣木》《归鸟》《赠长沙公》等五首均为三十二句,《答庞参军》《劝农》为四十八句,而《酬丁柴桑》则仅有十四句,与《诗经》的篇幅基本相同。陶渊明四言诗篇幅的精短化,使四言诗从冗长呆滞中解放了出来,前人对陶诗的这一转变作了不少精辟论述。钟嵘虽然只把陶诗列为中品,但对陶诗的精短特点非常推崇,誉称之为“文体省静,殆无长语”。明人许学夷认为:“靖节诗不为冗语,惟意尽便了,故集中长篇甚少。”诗歌篇幅的精短化,是陶渊明四言诗在形式上的最重要特色。
陶渊明四言诗变魏晋四言诗的古质典雅为清淳淡远,把行将呆滞的四言诗体变得自由灵活。魏晋诗坛由于受玄风务求古雅的影响,诗歌风格上出现了对古质典雅凝重的追求。钟嵘《诗品序》中认为当时诗坛“贵黄老,尚虚谈”、“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并指出“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经》”。而评论到具体作家时,也多用“古雅”来概括当时作家的创作风格,如评曹操诗为“古直”,应玚诗为“善为古语”、“雅意深笃”,这些都概括了当时的普遍诗风。
陶渊明诗也受到这股务求古雅思潮的一些惯性影响,在个别作品中表现出古雅的特点,如叙写“悠悠我祖”的《命子》诗,前半部分就被前人称为“雅穆”、“安雅”,但这并不是该诗的主要特色,更应值得我们注意的应是诗歌的后半部“抒写淋漓”、“笔腾墨飞”的特色。在陶渊明四言诗中,最主要的风格特点应是清淳淡远,他曾在《五柳先生传》中自称“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又在《与子俨等书》中说:“少好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更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欣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如《停云》《时运》等篇,就被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称为“清典简远,别成一格”的佳作,试看《时运》一诗: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
诗中虽有“黄唐莫逮”之叹,但整首诗的“清闲淡远”的风格是极其明显的。其中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花药分列,林竹翳如”等句子,不仅状物工肖,而且能透过这些清新自然之景流露出无穷的韵味。其他的四言诗风格也是如此,如“冬曝其日,夏灌其泉。勤靡余荣,心有常闲”等等。甚至飞鸟都被笼罩上了一层闲静色彩:“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他的《赠长沙公》被清马璞《陶诗本义》卷一称为“情真语朴”,《答庞参军》被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评为“通首隽逸轻清”,《劝农》被清张谦宜《现斋诗谈》卷四《评论》称为“词淡而意浓”等等,所有这些论述都表明了陶渊明四言诗的清闲淡远的艺术风格,读陶渊明四言诗自有一种清和婉约之气在笔墨外。
刘克庄曾说过:“诗四言尤难,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而在四言复兴的魏晋时期,曹操、嵇康、陶渊明都以自己独特的心智、才能、个性、情思浇灌了这一古老诗体,使之再现辉煌。魏晋时期,四言诗的黄金时代早成过去,因而锐气大减,已呈弱势,只能退居于一些特定领域发挥余热,或渗入其他文体去派用场,所表现的主要是某些带有“古”、“雅”色彩的内容,难以满足反映多彩现实的需要。而且这一诗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已没有多少潜力可以发掘,诗人“难于其中自出新意”,于是“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王国维《人间词话》,谭汝为校注,北京:群言出版社,1995年,第47页。尽管此时出现了有利于四言诗滋长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少数有才力的诗人也创出了一时之新,但终究无法挽救其衰落趋势。与此同时,五言诗却正如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渐至中天,这一诗体是应表现新内容、新情感的需要而产生的,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广大的拓展空间,它在玄风盛行时已经“腾踊”诗坛,而在“庄老告退”后更是独领风骚。章太炎说:“《三百篇》者,四言之至也。在汉独有韦孟,已稍淡泊。下逮魏晋,作者抗志,欲返古初,其辞安雅,而惰弛无节者众……非其材劣,固四言之势尽矣。”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见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