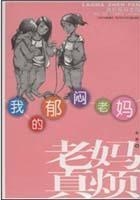四言复兴
四言诗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形式,也是流衍最长久的古代汉语诗体。西晋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说:“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四言诗的黄金时代是在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诗篇,它们集中保存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
就艺术成就而言,魏晋四言诗虽不如《诗经》那样硕果累累,却也往往能披沙砾金;在诗体风貌方面,本时期四言诗既表现出《诗经》以来四言诗所共有的简单质朴、自然和美、慢声缓气、一唱三叹等体貌特征,又自具时代特色。但历代的诗文选集都很少从中选录作品,与轰轰烈烈的《诗经》学相比,此片诗丛一直“寂寞沙洲冷”。有鉴于此,此节我们将对四言诗进行探讨。
魏晋时期是四言诗创作繁荣与复兴的历史阶段。魏晋短短二百多年中,共有四百多篇合九百余章四言诗留存至今。与两汉四百余年流传下来的约百篇四言作品相比,魏晋四言诗在数量上呈现出激增态势,若按一章即为一首的惯例来计算,完全可与当时的五言诗并驾齐驱。魏晋时期四言诗的繁荣复兴,是中古诗坛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于是,这里便有一个问题凸现出来:魏晋四言诗何以再度兴盛?
魏晋四言诗复兴首先和玄学清谈密切相关。玄学贵尚虚无,玄学家在社会生活和谈理著论中追求以尽量少的言辞和物象,表现出最丰富、最深邃的意旨,力主“得意忘言”、“得意忘象”。反映在诗歌体裁的选择上,辞句简朴、意赅旨远的诗体无疑会大受欢迎,而这样的体裁自然是非四言诗莫属。钟嵘《诗品序》云:“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胡应麟更指出:“四言简质,句短而调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声易杂;折繁简之衷,居文质之要,盖莫尚于五言。”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与五言、七言等其他诗体相比,四言诗独具简约质朴的体貌特征,因此在简易之风盛行的魏晋社会环境中备受青睐。本时期在诗歌创作上偏爱四言的三位诗人嵇康、傅咸、陆云就有重意轻言,或作诗撰文追求文辞省净的倾向,如嵇康的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第十四章有曰:“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自称“不便五言诗”,其诗绝大部分为四言作品,达二十五首一百三十章,堪称魏晋四言诗一大景观。挚虞则在《文章流别论》中宣扬“古诗率以四言为体”,并以“古诗”为准绳评论当世诗坛状况,鼓吹“四言为正”的观点,在他今存全部诗作中,除了一首仅存四句的五言残篇以外,其余都为“雅音之韵”。
在玄学清谈之风盛行的社会环境中,玄学诗人在交接亲朋,宴集群游之际,正可辨析物理,顿悟玄机,并以笔纸代喉舌,将所悟玄理昭示于人。这样,魏晋文坛上就出现了一种“追求集体性、功利性与交际功能”吴承学,何志军《诗可以群——从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形态考察其文学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的创作倾向。就诗歌而言,端方雅正,传统悠久,名分堂皇,深受时人推崇又便于进行应景创作的四言诗随之大量涌现,乃是自然之理。因此,这种群体性的诗歌创作形态成为魏晋四言诗复兴的又一重要原因。晋武帝曾多次在华林园与群臣聚会宴饮,并命令他们赋诗言志,特别是每年三月三日的诗会成为常例,因此留下了许多诗歌作品,如应贞的《晋武帝华林园集诗》、王济的《平吴后三月三日华林园诗》、张华的《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等,皆为四言雅诗。宴集类四言诗中最著名的当推四言《兰亭诗》。晋穆帝永和九年(353)暮春,以王羲之为首的一批文人会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临水修楔,流觞饮酒,并赋诗咏怀。当时作诗者共有二十六人,作品三十七首,包括四言诗十四首、五言诗二十三首,不少人是四言、五言同作的,半数以上的诗人都写有四言作品。这些四言诗均为好尚玄学的东晋士大夫抒发闲适萧散情致的作品,可谓雅集生雅诗,雅诗写雅怀。另外,围绕陆机、陆云以及石崇出现了一系列四言赠答诗。
玄学清谈“得意忘言(象)”的思辨方法,在魏晋时期还掀起了一阵音乐风。在玄学家看来,音乐是天地自然之道的体现,是玄学清谈中辨物致意的天然手段,阮籍《乐论》有云:“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音乐,特别是最能体现玄学简古雅致宗旨的雅乐,得到了魏晋人的普遍喜好,而带有音乐性质的诗体特别是具有雅乐属性的四言诗也随之大受偏爱。这当然也与魏晋两朝都是由篡位所建有关,要名正言顺便要自恃儒学门风,兴礼作乐,大倡雅诗以装点门面。魏晋官方朝会、祭祀等各种场合所采用的音乐,基本上是属于雅音正声。据《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记载,曹操在戎马倥偬中不忘招揽杜夔等音乐人才,以“创定雅乐”。司马氏统治期间,更是力倡典言雅音,晋武帝还曾下诏“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伎”。傅玄所作四厢乐歌共三篇十八章,全为四言;张华所作十六首,七首为四言;成公绥所作十六首,六首为四言,而从总体上看,这些燕射歌诗中四言诗是占了优势地位的。四厢乐歌以外,傅玄、荀勖、张华又各作有《晋正德大豫舞歌》二首,全用四言体。又据《晋书·乐志》记载,晋室南渡后重建宗庙,致力于纠集遗乐和乐工制备乐器、修复雅乐的工作,于是雅乐颇具,四厢金石始备,使曹毗、王殉等增造宗庙歌诗。“晋江左宗庙歌”凡十三首,其中十二首为四言。由上可见,两晋时期产生的大批四言庙堂歌诗,正是当时雅乐风靡朝廷的结果。
同样,魏晋时人特别是玄学名士们日常自娱的音乐,基本上也不超出雅乐的范围。“雅乐”具有简易、平淡、清远、高妙等特性,这正与玄学清谈崇尚简约、务求雅致的精神相契合,因此受到了魏晋时人的大力推崇,而秉性和正的“雅琴”更成为一时爱物。先就竹林名士阮籍、嵇康而言,阮籍“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的自画像早已深深镌入后人的心目,而嵇康临刑还要“援琴而鼓”,并叹息说:“雅音于是绝矣。”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裴注引《魏氏春秋》,中华书局,1982年,第606页。就连西晋富豪石崇也是“家素习伎,颇有秦赵之声。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并自诩“傲然有凌云之操”(石崇《思归引》序)。他作有四言乐府《大雅吟》《楚妃叹》,前者歌颂圣帝,后者赞美贤妃,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都属雅诗无疑。东晋玄言诗一大代表孙绰更对“庭无乱辙,室有清弦”(《赠谢安诗》)的生活表示欣赏,在他今存十三首诗作中,四言诗有七首。谢安在《与王胡之诗》中也说:“夕玩望舒,入室鸣琴。五弦清激,南风披襟。”直至晋宋之际的陶渊明,仍然是“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其《时运诗》(四言)有曰:“清琴横床,浊酒半壶。”《答庞参军诗》亦云:“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雅音起而雅心动,雅心动而雅诗生,信然。
魏晋四言自开奇响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魏晋时期,在时代思想潮流、政治社会环境、文学创作形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四言诗再现辉煌。同时,本时期对四言诗敷陈儒玄教义,辅助交际应酬等功能的强化,也使得这一诗体理过其辞,套语连篇,艺术水平大大降低。因此从总体上看,魏晋四言诗主要是以量取胜,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着较大反差。不过,在四言诗体的大规模运用中,不时也能有某种充实的内容、充沛的情感或生动的意象与这一古雅形式水乳交融,从而诞生了不少艺术价值较高的四言作品,可谓金石杂糅,唯待识者。
魏武曹操首先登上魏晋四言诗坛,唱出千古绝调。他改变了传统四言诗的诗行结构关系和诗句组合规律。清人吴乔说:“作四字诗,多受束于《三百篇》句法,不受束者,惟曹孟德耳。”吴乔《围炉诗话》卷二,转引自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第26页。此言充分肯定了曹操对四言诗的创造性贡献。《诗经》四言诗基本上是两句一行,各句意思不能独立,并存在着种种复叠排偶的句式序列,这种建行方式和典型句式被汉代四言诗沿袭下来,而在曹操的大刀阔斧下得到了改造。从表面上看,曹操四言诗仍是两句一行,但是一些诗行的两句之间已不存在语法结构上的依存关系,而是每句四言自成足句,主要靠意义的连贯构成一行,这样也就不必再使用《诗经》中的典型句式。例如《短歌行》(对酒当歌)一诗,诗中固然仍保留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之类的《诗经》式诗行结构(后者还是《诗经》原句),但也有许多诗行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等,各句在句法上都是独立的,主要以散句为精神,并不着意追求重叠排偶。再如《步出夏门行》中的《冬十月》和《河朔寒》二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