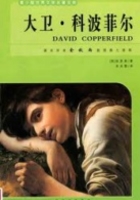来到晏婴的府第,宫人上前敲门多时,门才开了一道缝,接着便传出沙哑的话语:“喂,要饭也总得有个时候,虽说是我家主人乐善好施,可现在都后半夜了,宅子里哪里还有剩饭?主人忙了大半夜,刚睡下,行行好,明天再来吧,行行好!”
“你拿我们当要饭的?”宫人厉声呵斥道,“是国君亲自驾临至此,要见你们主人,还不赶快通报!”
这时门人看见了路边的马车和车上的伞盖,吓得魂不附体,立即转身,直奔晏婴的卧房,惊呼道:“主人,出大事了,国……国君来……来了!”
晏婴一骨碌爬了起来,惶恐地问道:“你……你说什么?”
“国君来了,就在门口!”门人说。
“你赶快去开门。”晏婴吩咐了一声。
门人转身跑了。晏婴匆匆穿好朝服,戴上朝帽,拿起笏板,大步流星地向外跑去,出了大门,便在马车前面跪了下来,问道:“敢问主公,国家可有重大变故?”
“没有。”齐景公答道。
这时晏婴闻到了一股酒气,他抬起头,借着门人手中灯笼的火光,看见齐景公从车窗里露出头来,笑眯眯的。
“那么主公何以深更半夜屈驾降临寒舍?”晏婴又问。
齐景公笑道:“国相日夜为朝廷操劳,寡人颇觉不安,今有甘醴之味、金石之声,不敢独享,特来与贤卿共乐。”
“安国家,定诸侯,整吏治,抚百姓,乃臣之本分,臣敢不殚精竭虑?”晏婴说,“至于侍奉主公尽甘醴、金石之享,主公左右自有其人伺候,臣实在不善此道,望主公见谅!”
齐景公听了,顿觉兴致索然,他没想到晏婴能如此直白而生硬地加以回绝,便没好气地说了一声:“不打扰了!”
一声鞭响,马车飞快地离开了晏府。
“去田司马家!”齐景公吩咐道。
来到田穰苴的府宅,宫人上前敲门。
田穰苴正在撰写兵法,闻听国君驾临,失声叫道:“必有犯境之敌兵!”当即戴盔披甲,佩剑持戟,匆匆跑出府门,跪地问道:“主公,可有紧急敌情?”
“没有。”齐景公答道。
“可有叛乱之臣民?”田穰苴又问。
“也没有。”
田穰苴困惑地抬起头起来,问道:“既无外敌,又无内乱,主公深夜屈驾,不知是何缘故?”
齐景公笑道:“将军南征北战,不避风尘,多有劳苦,寡人颇觉不忍,今有甘醴之味、金石之声,不敢独享,特来与爱卿共乐。”
“筹粮秣,振军旅,御敌寇,肃叛乱,臣当鞠躬尽瘁。”田穰苴说,“至于酒肉、歌舞之享,主公左右自有陪伴之人,臣不敢与闻。”
齐景公的脸立即耷拉下来,心想,怎么这个田穰苴跟晏婴竟像是一个模子压出来的?连说的话都酷似,真是败兴!他急忙把手向御者一挥,马车逃逸般地离开了田府。
田穰苴抬起头来,望着马车的背影,茫然地皱起了眉头。
马车走了不远,来到梁邱据的宅舍,齐景公喊了一声“停”,然后命宫人去叫门。出乎意料的是,宫人刚走上台阶,大门就“哗啦”一声开了,门洞里十几盏灯笼照得街衢通亮,齐景公仔细看去,提灯笼的竟是清一色的少女,个个如花似玉,梁邱据手捧排箫迎了出来,跪地说道:“主公屈驾光临,臣舍顿时为之生辉,卑臣真是三生有幸啊!”
“爱卿知寡人造访乎?”齐景公问。
“未知也!”梁邱据答道。
“既然未知,大门何以不敲自开?”齐景公问。
“卑臣的这一颗心,就是专门为主公而长的。”梁邱据的眼睛笑成一条线,“不论卑臣在什么地方,总挂牵着主公。方才在梦中听得车马声响,就觉得主公的圣驾将至,也是卑臣思君心切,方才有此巧合。”
齐景公在晏婴和田穰苴那里遭了冷遇,听了梁邱据的话,心里暖洋洋美滋滋的,说道:“难为你惦记着寡人,知道寡人的心思。”
四个少女凑上前来,把齐景公扶下车,向府内走去。郑姬和卫姬反倒无事可做了,只好跟在后面。
梁邱据吩咐家人端上酒肴和水果,君臣二人觥筹交错,谈笑风生,齐景公命随行的乐工奏起了“郑卫之音”,郑姬和卫姬翩翩起舞,梁邱据有意做出一副痴迷忘形的模样,一面摇头晃脑,一面用手指在案几上打着拍子……
“前几年,寡人喜听雅乐。”齐景公说,“现在,一听雅乐就唯恐打盹,而一听‘郑卫之音’这样的俗乐就不知疲倦,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俗乐好!俗乐好!”梁邱据忙说,“说来也怪,卑臣在国事上惟主公之命是听,在乐舞方面也步了主公的后尘,主公喜欢什么,微臣就喜欢什么。”
齐景公醉眼迷离地说:“唉,还是爱卿能够体贴寡人哪!”
君臣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十分投机,大有知己难逢之慨,未等兴尽,便听得四方鸡鸣,于是摇头叹息,只恨光阴似箭,良宵苦短。
早朝的时候,齐景公的精神萎靡不振,两眼迷迷瞪瞪,跟群臣匆匆议论了几句之后,就宣布散朝。田穰苴向晏婴递了个眼色,两个人都留了下来,晏婴劝道:“主公昨夜光临敝舍,臣未能尽心陪伴,望主公莫要怪罪。”
田穰苴也说:“臣也请主公海涵。”
“哦,你们不说,寡人倒忘了。”齐景公冷冷地说,“还有别的事吗?”
晏婴不紧不慢地说:“臣以为,作为一国之君,处处应以国事为重,深夜不应当到臣下的宅舍中宴饮欢歌。”
齐景公说:“朝中无你二人,寡人何以治吾国?若无梁邱据,何以乐吾身?寡人不曾妨碍二位的职事,二位最好也不要干涉寡人的行动。”
晏婴和田穰苴听了,面面相觑……
当晚,田穰苴来到田书家,对田凭和田武说起了这件事。
听完了这段奇特而有趣之事,田武心里油然升起了一股说不尽的敬意,他敬佩叔父对国事的忠诚态度,敬佩他敢于犯颜直谏的胆气,也敬佩他的无比威力,因为在这种威力面前,连国君都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
田凭皱着眉头说:“这恐怕不是个好兆头。”
“哥哥为何这样说?”田穰苴不解地问。田武也吃了一惊。
田凭说:“晏婴在庄公时就是国相,功高资深,主公即位后,视之如父兄,自然对他言听计从;你却不一样,你是晏婴推荐的,论出身,原不过是个园吏,论功劳,只有五年前抗击晋燕入侵一次,此功虽大,但在主公的眼里,你远远不能与晏婴比肩。然而,你的官职却已经与晏婴平行了,而昨夜你的言语行动又与晏婴完全一致,这样,你的官职和言行便超过了你在主公心目中的地位,不祥的结局就潜伏于其中了。”
父亲的话,田武完全听懂了,但他不明白叔父应该怎样去做才是对的,便说:“叔父如果想做忠臣,就只能这样做,难道要让叔父违背自己的意愿,像梁邱据一样,把国君请到家里一起饮酒作乐?”
“孩子,你说得很对!”田凭说,“你叔父只能这样做,没有别的选择。”
“没有别的选择,却又潜伏着不祥的结局,这……”田武茫然了。
“这就叫身不由己!”田凭说。
“身不由己?”田武疑惑地重复了一遍。
“比干不是不知道商纣王的残忍,但为了国家社稷,仍然屡次劝谏商纣王,结果被纣王剖心而死,尸体被垛成了肉酱。这是暴君身边忠臣的必然结局。”田凭说,“做不做忠臣,比干是可以选择的,可是一旦决定了要做忠臣,下场就由不得自己了。”
“是啊。”田穰苴似有所悟,“忠臣不是那么好当的。”
屋子里顿时沉默了。田武微微打了个寒噤,痴呆了好一阵。
却说田书率领车马六十乘士卒四千五百人出了临淄,向东南进发。不几天进入了蒙山地界,这里山峦连绵,荆棘遍野,饿殍遗弃于阡陌,狐狼出没于丛林,更兼道路坎坷崎岖,行军十分艰难。
除了斥候(负责探察的士卒)以外,已届花甲之年的田书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方,在平路或下坡路,他站在战车上;每逢遇到上坡路,便下车和士卒们一起步行。他严格按照行军速度的规定,每日一舍(三十里),将士们夜住晓行,秩序井然。
第六天,队伍来到穆陵关,这里不但山峰高耸,而且险峻陡峭,此关正巧在两座高峰之间,像是造物主劈开的一个豁口,其高度相当于山峰的一半,这是南下的必经之路。田书毫不犹豫地下了爬山的命令。
坡度太大,石砾又太多,马蹄不是打滑,就是陷进石砾缝中。田书指挥着将士们在似路非路的斜坡上按“之”字形的折线攀缘,几乎所有的士卒,都用一只手中的戈矛做拐杖,支撑着地面,而用另一只手牵马、拉车或推车,一面用泥土和树枝铺垫坑凹之处,以便让车轮驶过。队伍在山北坡缓缓地挪动着,远远看去,像是一群蜗牛在爬行……
“大齐的弟兄们,这是最艰难的一段路,翻过此山者方为真英雄,身在军伍,死且不避,况此难乎!”田书的喊声震荡山谷。
汗流浃背的将士们受到了主帅的鼓励,精神顿时抖擞起来……
中午时分,队伍陆续攀上山顶。举目南望,将士们笑逐颜开:山南边,竟是长达数里的平缓斜坡。
队伍稍作休息,然后继续前进。经历了艰难的攀登之后,走下坡路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将士们在惯性的驱动下,大步流星地向前迈进,虽然没有风,旌旗却全都舒展开来,发出悦耳的哗哗声响……
日头稍微偏西,队伍来到一片小树林,田书吩咐士卒们开灶做饭。不一会儿,整个树林便香气四溢。
正在这时,一群面色黧黑、衣衫褴褛的难民从南边向树林走来,足足有三四百人,有白发苍须的老叟,有赤身裸体的儿童,也有背着孩子的妇女……
等难民们走近了,田书问其中的一个耄耋之年的老者:“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是菖国人。”老者答道:“今天庄稼本来就歉收,官府反而加重了赋税,不等我们动手,官府就派差役把地里的粮食都收去了,我们颗粒无获,还欠着官府的钱粮。走投无路啊,只得流落他乡,乞讨为生。”
田书当即下令用军粮接济难民,佐将公叔隼说:“我们只带了十天的粮食,分给了难民,将士们怎么办?”
“我们出征的目的,正在于解万民于倒悬,否则,谈何正义之师?”田书答道:“至于军粮,我们已经走了一半难走的山路,剩下了一半好走的平路,可以提前一天到达,到那时,打开了菖都,何愁无粮?”
公叔隼不敢再说什么,安排将士们从每一锅灶里舀出一碗小米饭来,分给难民。
老者分到了一碗米饭,吃着,一面问田书:“老朽素闻齐军威武,想来征讨小小的莒国易如反掌,敢问将军,拿下了菖国之后,欲将何为?”
“菖共公逆天道悖人理,故齐主命我前往征讨。”田书说,“平定之日,自然是行天道,布仁政,扶农耕,安百姓,老人家不必再流落他乡了。”
“仁义之师,仁义之师啊!”老者感动地说,“如此说来,我可以带着乡亲们步将军之后尘,返回故园了!”
“老人家放心地回去吧。”田书说。
“将军的恩德,老朽无以回报,今遣孙子郗獾跟随将军,可以为义军带路。”老者说,接着便把郗獾叫了过来,如此这般地叮咛了一番。
田书给难民们留下了十袋炒面,难民们千恩万谢,异国军民依依作别。
有了郗獾引路,田书行军速度大增,竟提前了两天便到达了菖都城北。
却说莒共公在菖都闻知齐国大军压境的消息,顿时面如土色,急忙召集朝臣,言不成句地说:“齐军来……犯……犯我境,如……如何是……是好?”
大夫淳于炳说道:“齐军远道而来,必定疲惫,田书年过六旬,已是衰颓不堪之人,不足为惧,待我前去将他擒来便是。”
淳于炳披甲执械,率领车马四十乘士卒三千人匆匆出了北门,只见齐军已经布阵完毕,等待厮杀,便回头催促将士道:“快,快!”
这边,公叔隼对田书低语道:“趁他们布阵尚未停当,攻之可也!”
“不必。”田书摇摇头,笑道,“在双方势均力敌或我方稍弱的情况下可以那样做,现在却不必,这次伐菖,旨在威震敌胆,而不在杀戮人众,等他布好了阵势,再将他击败,更能起震慑之效。”
淳于炳显得很急躁,未等车马完全出城,就催着部下击鼓,一面驱车杀向齐阵。这边田书驱车迎上,两车交错之际,田书抡起凤头钺竖直地劈下来,淳于炳举起三戈戟接住,“铿”的一声钝响,淳于炳登时觉得双臂断裂似的剧痛,身子一歪,便从战车上摔了下来,田书顺势将长钺向下一扫,淳于炳便首身异处了。
莒军见自己的主将第一回合就丧了性命,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阵势顿时大乱。于是,战场上出现了奇特的景象:士卒们纷纷夺路奔窜,大半逃进城中,小半落入了护城河,兵器横七竖八地丢在地上,而一百六十匹战马却井然地守候在阵地上,保持着原有的队形,偶尔发出几声不安的嘶鸣……
田书挥军从北门冲入城中,菖侯的宫室早已空无一人。斥候报说,莒君早在淳于炳领军出城的时候就从南门逃走了。
田书命令将士把莒军所弃兵械封锁入库,以木牌写出安民告示,抚慰城中百姓。次日,命佐将公叔隼留守城池,自率一半人马向南追击。
仍是郗獾带路,他身上多了一根长绳,绕了十几道缠在肩上,绳子细而柔软。田书问他带这绳子做什么,他说:“昨天晚上我去看望远房的一个姑母,姑父三年前被莒君杀害了,她一心要为丈夫报仇。她说,无道之君必定引来正义之师,就用麻绳和丝线编了一根长绳,专等伐莒之军到来,便从城墙上抛出,不想这次齐军顺利地打开了城池。她还说,菖君必定逃往纪鄣,而且肯定紧闭城门,不敢出战,就让我带上它。这绳子又细又轻,却比平常用的草绳线绳结实得多,缒城正好用得上。”
田书听了,十分惊讶,慨叹道:“你姑母不但刚烈之气不让须眉,而且料事深远,实在令人钦佩啊!”
队伍日夜兼程,只三天,便赶到了纪鄣。天色已晚,田书吩咐将士们稍作休息,将就着吃几口炒面,自己登上城北的高坡,思谋着攻城的计划。
田书知道,这一仗是十分棘手的:我军轻装追击至此,粮草没有后继,因而此战必求速胜,否则,不消三五日,便只能因粮尽而自动退军。然而,菖军在都城新败,主将淳于炳身亡,莒共公心怯,必不敢出战,只能闭门固守;我只带了三千人马,又无云梯,根本无法打攻城战。现在,菖国方面还不知道齐军已经兵临城下,这正是偷袭的最好时机,时间不能拖过今夜,因为到明天,莒军就能从城里的望楼上看见我军,一旦他们弄清我军的实际人数,胆怯之心便一扫而光了。
秋风吹来,树叶沙沙作响。田书忽然注意到,身边这片浓密的树林中间有一块空地,空地恰好在高坡的顶部,如果从城里的方位向这边看,空地就是树林中的大豁口。顿时,一则巧计扑上心头。
不多时,三百名士卒举着松明和旗幡在高坡顶上从西向东飞跑,当他们经过豁口隐没在密林中之后,却又顺着坡北的山腰处跑回了原地,然后再一次从高坡顶上穿过。就这样,三百人在坡顶和北山腰转了个大圈子。当他们跑到坡顶时,城里人能够看得见,从北山腰返回时,城里人却不知道。
这一招很灵验,先是望楼上的士卒,接着是城墙上的守军,最后是全城的居民,他们分明地看到,城北山坡顶上一团又一团的火光川流不息地向东飞驰而去,火光中,飘展的旗幡若隐若现……不到半个时辰,整个纪鄣城便人声鼎沸、嚎叫连天了。
莒共公得报,登上行宫里临时搭起的望楼,看了一阵,惊叫道:“火把是向东去的,齐军要从东门攻城,火速守护东门!”
西城门外,田书和将士们埋伏在草地里。郗獾将丝麻长绳顶端的铜爪甩上城垛,然后悄无声息地爬了上去。城墙上居然没有一个菖国士卒。他拍掌三次,城外的将士们一个接一个地攀缘而上……
忽然,绳子断了,攀上城头的只有六十个人。
“击鼓!”田书当机立断,命令道。
惊天的鼓声顿时响起,城下和城头的齐兵杀声大作……
莒共公万万没想到鼓声杀声会从西方传来,一时间六神无主,哪里顾得上调兵遣将,心里只剩下了逃命的念头,他急忙叫人打开南城门,带上眷属和亲信仓皇奔窜而去。
齐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纪鄣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