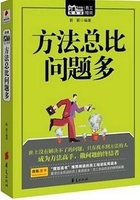“好呀,先生,”我答道,“我希望你会想到希斯克厉夫太太是习惯了受人照料,被人伺候的。她像个独生女那样长大,人人都愿意服侍她。你一定得让她有个丫头,帮她收拾整理东西,一定得和善待她。不管你对艾德加先生怎么看,你不能怀疑她是有着强烈的情感,要不然她也不会放弃她先时家里的优雅舒适,以及她的朋友,心安理得同你守在这般荒凉的处所。”
“她放弃它们是因为幻觉,”他答道,“以为我是传奇故事中’的英雄,期望从我的骑士精神中得到无穷尽的宠爱。我简直就没办法把她当成一个有理性的东西,她是执迷不悟,非要用荒诞的想法来构筑我的性格,而且硬是要照她钟爱十分的那些谬误印象来行事。可是,到最后,我想她是开始认识我了。起初我没有理会她那叫我恼火的傻笑和鬼脸,以及她冥顽不灵的知觉,当我告诉她我对她的情感和她本人的看法时,竟然弄不懂我是认真的。发现我并不爱她,这可真是耗尽了她的心力。有一阵我相信,她是怎么教也教不明白的呢!可是居然她还是勉勉强强明白了。因为今天早上她宣称,好像是一个惊人的消息似的。说是我实际上是成功地叫她恨我了!那真是大力神的一大劳作呢,我向你保证!如果它已经成功,我有理由来答谢你——我能够相信你的话吗,伊莎贝拉?你确信你恨我吗?要是我让你独个儿待上半日,你就不会叹息着再来同我纠缠了吗?我敢说她宁可我当着你装足温情蜜意,把真情暴露出来,是要伤害她的虚荣心的。可是我不在乎谁知道了这情感完全是一边倒的,我从来就没跟她说过一句谎话。她没法指责我可曾表露过一丁点儿虚假的温柔。我们从田庄出来,她看到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吊起了她的小狗。当她哀求我放过这狗的时候,我的第一句话,便是但愿我把属于她的个个都吊死,除却一个:兴许,她把这一个例外当成她自己了。可是残忍并不使她厌恶,我想内心她还崇拜它呢,只消她的宝贵身子不受伤害!如今,这可怜的、下贱并且邪恶的母狗梦想我还能够爱她,岂不是荒唐之极,真是地道的白痴?告诉你家主人,奈莉,我生平从来就没有遇到过像她那样下作的东西。她都玷污了林顿家族的名声,我测试她的忍耐力,可她总是羞羞答答一副谄媚相地爬将回来,因为想不出新的招数,有时候我都动了恻隐之心!不过也告诉她,让她那颗官气十足的兄长心放宽些吧,我是严格遵守法律。迄至今日,我避免给她最细微的口实提出分居。不仅如此,她还不必感谢任何人来离间我们。如果她想走,尽管请便,她在我面前的讨厌相,远超过我折磨她时得到的满足呢。”
“希斯克厉夫先生,”我说,“这是疯子的话,你的太太很可能认准你是疯子。这么说来,她对你是忍了又忍,一直忍到今天。可是既然你说她可以走了,毫无疑问她就会接受你的恩准。太太,你还不至于这般迷乱吧,是吗,还自愿跟他同住下去?”
“当心哪,艾伦!”伊莎贝拉答道,两眼冒出怒火来。这表情明白无误地说明,她丈夫努力叫她恨他,真是圆满成功。“他的话一个宇也别信。他是个撒谎的魔鬼,一个妖魔,根本就不是人!以前他也说过我可以走,我也企图走过,可是我不敢再走了!艾伦,我只求你答应我不要把他那无耻的话跟我哥哥和凯瑟琳提一个字。不管他怎么装假,他只希望激怒艾德加来同他拼命。他说他娶我就是为了挟持他。可是他办不到,我先就去死!我只希望,我祈求他会忘却他那魔鬼般的慎重,来杀死我!我能够想象的唯一乐趣便是死亡,再不看着他去死尸。
“好了,这就够了尸希斯克厉夫说。“倘使你给传到法庭,你得记住她的话语,奈莉!好好瞧瞧她那张脸吧,她眼看就要合我心意了。不,现在你不适合做你自己的保护人,伊莎贝拉。我作为你法律上的保护人,必须把你放在我的监护之下,不管这义务多么烦厌。上楼去,我有些话要对艾伦·迪恩私下里谈一谈。别往这走一一上楼,我告诉你!怎么的,这才是上楼的道儿,孩子!”
他捉住她,把她推出房去,然后嘟嘟哝哝走回来:
“我没有怜悯心!我没有怜悯心!虫子越是扭动,我越是渴望挤出它们的五脏六腑!这是在道义上出牙,越是疼痛,我就越是要用力去磨。”
“你知道怜悯这个词的意思吗?”我匆匆忙忙带上我的帽子说。“在你一生当中可曾感觉到过它的一丝一毫?”
“放下帽子!”他打断我说,看出了我是要走。“先别走,这边来,奈莉。我非得或者是说服你,或者是逼迫你来帮我,让我实现去见凯瑟琳的决心,而且不要迟延。我发誓决不伤人。我不想惹是生非,或是激怒和侮辱林顿先生。我只希望听她自己说一说她怎样了,她为什么得病;问一问我能为她干些什么。昨晚我在田庄的花园里晃荡了六个小时,今晚我还要去。每晚我都要去那里,每天也去,直到有机会进去,要是艾德加·林顿撞见了我,我毫不犹豫就打倒他,让我待在那里的时候,他能歇息个够。要是他的仆人遇见了我,我就用这些手枪把他们给吓回去。可是让我去了避开撞见他们,或是他们的主人,岂不更好?这于你轻而易举就能办到!我来了先让你知道,然后一俟她一人独处,就让我悄悄进去,再放风放到我离去。你的良心也平平静静,因为你要阻止事态恶化。”
我抗议让我在我雇主家里干这背信弃义的勾当。除此之外,我特别指出,为了他自己的满足而破坏林顿太太的安宁,是残酷而且自私的。
“最平常的事情也会叫她大吃一惊,痛苦非常,”我说。“她神经脆弱极了,受不了这个惊吓,我确信无疑。别坚持了,先生!要不然我就不得不告诉我家主人你的计划,他会采取措施保卫他的家园和家人,来防范一切像你这样的不速之客!”
“要是那样,我就采取措施先来保卫你,娘们!”希斯克厉夫大喊道,“明天早上之前,不许你离开呼啸山庄。说凯瑟琳经不起见我一面,真是荒唐透顶。讲到惊吓着她,那也并不是我的想法,你必须让她有个准备,问问她我是不是可以来。你说她从未提起过我的名字,也从来没人向她提起过我。倘使我是那一家子噤若寒蝉的话题,谁又会提起我来?她觉得你们全是她丈夫的密探。哦,我一点都不怀疑她活在你们当中,就像身陷地狱!从她的沉默里,就像别的方面一样,我猜得到她感到了什么。你说她时常坐卧不安;神色焦躁,那难道是安宁的证据吗?你还讲到她心绪紊乱,她被这样可怕地孤立起来,鬼又能给她换上一种心情?那个无味的、卑鄙的东西出自责任和人道来照料她!出自怜悯和慈悲!他还不如把一棵橡树种在花盆里,盼着它枝繁叶茂.居然以为在他浮浅照料的土壤中,她会恢复健康!让我们一言为定:你是愿意留这里,让我扫平林顿和他的下人,杀开一条血路去见凯瑟琳,还是愿做我的朋友,就像你迄至今日一直是我的朋友,去做我告诉你的事情?决定吧!因为我没有理由再耽搁一分钟,倘使你坚持你那冥顽不灵的劣根性!”
你看,洛克伍德先生,我争辩了、埋怨了、坦白地拒绝他了五十次,可是到老他还是逼着我答应下来了——我答应帮他给我家女主人送一封信,倘使她同意,我应诺向他通报下一回林顿出门的消息,那时他就可以来,要是做得到就进门——我不会在那儿,我的仆人同道们也将同样避开。
这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我恐怕是做错了,虽然这只是权宜之汁。我以为我依从下来是防止了另一场乱子。我还以为,这对于凯瑟琳精神上的疾病,兴许能够创造一个有利的转机。然后我又记起艾德加先生严厉责骂我搬弄是非的话来。我反复对自己说,那次背信告密,是有罪的,这就应是最后一次了。我由此来抚平由这话题引起的一切不安。
虽然如此,我回家的路程比我来时更是凄惶。在我能够说服自己把那信交到凯瑟琳手中时,我的忧虑是多不胜数哇。
可是肯尼斯来了,我得下去,告诉他你是好了许多。我的故事照我们的说法,是很凄凉的,而且可以再消磨一个早上呢。
凄凉,并且凄惶!当那好妇人下楼去迎接医生的时候,我这样想着。确切地说这并不是那一类我应当选来解闷的故事,可是没关系!我会从迪恩太太的苦辛的草药当中,熬出地道的良药来。首先,我要,当心蛰伏在凯瑟琳·希斯克厉夫明亮眼睛中的迷惑力。要是我把心儿交给那个年轻人,我一定会落入古怪的烦恼中去,那女儿正是她母亲的翻版啊!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离健康,以及春天又近了许多!现在我听完了我邻居的全部故事,那是在不同的时候陆续讲述的,因为女管家总是可以从她更重要的作业中挤出时间来。我将用她自己的话把故事讲下去,只是稍微压缩一点。总的来说,她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我并不觉得我能在她的风格上锦上添花。
那天晚上,她说,就是我去山庄的那天晚上,我知道并且也仿佛看见了希斯克厉夫就在附近。可是我不出去,因为他的信还在我口袋里边,我可不愿再被威胁一通,再不调笑一气。
我下定决心,除非我家主人出门,我就不把信儿送到。因为我说不上凯瑟琳收到信会是怎样。结果是,三天过去,信还没有到她手里。第四天是星期天,在一家子去了教堂后,我带着信进了她的房间。
有个男仆留了下来同我一起收拾家务,通常在做礼拜的那几个钟点,我们把一道道门都给锁起来。可是这一回天气是如此晴朗暖和,我把门都大敞开来。为了完成我的使命,诚如我知晓有谁要来,我告诉我的同伴太太很想吃几个桔子,他必须到村里去弄些儿来,明儿个付账。他走了,我就上了楼。
林顿太太身穿一件宽宽松松的白衣裳,肩上搭着一条薄薄的披巾,像往常那样坐在一扇敞开的窗子跟前。她厚实的长发在她犯病之初就剪去了一部分,此刻简单梳梳,很自然地盘在她的鬓角和颈子上面。她的模样改变了,就像我告诉希斯克厉夫的那样,可是当她平静的时候,这改变当中似乎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美。
她双目中的亮光已经被一种忧郁的梦幻般的温柔所替代。它们不再令人感觉是在看她周围的东西,却显得总是在凝视远方,很远的远方,你可以说是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然后,虽然脸上的憔悴是消失了,因为她恢复了长胖了些,她那苍白的脸上有一种特别的表情,尽管痛苦地指示着它们的由来,却格外增强了她的动人之处。并且我知道,在我看来,以及在任何看到她的人看来,那是必然会推翻那许多更为显见的康复明证,标明她是命定要凋谢了。
一本书摊在她面前的窗台上,她几乎察觉不到的微风时不时掀动着书页。我相信是林顿放在那里的,因为她从来就没有努力去读书消遣,或者去做任何事情。他会耗上好几个钟点,试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她先时喜好的什么东西上去。
她明白他的用心,在心境好的时候,也就温顺地听他摆布,只是时不时咽下一声疲倦的叹息,表示它们毫无用处,最后,便用最是凄惨的微笑和亲吻来制止他。在别的时候,她会突然转身而去,把脸掩在双手当中,甚而愤怒地把他推开。然后他就小心翼翼让她独个儿待着,因为他确信自己是无能为力了。
吉默顿教堂的钟声还在响着。山谷里的小溪涨满了水,欢快的水流声淙淙悦耳。它甜美地替代了还没有到来的夏日里飒飒树声,当树上枝叶丰茂的时候,就淹没了田庄附近这美妙的音乐。在呼啸山庄.冰雪融化或是久雨之后的平和日子里,它总是这样淙淙响着的。凯瑟琳一边在听,一边在想,想的就是呼啸山庄。那是说,要是她果真在想、在听的话。但是她两眼空洞洞望着远方,就像我方才所说的那样,这表明她不论是耳朵还是眼睛,都分辨不出物质的东西了。
“你有一封信,林顿太太,”我说,慢慢地把信塞人她放在膝上的一只手中。“你得马上就读,因为等着回信呢。要我拆封吗?”
“拆吧,”她答道,没有改变她双目的方向。
我拆开了信,信很短。
“现在,”我接着说,“读信吧。”
她把手抽回,由着信落到地上。我把它重又放到她的膝头上面,站着等她高兴了往下瞟上一眼。可是那一刻迟迟不来,最后我又说:
“非得我来读吗,太太?信是希斯克厉夫先生写的。”
她猛一惊,露出苦苦回忆的神色,竭力整理着她的思想。她举起信,像是在读,读到签名她叹了口气。可是我依然发现,她是没有领会信的内容,因为我问她作何答复时,她只是指指那名字,带着哀伤和探询的急切神情,紧盯着我。
“是呀,他想见你,”我说,猜想她是需要人类作阐释。“这会儿他在花园里呢,等我带回什么答复,已经等得不耐烦啦。”
我说话的时候,看到一条大狗,躺在底下草地上的阳光里,竖起了耳朵,仿佛要吠叫的样子,然后又把耳朵耷拉下来,摇着尾巴宣布有个它并不认为是生客的人来了。
林顿太太俯身向前,凝神屏息地听着。片刻一会儿有脚步声穿过厅堂。对希斯克厉夫来说,敞开的宅子诱惑力是太大了,他身不由己要走进来。很可能他以为我有意躲避我的诺言,所以决定宁可相信他自己的胆气。
凯瑟琳眼巴巴盯住她卧房的门口。他没有径直找对屋子。她做手势叫我引他进来。可是我还没有走到门边,他就发现地方了,一两步就跨到她的身边,把她抱在怀里。
有五分钟的光景,他一言未发,也没有松开他的怀抱。在这段时光里,他给她的吻,比在这之前他一生中给人的吻还多我敢说。可是是我家女主人先吻他的,我分明看见他顿时就痛苦得几乎没法正视她的脸!从他看见她的那一刻起,他就同我一样确信无疑,她是没有最终恢复的希望了——她命里注定了,注定要死。
“噢,凯茜!噢,我的生命!我怎能忍受?”那是他说出的第一句话,声调毫不掩饰他的绝望。
现在他全神贯注地盯着她,以至使我觉得,光是这么热切地盯着,也会把他的眼睛盯出泪来。可是他的两眼燃烧着痛苦,并没有化成泪水。
“现在怎么的?”凯瑟琳朝后一倒说,脸色猛然阴沉下来回报他的凝视。她的脾气不过是她变幻无常内心的风向标。“你和艾德加弄碎了我的心,希斯克厉夫!你们两个都为那事来向我哀告,好像你们才是该被怜悯的人!我不怜悯你们,我不。你杀死了我——得了不少好处吧,我想。你多么强壮啊!我走了以后,你还打算活多少年呀?”
希斯克厉夫一直跪下一条腿抱着她。他想站起身来,可是她揪住他的头发,把他压在底下。
“我真希望我能够拥抱你,”她辛酸地接着说,“直到我俩全都死去!我不管你受了多少痛苦。我毫不关心你的痛苦。你为什么不该受苦?我在受着!当我人土以后,你会忘记我吗,你会快乐吗?二十年后,你是不是会说,‘那是凯瑟琳·厄恩肖的坟。很久以前我爱过她,因失去她而痛苦不堪。可是这已经过去了。从那以后我又爱过许多人。我的孩子对我来说比她更亲,而且要死的时候,我不会因为去会她而快乐,我会因为离开孩子们而悲伤!’你会这样说吗,希斯克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