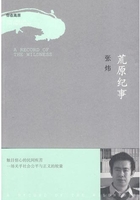仍然拣尽寒枝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
当谈晶打开门看到满脸泪痕的盛夏时,着实吓了一大跳。盛夏素来要强,鲜少在旁人面前流泪,认识了这么多年,谈晶只见到她哭过不超过五次。
连忙一把抱住盛夏,谈晶一边轻拍着她的背,一边担忧地问:“怎么了?是不是同顾映宁吵架了?”
盛夏只是伏趴在谈晶的肩头放声大哭,手臂越揽越紧。愈是措手不及的事情愈让人痛心,而她,甚至都没有一个可来得及商量的对象。
待盛夏哭得疲累了,谈晶终于得以知晓发生了什么事。听盛夏断断续续地说完前因后果,谈晶也是极其震惊—因为许亦晖和顾映宁两人当中,必定一白一红。以谈晶对许亦晖的认识和了解,她极不愿相信许亦晖现在竟是这样一个人,然而她也明白,顾映宁确实不是那使下三滥手段之流。
这样一个进退维谷的局面,谈晶也是哑口无言,不知从何说起。
已是三更半夜,星子在漆墨色的苍穹里忽明忽暗,月色倒是模糊的,仿佛毛了边似的。这样静谧的夜里,谈晶望着自己身旁泪犹在掉的闺密,只觉格外心疼。
拭去盛夏满脸的泪,谈晶轻声问她:“小夏,你告诉我,你到底相信谁?”
盛夏抬眼,抿唇望着谈晶,却半天不说一个字。然而谈晶却不放过她,硬是逼问:“你究竟是相信顾映宁还是许亦晖?小夏,你知道自己必须做一个抉择不是吗?”
哑着嗓子,盛夏咬唇咬得很紧,许久后才开口:“小晶子,我真的不愿意去想亦晖他现在竟然……”
她的声音沙哑而模糊,然而谈晶心里到底是松了一口气,面上却不露丝毫,只是继续说:“明明你心里相信的是顾映宁,那为什么当他和许亦晖的话发生冲突的时候你选择质问的人却是他?”
谈晶鲜少的咄咄逼人,因为她晓得如若不这样,依盛夏的性子或许会一直鸵鸟下去。
盛夏怔忪,张口说了好几个“我”字,却再没有下文。
幽幽地叹了一口气,谈晶无奈道:“之前顾映宁的悔婚我确实很为你恼火他,但平心而论,这三年你们都在一起,你那么爱这个男人,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难道还需要我来说吗?”顿了一顿,她继续说,“我明白,许亦晖是你青葱岁月里最夺目斑斓的里程碑,也是你心里一个特别的印记,可是小夏你别忘了,分隔的这四年多他到底经历了什么、现在又是怎样,你真的还清楚吗?”
其实谈晶说的这些盛夏都明白,然而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深陷其中时,盛夏无可避免地会感情用事而拒绝去思考—比如,许亦晖也许早已不是从前记忆里那个眼睛会笑、温暖和煦的许亦晖了。
努力顺了顺气息,盛夏竭力用稍微平稳一点儿的声音说:“道理我都懂,只是……”
“只是小夏,你若是爱顾映宁至深,怎舍得让他受委屈?”在她犹豫的空子里,谈晶已经幽幽打断她而说了下去。
想起甩门离去前顾映宁勃然大怒中又饱含着悲哀的神情,盛夏心中一痛,刚刚逼退下去的眼泪瞬间又重新涌了上来。
她从没想要伤害他,但不知不觉中,她竟变成了伤他最多也最容易的那个人。有时候,正是因为太在乎、太爱对方,反而陷入死胡同里走不出来。因为期望值太高,才会在一有风吹草动时就如惊弓之鸟。明明心里是向着他的,却总会在他面前不依不饶,把那也许原本分明只是一毫米直径的圆点放成无限大的一个巨大黑圈,淹没了自己也伤及了对方,却又倔强地不愿先低头。
盛夏,分明就是这样的一个写照。
见她的表情有所松动和走神,谈晶拍拍盛夏,轻轻道:“不早了,我给你热一杯牛奶,早些休息吧。”
起身走了几步,她想了想还是说:“小夏,明后天平静下来,你还是主动去找顾映宁吧,无论是把事情说开,还是……先道个歉。”
不管与顾映宁怎样,工作总还是要照常去做。
同辜子棠汇报完S.R.方面传真过来的补充材料,盛夏正欲转身离开,辜子棠却喊住了她。回头,触到辜子棠关切的目光,盛夏只听得他问:“最近很累吗小夏?脸色这么差。”
盛夏浅促一笑,低声道:“多谢辜总关心,不过我还好,没事的。”
辜子棠沉吟片刻,尔后右手一挥断然地开口:“批你半天假,回去先好好休息,明天再来。”盛夏还想再辩解,但辜子棠已经不由分说,只道,“上司命令。”
盛夏没辙,于是只好应声下来,再次谢了他一番然后带上门离开。
然而当盛夏真的收拾好东西下楼,站在公司门口的马路边,她却茫然了。脑子里一片混沌,她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去哪里,是回清茶花苑,还是去顾映宁的别墅。虽然她心底里是格外想回别墅、想晚上一开门就能看到顾映宁的身影,可是盛夏又明白,自己昨晚同他那样大吵一架还甩门落跑,怎有脸再回去。
这样想着,盛夏忽然觉得疲乏至极,全身所有的细胞仿佛都是喝饱了水的海绵,沉重窒息而呼吸困难。她随意地向左边走去,这一带都是高级商业区,过眼是一家一家的奢侈品店:Hermes、VERSACE、LV,每一家店里几乎都是男女相携而逛。隔着玻璃橱窗,盛夏看到店里女人的喜悦笑容和男人的宠爱眼神。
她恍然忆起有一次顾映宁去意大利出差,回来的时候给盛夏带了一只Prada的手袋,樱花粉的颜色很好看。那时他送得淡然,而她收得更平淡。那会儿她接过他递来的包装纸袋,打开袋口粗略看了看后便放到车座一旁,平平淡淡地说了一句:“谢谢。”其实她心里根本不是表面上这般淡然处之,而是早就掀起了惊涛骇浪。虽然那时候还很早,但她已经开始明白自己的心意。只是她以为自己是顾映宁诸位“藏娇”中的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身份和关系让她除却甜得苦涩外再无别的感觉。不过从那之后,除了偶尔的首饰,他再没有送过她一件奢侈品礼物。
现在想来,也许那时候看起来毫不在意的顾映宁,心里其实也在意得紧。
顾映宁……想到这三个字,盛夏只觉心里又是欢喜又是痛。对她而言,这三个字所代表的根本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最柔软最牵动她一情一绪的那个生动的存在。哪怕是相似的字、相似的读音都会让她联想到他,联想到他的卓尔不凡,联想到他的时而清冷时而阴鸷,甚至是他鲜少流露却倚光流离的笑容。
然而一想到昨晚那场争吵中顾映宁前所未有的疲倦和微带悲哀的神情,盛夏就惶然得一塌糊涂。不想回去,也不知该不该回去,其实说穿了,盛夏是在胆怯惧怕—信任于情侣而言何其重要,昨晚她却打破平衡,也许这之后的结果是自己承受不起的万丈深渊。
因为她走得极慢,所以走着走着,竟是从下午走到了傍晚。盛夏不记得自己穿过了多少条巷道,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走去哪里,但是当她被紧擦而过的一辆摩托车尖锐的鸣笛喇叭而惊醒时,回过神才猛地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竟走到了这里。
西雅公园。
两年前,他和她刚刚开始有了最深的羁绊。某个周六清晨,当盛夏还在被窝里没睁开眼时,手机铃声忽然锲而不舍地响了。她迷迷糊糊地接起来,那头的声音低沉而清冷:“下午两点,我去接你。”
并不陌生的嗓音让盛夏骤然从朦胧睡意中苏醒,她立刻睁大双眼、一骨碌坐起身,拿着手机的手微微握紧,声音有些不易觉察的颤抖,说:“今天下午?可是我已经约了朋友……”她确实是约了谈晶一块儿喝下午茶。
然而顾映宁的回答一如既往的不容置喙,“推掉”,顿了一下他说,“就先这样。”
那一头,他的电话已然挂断,但这一头盛夏的脑子却一下子又乱又清醒。两手将头发一把顺到后头,盛夏曲着腿怔怔发愣。起床梳洗一番之后,盛夏煮了一杯卡布奇诺,推开窗户,倚在墙边望着窗外的风景出神。那时候她没有完全理清心里的感受,也还没有下定决心到底是任由自己继续靠近他还是远离,所以那天上午,她的脑中是混沌不堪、头痛欲裂的。
不过下午,她到底还是安安静静地在家等他。
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天是他生日。
起初顾映宁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将盛夏带来西雅公园,江镡准备了一瓶红酒和一些长条法式面包。那是盛夏第一次来西雅公园,之前她从未听说过这里。彼时春意已浓,公园里绿草茵茵、满树碧叶,正是一派万物复苏的生气景象。
盛夏当时正被一簇虞美人所吸引,忽听得侧前方他低低说:“今天是我生日。”
她愣住,愕然抬头,顾映宁的表情却是一贯的冷峻淡然。没有等她开口,他已经继续道:“父亲上个礼拜去了德国,而我的母亲……她早已不在。”望着盛夏,顾映宁一字一句,“所以今天,你陪我半天吧。”
他连孤独都说得这样要强,盛夏的心瞬间柔软地塌陷下去,在她还没有察觉之前,心里有一块地方已经莫名地微微作痛。她缓缓露出笑颜,侧头说:“过生日,怎么能没有生日蛋糕?”
也许是因为她的话,顾映宁脸上的线条柔和了许多,声音却依旧低沉:“不用了,又不是小孩子,况且我本身也不喜甜食。”
他们坐在公园西北角的一个亭子里,一张圆形的石桌,外面围着一圈古朴的石凳。不远处假山上的流水潺潺而下,空气里是春日下午暖洋洋的味道,花团锦簇中,盛夏想了想,打开那瓶红酒倒满了两只玻璃杯,然后笑颜如花、齿若编贝,举起酒杯说:“那好,那就干杯,祝你生日快乐!”
那时候自己说的话语还犹在耳旁,而现在,盛夏站在公园外头远远眺过去,院墙遮挡住了亭子的一角,让回忆都变得不真切起来。
忽然,她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脊背倏地僵直,停顿了片刻之后,盛夏终于下定决心。走到马路边,她扬手拦下一辆的士:“城郊别墅,谢谢。”
盛夏从的士里下来的时候,已是暮色四合。冬日的天本就暗得早,虽说现在只是六七点的光景,外头早已是黑压压的一片,细细分辨倒还能看到大朵大朵的云。
捂着大衣的衣领,当真的站在顾映宁别墅的门口时,盛夏却犹豫了。并非是感到后悔,相反,她是觉得怯怕,害怕他会不原谅、害怕他会冷眼相对。然而上天仿佛听到了她的惧怕,于是断然地切断了她的后路。
伴随着尖锐的“嘀—嘀—嘀”声,盛夏转过身去,只看到满目刺眼的照明灯光。熟悉的车身让盛夏的心陡然间跳得快要跃出来。车门打开,那道熟悉得似乎深入她骨髓、刻进她心板的身影果然慢慢地立在了她五步之外。
天这般冷,他却只在浅灰色条纹衬衫之外罩了一件藏青色呢大衣,她看得只觉鼻子发酸。想上前替他拢一拢衣服,刚迈出了一步却又顿住了。顾映宁自然也看到了盛夏,俯下身跟江镡交代了几句让他收工回家,然后才不紧不慢地踱步到她面前。
“没带钥匙?还是,”他的面色冷凝至极,口气也不甚好,“你根本不想回这个家?”
听到顾映宁还会同自己说话,盛夏连忙摇头:“不是不是,我……我只是在等你。”
她的声音越说越小,而顾映宁的表情也越来越讽刺。他挑眉,嘴角的线条刀刻般凌厉:“等我?盛夏,我倒是不知现如今你撒谎的本事越来越差。”
说完话,顾映宁举步就走到铁栅栏前开了门,快要关上门的时候他忽然停住了,转身对后面已经红了眼眶的盛夏冷肃道:“不进来我就关门了。”盛夏闻言先是一怔,然后一喜,赶忙小跑着跟了进去。
在沙发上随意坐下,顾映宁望着距离自己几步开外的盛夏,头顶上那水钻大吊灯折射出的光洒在她脸上,他心里一紧只觉讽刺—这一幕,和昨晚她不分青红皂白斥责他的情景根本就是一模一样。昨晚的事,又要重复上演一次了吗?
闭上眼,顾映宁捏着眉心,声音绷得很紧,道:“又来为你的‘亦晖’伸冤吗?说吧,我洗耳恭听。”
他把“亦晖”两个字咬得很重,盛夏又怎会听不出他的嘲讽与防备,一时间竟觉得喉头一堵什么都说不出来。
许久都不见她开口,顾映宁睁开眼,眸子里浓墨般暗沉,冷冷道:
“没事的话,我要洗澡了。”
他站起来便要上楼,刚走到扶梯口,身后却突然传来她细细的带着颤抖的声音:“映宁,对不起。”
顾映宁陡然僵住,两三秒后猛地回过身,然而眼里的暗沉却越聚越深,几乎是勃然,他和她怒眼相对,咬牙切齿道:“盛夏!
你以为你是谁、我又是谁!随随便便地打一巴掌然后又赏一颗枣子吗?这样的路,你妄想在我这里走得通!”
他说完便要转身上楼,然而下一秒盛夏已经从背后抱住了他,声音里满是担惊害怕和哽咽的模糊:“真的对不起……映宁你听我说好不好……”
没有回头,顾映宁字字嘲讽,声音冰冷:“听你说什么?说我怎样对你的亦晖使绊子吗?听你是如何护着旧情人而罔顾新欢吗?”
他用力一把拽开她的手臂,腰间陡然消失的温度让他的眸色变了变,转头望着盛夏的眼睛,顾映宁一字一顿,仿佛是挤咬出这句话:“别跟着我,也别再让我听到你说一个字。”
这一次,他终于顺利无阻、头也不回地决然上了楼。
盛夏觉得冷,彻骨的冷,就好像被关在冰窖里整整一个日夜那般濒临意识涣散的冷。可是一会儿又觉得火烧一般的热,这样的冷热交替让她仿佛置身于一团雾弥漫的迷宫里,她试图走出去却看不清路,试图喊人却发不出声音。早失了平时的冷静,心里越来越升腾的焦躁和恐惧快要从头到脚地淹没了她。
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慢慢传过来,盛夏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雾太大,起初她分辨不清方向,直到后来有光亮一丝一丝地透进来,她惶惶惑惑地探过去,终于看到一张熟悉的脸—顾映宁。然而就在盛夏想要喊住他的时候,那张脸却又在突然之间消失了。她一惊一急,终于睁开了双眼。
喉咙冒烟般干涩,眼角酸胀,头痛得仿佛要裂开来,后知后觉的盛夏才发现,自己应该是生病了。
勉强坐起身,努力伸手到床头揿下开关,房间里瞬间亮堂。翻身下床,然而盛夏只觉得每一步都好似走在棉花上,软而不实,似乎随时都可能会栽个跟头。她就这么摸摸索索地开了房门,原本想自己直接下楼去厨房倒点热水,然而路过顾映宁房间门口时,不晓得究竟是真的走不动了还是心里不愿再走下去,盛夏竭尽最后的力气敲响了房门。
就在她以为面前的这扇门会一直这么岿然不动打算放弃时,门突然从里面打开了,盛夏一个不察双腿一软,就这样直直地向着顾映宁倒去。
起初顾映宁面色怫然,正欲冷声质问她到底想要做什么,然而她忽然这么一下子软倒在了自己怀里,顾映宁神色大变,焦急担忧的情绪到底掩都掩不住,连声道:“盛夏,盛夏你怎么了?”
触碰到盛夏滚烫的额头,顾映宁终于心惊失措,抱紧怀中柔软滚烫的身体,半是后悔担心半是温柔缱绻的目光再也毫无遮拦地倾泻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