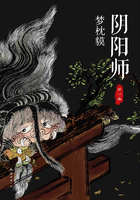他对我说:明妙,我得去。并不告诉我更多。
当他讲到最诚实的愿望,就会嗓音低沉,两眼灼灼闪亮。在遇到他之前,我从未见过像桑青这样的人,他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困境,总是在行动,总是往前看,如果他一不小心死了,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尸体就地掩埋,然后继续行动。
我一声不响。
明妙,我需要你的祝福。
他说出的话就像堵在我们之间的高墙,这令他更加像一个男人,勇敢,自由,充满欲望。我喜欢他皮肤上的气息,心中却油然升起一股怨恨:一定要这样艰难吗?这一刀一刀的感情,简直令人难以承受。
明妙,你等我。
我说不出话,没有任何语言是妥当的。桑青,我不会等你,如果你回来,看见我还在这里,只是因为我对你的感情太多,尚未用尽。
他不喜欢告别的场面,他答应我:偶尔离开,永远回来。他英俊,糊涂,有时候很糟糕,从不欺骗我,可他失踪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没头没脑的命运激怒了我,所以我得坚持下去,即便面对天大的困难,我也要拖着困难往前走,咔咔咔,拖着困难往前走,我不要假惺惺,不要遮遮掩掩,也绝不转过头装糊涂,我要睁大眼睛,弄清楚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你不知道他在哪儿?黄凉若难以相信:一个人怎么可能失踪?
我也不信,可他就是失踪了。
在利比亚,凉若和桑青一起冒险,一起吃了些苦头,用身体慰藉对方,这种感觉很刺激,她觉得完全可以再来一下。每到陌生的地点,桑青都会拿出一个金色嘎乌盒拍照,盒子上绘画蓝色佛眼,他让佛眼看见他做了什么,为什么紧张,为什么专注,为什么奋不顾身。夜晚,凉若爬上床,钻进他的睡袋,嘴对嘴喂他一口烈酒,金色嘎乌盒挤在她胸脯上,有点凉。
把这个给我,桑青。
他摇头:你可以要点别的,除了这个。
他的语气郑重其事,这让她不舒服。趁他睡着,凉若偷走那个嘎乌盒,沿着街边的石头矮墙一直往前走,有点邪恶,又有点幸灾乐祸,甚至都没有察觉到天在下雨。路的尽头有一个小广场,有人在喷泉旁边拉小提琴,琴声吱吱嘎嘎。凉若看见一个老乞丐,垂着头,大胡子微微飘拂,她掏出一把本地硬币,连同那个金色嘎乌盒一起扔进他面前的铁皮盒子里,叮叮当当,这声音真让人愉快。
她觉得迎来了一个快乐的早晨。
没想到桑青竟敢毁灭这快乐,他责备她,凶狠地对待她。他们大吵,她跳上床,跳得很高,她只想吓唬他,可他真的想掐死她:凉若,你怎么能这样?
我不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粗鲁地说。
他铁石心肠,没有一丝感情:我不想再看见你。
他果然走了。
几个小时以后,凉若终于发现:他不会再回来了。
她去找他,每一步都踩在桑青走过的地方,地上没有留下脚印,可她知道没走错,桑青一定就在附近,他躲着她。凉若厌恶地看着这个地方,她很愤怒:我愿意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你可以害怕我,可以为我疯狂,可以膜拜我,可你怎么能拒绝我?
她没办法接受这个,她一定要找到他。
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一场车祸,桑青肯定不会再出现。
车子撞过来的时候,凉若闪躲了一下,她不想自杀,只是有点恍惚,那是一辆黑色摩托车,一撞就跑,连停下来看看的愿望都没有。凉若以为自己会飞起来,没有,她滚出去两米多远,整个人扑倒在路边。糟糕!她心里好恨:这姿势一定丑陋极了。有人凑过来看,她的牙齿磕到了嘴唇,满嘴的血,有点吓人,不怎么痛,她躺着不动,不想起来。
几个人来围观,小声说着什么,表情又肮脏又懦弱。凉若听不懂,也懒得听,她愿意就躺在这儿睡着,也许一觉醒来,发现很多年已经过去了,自己是在很远的地方,有很多陌生人在身边,他们都爱她。她闭上眼睛,感受到一双手从身体下面伸过来,托起她。
她睁开眼睛,看见桑青,这张脸真英俊,像广告里的模特儿,只是没刮胡子。他脖子上挂着那个金色嘎乌盒——他是怎么找到它的?
这让人充满想象。可是凉若没工夫关心这个,她抬起手背,擦了一下受伤的嘴唇,它开始痛了,迅速变得非常痛。
她哆嗦了一下,狠狠骂了一句脏话,说我很想睡觉。
然后她就睡着了。
凉若在诊所待了五天,除了擦伤和轻微脑震荡,没有更严重的伤害,身上搽着当地人配制的一种药膏,黏糊糊的,黑褐色,凉若闻了一下,有点臭臭的,她在病床上跳了一下,这姿势显得很可爱。桑青拿起照相机拍摄她,凉若索性在他面前脱掉衣服,问他:你最喜欢我哪个部位?桑青低着头,咔嚓咔嚓按快门,拍了一阵子,他收起相机。
凉若,他叫着她:我明天返回中国,我们不会再见面。
她惊呆了,难道不是和好如初了吗?听听他在说什么,让事情一下子变得不可收拾。
她气坏了,抄起一盒饼干朝他丢过去,抄起药瓶丢过去,抄起枕头丢过去,连衣服也丢过去,手边什么也没有了,她光溜溜地跳下床,朝他扑过去。桑青站在那儿等,等她扑到面前,一把攥住她的手腕,把她按在床上,用绳子捆她。她挣扎了好久,直到一塌糊涂,瘫软在被子里,他松开手,也喘着粗气,不和她说一句话,就消失在门外了。
我这么美,他竟然背叛了我。
从很年轻的时候起,黄凉若就背叛了好多人,可那些人也从她身上得到了一些不该得到的,这很公平,没有人敢说比她更清白,起码她忠于自己,无论那想法有多么大逆不道,她从来没有动摇过。的确如此,一旦黄凉若头上长出光环,当年唾弃她、伤害她的人都会掉过头来奉承她,人就是这样势利。所以黄凉若是强者,她喜欢别人奉承,如果那真话不好听,她宁肯把真话扔进垃圾桶。
她想过雇一个杀手干掉桑青。价钱很贵吗?还可以加上我,一个女人,有魅力的女人。
很快地,她改变了主意,并前往中国寻找桑青。
她不相信桑青失踪了,而令凉若改变主意的原因是:她怀孕了。
在这高海拔的寺庙里,李明妙见到黄凉若。
她们望着彼此,一动不动。
这一切都是为了谁呢?凉若觉得应该狂暴地哭一下,难道她不该哭吗?可她哭不出来。胸中有一座巨大的火山在爆发,她应该把一切都煮熟。那个万恶的男人失踪了,我还得没完没了地在这儿受罪。她抓住明妙的肩膀,都是因为这个该死的女人,她怎么可以这么小,怎么不是一团糟?她越看越气愤,猛烈摇晃她: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
那你知道什么,你这个蠢女人!
凉若想着:要是她不说出来,我就去死。
于是她放开手,一步蹿到窗前:快说他在哪儿,不然我就跳下去。
明妙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看看她,转身走向房间另一边,那儿有一扇同样的窗,她推开窗,翻出去,坐在狭窄的窗台上,双脚悬挂在空中,说:你跳我也跳。
凉若愣住了,月光照在明妙脸上,光洁完整,她看起来不像真人。
你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明妙点点头,望向远处的暗蓝色峰峦。
凉若有点相信她没说谎,她回到房间中央,觉得很累,累极了,累很好,让人没力气愤怒。
高海拨的风吹乱了明妙的头发。
你为什么不掉下去?凉若捂住脸:你真让人讨厌,我要把你吊起来用火慢慢烧死。
明妙并不回头,她侧过脸倚在窗棂上,说:黄凉若,我给你唱首歌。
难以驯服的风穿过她,从这扇窗户进来,从另一扇窗户出去。凉若也被同样的风穿过,她们是一根线上的珠子。
在古老的月亮之下,歌声轻柔,她唱:歌舞升平孤单朝秦暮楚虚荣怎么样才能得到你的眷恋一生如灯火挥灭千年也如此度过我依然在你身边只一瞬间凉若忍不住抽泣起来。
太残忍了,你太残忍了,这风太大,让我觉得很伤心。
那天晚上,黄凉若哭了很久。
她的瞳仁颜色浅淡,光可以进入最深处,她看着我,好像是身体里最厉害的一部分在往外挣,迸发出一种难以言传的激情,犹疑的人会被她吓到。她很美,脸部线条硬朗,似乎一下子就能燃烧起来,大概就是这样的火焰让桑青难以抑制——在凉若面前,男人的渴望总是难以掩藏,如同一座岛屿从海底猛烈地涌现。
我从未听过这样的哭声,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她让人感到整个世界都不值得留恋,没有一点温暖的地方,听见她这样哭,连仇人都想去安慰她,甚至赴汤蹈火地去救她。
天快亮的时候,凉若哭着朝通天河走去。那天起了大雾,什么都看不清楚,我跟踪她深一脚浅一脚,在大雾中呼唤她的名字,嗓子也哑掉了。她瞪着我,恨我,这持久的恨足够我从容不迫地从一数到七,当我数到六的时候,她肯定会一刀扎死我。她和我一样,失去了桑青,这世界上果然还有一个人,和我一样在受苦,遭受到命运严厉的责罚,就是她。
我在河岸的荒草里找到凉若。
通天河水寒冷澄澈,她伸开手臂抱住自己,头发很长,如同浓密乌云披散。我摸摸她肩上的头发,眼泪正扑簌簌地从她脸上落下。
折腾了一夜,她不再强硬了:我很孤独,我不愿意爱他了。
那就别孤独。
如果这时候他就在眼前,你怎么说?
我看着浓雾深处,想着桑青从那雾气中走出来,心重重跳了一下:如果他出现,我要亲吻他,这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情。
她抱怨着:这可怕的命运、可怕的人,我根本不必看见你,我和你不是一类人。
是的,在最难的时候,人还是得依靠人。我拨开她脸上潮湿的头发,也觉得心酸:凉若,我需要你,不要讨厌我,不要让我一个人。
她心烦意乱,捂住脸说:李明妙,你很奇怪,你是我遇见的最自然的人,但自然在你身上的表现很奇怪。如果你是一个男人,我要追求你,渴望被你爱慕,因为你这样的男子从未出现过。
让我们重新认识吧,也许会感觉好一点。
我伸出手:你好呀,我是李明妙。
她犹豫了一下,也伸出手:我是黄凉若。
同样冰冷的手指,握在一起,也有几分暖意。
接下来还需要一点时间,用来澄清我和她之间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