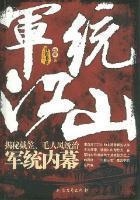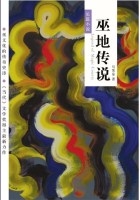连续两个多月,每天工作到很晚,乘末班公交车返回,云榕在车上睡着。好几次,他的头滑下来依靠在明妙肩上,努力地睁开眼睛,说对不起,慢慢又滑下来,终于放弃了抵抗,困顿沉睡。他头发上有马栗树和杜松的清远气息,这气息背后,应该是一个稳妥康宁的家庭。明妙让他倒下来,用手掌托住他的脖颈,让他睡得更舒服一点。
深沉夜色中,公交车晃晃悠悠穿过长安街,深夜的长安街心平气和,和白天完全不同。
明妙有一次在这里迷路,找不到要去的地方。那天大风又大雨,有个陌生人送给她一把伞,不幸的是,他送了她伞,但他指错了路。她又湿又冷,躲进路边的电话亭,一对年轻的恋人站在里面,男孩子撩起衣服给女孩子擦头发,女孩子正在生气。
明妙看了他们一分钟,把手里的伞递过去说:送给你们。
她走进大雨里,更湿更冷了。这真是悲惨的一天,唯一美好的事情,就是一把送来送去的伞。她仰头微笑:陌生人,命运开始对你好些了吧。
到站了。明妙摇醒手心里的男孩,拉着他下车。
男孩微闭双眼,跟随她的脚步,流露出全然的信任。一直走到胡同深处,明妙掏出钥匙,转过身等他完全清醒,平静地问:你要住在我家么?他眼角细长,呈现出优美的弧度,有点犹豫不决。明妙并不等他回答,转身开门,他也毫无主见地跟随进来。
她拼起长桌,让他睡在上面。
男孩入睡很快,呼吸宁静,醒来已近中午。他沉默地找了一会儿,明妙不在。单人沙发上有一只托盘,奈良造的碗和水杯,盛放简单早餐,旁边有一支牙刷,一个笨重的锁,她在明信片背面留言:锁门。要再锁一道。
回到公司,云榕又看见她,不由得心跳加快。可是她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盯着电脑屏幕,咬铅笔,思考的时候竖起脚尖。
她的侧脸线条锐利,眼白微微发蓝,她完全不看他。八秒钟之后,她还是不看他。云榕转身走开,过了很久,他感觉到胸口憋闷。
他们继续合作那本书。明妙总是随手拿到什么东西就开始写,皱巴巴的纸,圆形树叶,一片瓦,海报女郎的白胸脯。云榕在废纸篓里捡到一个扇贝,上面也有她的字:我还为你留了一颗牛奶糖。
这样没头没脑的一句话,让他彻底爱上她。
书稿交出后第五天,明妙和云榕走进了老板的办公室。
你们来了。老板把手里的一本画册放下。
明妙试图从他的声音里判断是坏消息还是好消息,但完全听不出来。
老板点点头:我看了你们的书,很不错。
云榕缓慢地露出微笑。
不过,老板看看他们,说出了最令人泄气的一句话:对方高管换人了,方案要推翻重来。
老板通知他们,明妙所写的内容都不能用,图画部分需要调整百分之八十,公司希望仍然由他们二人合力,完成新的绘本。
明妙靠在半透明的亚克力墙上,淡淡地哦了一声,似乎这是与她不相干的事儿。
云榕老老实实坐在椅子里,过了好久,脸上终于浮现出失望的表情。
他是个木讷的男孩子。
明妙看过书上的小故事,说一个男子口渴,走到泉水边,喝了个痛快之后,发现泉水还是不停地涌出来,他站在泉水边发呆,渐渐有点恼怒,责怪那泉水:我已经喝饱了,你还一直涌出来,太浪费了吧。
明妙呵呵笑,在书的空白处画个呆呆的小人儿,旁边写两个字:云榕。
她觉得这就是云榕的故事,木讷的男子有时候很让人喜欢。
结束工作已经是深夜,天空是紫紫的颜色,几缕透明的云缭绕,这么美,让明妙以为有什么又大又坏的事情就要发生。
她关掉电脑,关掉走廊里的灯,登上屋顶抽烟。她抽小姑喜欢的茶花烟,烟盒上有两行字: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小姑留下的那盆高山茶花,明妙养了很多年。小姑爱花,有时与男人一夜欢好,只是因为那人送来的花又白又香,恰好是她喜欢的,不忍心让送花的人失望。
在很多人看来,她是多么随便和荒唐的女子,可是明妙知道她一字一句,都是真心话。她不忍心让别人失望,她看重所有人,包括那些唾弃她和伤害她的人,她一心一意想要让他们喜欢。
傻瓜,我爱着你,傻瓜。明妙猛猛地吸了一口烟,在一片漆黑中,眼泪掉下来。
手机嘀地一响,收到短信,是云榕发来的:我想辞职,我对自己很失望。
明妙拨通他的号码:喂。
他应了一声,明妙愣一下,挂断了电话。
原来他也在这里,在屋顶上。
她叫他:云榕。再叫一声:云榕。
男孩慢慢从角落里走出来,坐在台阶上,还为她带了一块蛋糕。
明妙把手里的烟盒放在他腿上,吃了一口蛋糕,栗子的,放了碎核桃。
云榕,你为什么在这里工作?
他回答:在电影院,有个女孩咬了我一口,她是这家公司的,我就来这里找她,在这里上班了。可是她有男朋友,他们结婚了,后来她回家生孩子,不来了,我留在这儿,也习惯了。
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这些。明妙掰下一小块栗子蛋糕,送到他嘴边,他乖乖吃掉。
云榕,很多事情都是徒劳无功的,明知这样,我们还是要工作,如果工作可以赚到一百万,为什么不呢?我们还是要恋爱,如果恋爱能让你更喜欢自己,只管去做。
他小声说:我对自己很失望。
那你就记住这失望,一切都会失去,连失望也很快会失去。
他又变呆了,他身上铜墙铁壁一般的木讷,倒也具有某种力量,让他在任何处境下都不至于受到很大的伤害。
明妙,如果可以穿越,你要去哪里?
我最想去的地方,是伦敦,我要回到“二战”时期。你看过那些老照片吗?二战时被轰炸超过了七十六个昼夜的伦敦,人们仍然排队去看《费加罗的婚礼》,在干枯的喷泉旁边,人们散步,讨论,阅读电影杂志,街头照样有魔术表演,还有人发明了专门的工具,让姑娘们在光腿上画出袜子。
在苦难降临的时刻,人们接受孤独,接受失去,接受自己是不完整的,偶尔会被变故打败,可是谁也不必被苦难变坏。这多么好,我喜欢他们的脸,很温柔,我希望像他们。
云榕听着,慢吞吞地说:明妙,你可以和我约会吗?
她从最高的台阶上跳下去,拍拍牛仔裤,回答他:好啊。
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约她看电影,吃饭,散步。没喝完的半瓶矿泉水,云榕拿过去,塞进牛仔裤屁股后面的口袋里,另一只手伸过来,轻轻牵住她。明妙忽然愣住,直勾勾地看着他的手,这个动作是她从未见过的,它不属于真年,也就从未在她的青春里发生过。
明妙忽然意识到,她已经很老了,实际上还从未年轻过。
他们一起去海洋公园。明妙喜欢看巨型生物,鲨鱼和白鲸,她把脸贴在玻璃上,鼻子挤得扁扁的,看着白鲸在半空中缓慢游弋,觉得安全。春天,一只海豚怀孕了,云榕在水族馆看见告示:海豚宝宝将在三个月后的某一天降生。他们很高兴,每隔半个月就去水族馆看看,换乘好几趟公交车,穿过越来越大的城市,在路上听歌,讨论海豚宝宝的名字。
周末,他们又来到水族馆,水箱上贴着新告示,海豚宝宝出生时就死掉了。
这里空荡荡的,听说海豚妈妈孤单地游了一天,它转着圈子,一圈又一圈,忽然就发疯了,猛烈地撞击水箱。训练师赶来,没办法让它安静,医生给它注射了针剂,运去别的地方,不再见人,它需要独自待着。
明妙看着那个骨肉分离的水箱,忽然微微发抖,她用手心抵住一堵墙,从脚底到头发,哗啦啦越抖越厉害。云榕呆呆地看了一会儿,想要拥抱她,她竖起手臂,仿佛竖起一柄刀,不允许他靠近。
我需要一个人待着。
她丢下云榕,独自回家,两天没去上班,也不接云榕电话。
她抽光了所有的烟,长时间地站在浴室里,让热水冲过头发、锁骨、小腹和脚背,直到感觉可以再活一遍。邻居放着闹翻天的摇滚乐,她走出房间,打开门。
云榕站在门外,靠着墙,不知道来了多久。
他把她的大门整个涂满蓝色,海底一样柔软,画上了一只海豚宝宝,它睁开聪明的眼睛,露出人类才有的笑容。明妙一言不发,看着门上的海豚。云榕鼻尖上渗出一点点汗珠,他嘴角动了动,什么也没说,然后转过身,伏在墙上写着什么,一张明信片。
明妙接过明信片,翻过来,是墨迹未干的几行字:你坐在屋顶上,所有人对你一见钟情,我还为你留了一颗牛奶糖。
我要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就好了,就能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一直是这样想的,我想和你做个爱,我真的好想啊。
明妙盯着这几行字看了又看,微笑起来,她说:知道了。
无论等待你的是什么,那就是唯一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