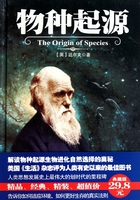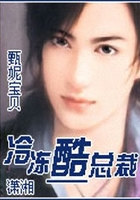清晨七点,土登寺正殿前的甬道上。
下了早课的僧人与来此朝拜的弟子们走在雨水里,三三两两结伴而行,或独自拿着念珠持咒,或轻声聊天。江阳堪布和穿着白裙子的瑜伽士文青走过来,弟子们恭敬地停下脚步,侧立路边,让老师先行。长长的甬道上,他们静默地合掌而立,红色僧袍被雨水浸湿,转成暗红色,在庄严的白塔下显示出肃穆的气息。
再过几个月,土登寺将有一个盛大法会,白塔将被开启,遵照秋英多杰仁波切的遗言,来到这里的人们可以进入白塔,登上最顶层,那里安放着他的法体。他说过:你们将亲眼目睹一个非凡的转化。究竟会是什么?秋英多杰仁波切并没有解释。
江阳堪布认为,这将是一次伟大的传授。
只要江阳堪布在寺庙里,就不断有人来找他,讲课,诵经,请教一些修持方法,他要给亡故者做祈祷,给陷入痛苦和失恋中的人做心理辅导,翻译经文,整理书稿。搬新房子的人也来找他加持。有时候,他提供食物和场地给一些人,协助他们完成一年到三年的闭关。
他非常忙,今天早晨来不及吃饭,手里握着一块硬的糌粑。
众人跟随他进入大殿,在这里打坐。
佛祖说:佛是过去人,人是未来佛。
有人问:那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佛?
江阳堪布神色庄严:大成就者早已说过,佛的伟大,不在于神秘。凡人悉知的,做不到,有人知道,相信,并且做到了,他就是佛。神佛就在你身体里面,人之所以能够历经劫难地活着,唯一的动力就是重塑自己。
明妙坐在大殿角落,抄写佛经上的话: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藏,犹如地藏。
江阳堪布说:虽然人容易失望,容易糊涂,容易多疑,犯种种错,有种种坏习气,但你还是要爱人,爱各种各样的人。
广场上,弟子们虔诚地跪在雨中,无遮无拦。
江阳堪布带领学生们念受戒词:我们发愿,当众生生病的时候,我愿意是他的药,当众生要过河的时候,我愿意是他的桥,当众生要写东西时,我愿意是他的纸和笔,我愿我能化现成众生所需要的一切。因为受了菩萨戒,我就是众生的仆人。
雨水顺着他的脸颊潸潸而下。
明妙抱着一盆高山茶花,这是小姑留下的。
她要去花木市场,她正准备离开这城市。
一个白胖子经营着最大的花棚,养着上千棵杜鹃花、很多热带植物、两条黄狗和一只爱生气的八哥鸟。明妙把自己那盆花往地上一放:老板,这花送给你行不?
白胖子用鼻子说了一声,嗯。
明妙转身就走,大风豪迈地卷过来,这下她可以一干二净地滚蛋了,这城市再没有什么东西是她的。
她跟父母告别,说我要去北京。
母亲好半天没说话,明妙狠狠心,又说:我是来通知的,不是来商量的。
她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找到工作,租住在四合院里,十五平方米的房间,搭建出来的厨房和浴室在对面,院子里有棵老树,挂着很小的铜牌,写着:榆树,两百年。不知是谁在树干底部刻下短句,明妙尝试辨认那些依稀的字迹:他死了。
灵魂埋藏在粪堆中。
明妙很高兴住在北京,这个城市的尺寸大到失控,她不需要和任何人主动说话,是个真正的陌生人。
改变并没有那么难。
她买回铁条、木板、藤条筐和各种钉子,叮叮当当,把十五平方米的房子弄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她换了手机号码,有了新同事,还剪了短发。她把头发捐了,捐给白血病儿童做假发,年轻的医生对她吹口哨,拉着她拍了一张照片,交给护士印出来,贴在医院墙壁上。
这些欢天喜地的鼓励,让明妙变得柔软,以后遇见再坏的人和倒霉的事,她都想,自己曾经被温柔地对待过,并无堕落的权力。
只有一次,半夜里高烧,烧到晕眩,每一样东西都摇摇晃晃,它们越来越小。她不知道找谁求助,也喝不到水,孤独地睡了三天,皮肤上烧出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
持续做梦,梦见自己撑着一把荷叶伞,穿着一双绣有金鱼和莲花的鞋子,踢踢踏踏走去花下立着,茉莉正开,浅浅金黄,真年就站在面前,伸手来触摸她的头发。缓慢地醒过来,抬手摸摸眼睛,干干的,心里却比梦里难过。又昏昏睡过去,似乎听见一朵花呱嗒落在地上,真年来了,躺在她身边,离得那么近,两人鼻子碰着鼻子,她看不清楚他的样子,呢喃叫他:真年。他贴得更近一点,含住她的嘴唇,舌头清凉湿润。
不知过了多久,再次挣扎着醒来,眼睛还未睁开,她喊了一声,真年。
四下无人,窗帘上透出一片灰白的光亮。
她舔舔嘴唇,褪下来的皮层层叠叠,堆成一个硬邦邦的壳,她闭紧嘴巴,再也不喊他。
她躺在那儿想:真年曾经一时兴起,带她看了三天样板戏。
他说,《白毛女》中那个红头绳,看过有种冲动,想要把所有东西都给别人。明妙学会唱红头绳,唱了喜儿,又压低嗓子唱杨白劳,然后摊开手心,说:我要你一行眼泪,给我。
真年大笑。
明妙招手呼唤他过来,在他耳边悄悄说:最不难过的女人哭得最凶。
哭和抱怨最没用,她只是遇到了现实。
碎成一片一片的人,倔强地把自己一片一片粘好。
她曾经心存期待,期待他更勇敢地爱她,他做不到;期待他保护她,他做不到;期待他忠于他自己,他也做不到。的确,他不是为了她的期待才出现在这里,可他毁坏了她的初心。她吃到苦头,如同一只被打断了翅膀的鸟,再也没有能力飞翔。接受这后果也很苦,要咽下一万种坏,只有一个好处:真年,对你不存期待之后,再想起你,我心里不动了。
明妙开始专心工作。说话的时候在工作,坐车的时候在工作,吃饭的时候在工作,躺在床上脑子里还是想着工作。这倒是不错,拼命工作,让人没时间多愁善感。身体和头脑都被用到极限,睡眠更糟了,睡不着,就什么也不做,呼吸,听一点点音乐,冰岛女王的声音,有时候是巴赫,没完没了的平均律。别的什么也不行,她只需要枯燥的夜晚。
有人追求,明妙从不跟他连续两天一起吃晚餐。
他很好奇:我见不到你的晚上,你都怎么过?
什么也不做。
他难以置信:一个人怎么可能什么也不做?
好吧,我去见另一个男人。她不动声色: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我不知道更喜欢谁,所以我今天见你,明天见他。
他的脸变难看了:他是谁?
一个建筑师,没什么名气。
他长时间地凝视着她:你必须做出选择。
好吧,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
吃完饭,明妙删除了他的电话号码,准备去买个平底锅,煎一个金灿灿的鸡蛋。这样过了几个月,明妙越来越关心自己了,这让她很满意。
十九岁,她遇见他,二十一岁,成为他的情人,二十六岁,离开他。
这些年的这些事儿,一句话就说完了。
现在她不再是个孩子,在北京,李明妙是一个能够赚钱养活自己的女人。
为了把旧的扔掉,要让新的进来。明妙遇见了云榕。
云榕是公司制作部门的美术编辑,善良的北京男孩,安静,长着好看的手指。
他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她知道他叫云榕,他知道她是李明妙,每天擦肩而过。
在停车场,她看见他,用手指在脏的车上画画。
他喜欢MarkBryan,一个美国画家,风格既奇幻又古典。他画一千个士兵的头骨拼成乔治·布什的脸,他们是第一批死于伊拉克战争的士兵;他画耶稣被导弹发射到半空;画个弥勒佛,抽烟喝啤酒戴着大钻戒,搂着比基尼女郎,女郎望着窗外,一点儿也不爱他。
云榕模仿他,画骷髅一家的下午茶时光,骷髅爸爸和骷髅妈妈很甜蜜,爸爸爱Armani西装,妈妈系着粉红色围裙,往咖啡里加一勺白骨,骷髅宝宝骑着一匹胖兔子在农场飞奔,他的宠物是一条鲜绿的蛇。
公司让他们共同制作一个大客户订制的广告绘本,云榕画画,明妙写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