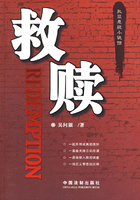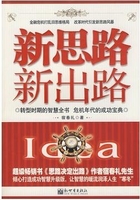自元宵节之后,皇上似乎对雍婕妤多了几分宠爱,不时驾临观止园,雍婕妤喜不自胜,对沾衣也格外赏识,但凡外事,或带沾衣出行,或由沾衣代办,使得沾衣在观止园中地位陡然上升。沾衣也不负所托,将观止园打理得井井有条,再加上她慷慨仗义,乐善好施,在观止园上下有口皆碑。
有民谚云:“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二月初二,民间认为是天上主管雨水的龙王爷抬头之日,这以后,雨水会逐渐增多,所以这天又叫“春龙节”。每逢此日,民间欢庆不提,皇上也携众皇子陪同太后到京城西郊的安国寺进香,皇后与后宫众女眷从行,雍婕妤自然带了沾衣跟随。皇帝出行,侍卫头尾护驾,宦官们前后簇拥,浩浩荡荡,场面宏大,不多时便到了安国寺。
那安国寺原名京锡庙,早在前朝末年,传说庙中和尚曾助先祖逃过敌兵追杀,让先祖得以九死一生,后复起兵大获全胜,开国元年,先祖捐重金修缮扩建庙宇,御赐匾额曰“安国寺”,自先祖以后,历代皇帝逢年过节,总要前去上香,以祷祝江山稳固,社稷安康。
进香完毕,沾衣扶雍婕妤进房安歇,起身到茶水间寻水沏茶,经过柴房时,忽觉身后一阵冷风掠过,下意识侧身一让,右掌向后拍去,不想手腕被人捉住并后拧,她正待反手破解,却被猛然拉进柴房,随即听得喀嗒一声,房门被从里闩上。沾衣一惊,出左肘猛顶对方下胁,却被对方避让开去,沾衣就势右手反扣,一别一推,甩开对方的嵌制,跃后站稳,此时就着窗口透进的光亮,看清眼前不速之客,只见他头戴束发金冠,身着枣红朝服,龙纹镶边,玉带紧箍,面孔俊美,英气逼人,不是祐骋又是谁?
“三殿下?”待沾衣看清眼前之人,不由惊呼,急忙下拜。
祐骋捉住沾衣的胳膊,不教她继续拜下去,就势将她拉近身边,与她正面相对。“真没想到,那日我的救命恩人,竟是宫中侍女。”
“奴婢也没想到,那日所救之人,竟是三殿下您。”沾衣一边回话,一边努力不使自己离祐骋太近,然而这三皇子乃习武之人,臂力无穷,沾衣又不敢运功挣脱,一时间又被祐骋拉得更近了些。
“三殿下!”沾衣急道:“请放开奴婢,娘娘那里还等着奴婢回去伺候……”
“我让你害怕么?”祐骋双目炯炯,盯住沾衣,“为何每次你离我一近,就总想逃开?”
“三殿下威风凛凛,气度不凡,奴婢所以不敢靠近。”沾衣低声道。
“哦?”祐骋挑起眉毛,似笑非笑,“如此说来,我在源北村养伤之时,你就已知晓我的身份?那为何敢与我平起平坐?为何敢对我隐瞒你的去处?又为何敢对我动武?”
祐骋这最后一句让沾衣一惊,随后想到那夜为了阻止祐骋起身,不得已点了他的穴道,现在想来,的确大有不敬,于是索性沉默不语,目光移向别处,此刻祐骋便趁机定睛打量她,发觉她肌肤嫩白,细腻光滑,睫毛修长,微微颤动,樱唇紧抿,似含微怒,发肤间又透出一缕少女特有的幽香,沁人心脾,不由心旌摇荡,几欲把持不住,极想拥她入怀纵情热吻。沾衣发觉祐骋胳臂愈箍愈紧,甚至感受到他吹出的灼热气息,心知不妙,便发力挣脱。祐骋本无他意,但沾衣如此一挣扎,反倒撩拨起他正极力按捺的念头,于是将她强拉入怀,紧紧搂住,扳起她的脸,滚烫的唇便覆了上去。
沾衣冷不防被祐骋吻住,只觉得一阵恍惚晕眩,慌乱中更是极力挣扎,祐骋岂容她挣脱,自是愈搂愈紧,索性将她抱起,不料站立失衡,两人一同滚倒地上,沾衣一时情急,发指猛戳在祐骋胁下,祐骋闷哼一声,当即软倒在地,一动不动。
沾衣翻身立起,正欲扶祐骋起身,发觉他竟不省人事,气息奄奄,搭脉一测,脉息甚微,顿时慌了手脚,以为自己用力过猛,祐骋虽也习武,可毕竟是金枝玉叶。眼下看祐骋双眼紧闭,脸色苍白,只觉得心急如焚,顾不上许多,当即解开祐骋衣扣,为他推血过宫,见不奏效,又扶起祐骋靠在自己怀里,从后背穴位输送真气给他。几番尝试,祐骋依旧沉沉昏迷,沾衣一筹莫展,伏在祐骋身旁嘤嘤啜泣起来。
少顷,沾衣满脸泪痕抬起头来,惊见祐骋躺在那里,正笑眯眯望着她,不禁大喜过望:“三殿下,您……无碍了?”
“当然无碍,有佳人为我推拿运功兼暗弹珠泪,我怎敢继续有碍?”祐骋狡黠笑道,同时一跃而起,顺手拉沾衣起来,敏捷如初,全然不似受过伤。
沾衣才明白祐骋刚才的晕厥昏迷全是做戏,不由哭笑不得。祐骋笑道:“适才为试出你的真正心意,只好出此下策。见你如此担心,也不枉我卤莽这一回。”
沾衣后退一步,恢复为谦恭冷静的神色,欠身道:“三殿下若出了闪失,奴婢非但性命不保,怕也要连累爹娘和雍娘娘一起担待,所以奴婢才这般担心。”
祐骋敛住笑容,望定沾衣,道:“你骗得了你自己,却骗不了我,同为担心,却有担心自己性命和担心他人性命之分,你那种担心,与你当时在源北村同出一辙,分明是担心我有性命之虞。”
“三殿下此言差矣,奴婢自知功力浅薄,根本不是三殿下的对手,又如何能让三殿下有性命之忧?”
祐骋上前一步,抓住沾衣肩头,迫她也看着自己眼睛,“当初在源北村,我失足坠崖,恰为你所救;东郊一别,都以为今生永无机会相见,谁想京城之大,你我后来竟能重逢于宫内,上天都如此安排因缘,你又为何不肯承认你对我有情?我都不会瞒你,你为何要瞒你自己?”
此番话正说中沾衣心事,她登时面红如霞,嗫嚅着不知说什么好。在祐骋还化名为“干骋”在源北村养伤之时,她就已芳心暗许,却耽于宫中严规,终究不敢吐露心迹。东郊别后,原以为这份情可随岁月或逐渐淡漠,或永埋心底,谁知那“干骋”竟是三皇子!天下亦大,天下亦小,天下情缘的辗转起伏,这皇宫里也有份,然而祐骋贵为皇子,自己不过一介宫女,如何敢斗胆表白?若不是今日祐骋强问,自己怕是要守口如瓶到不知何年何月。
从沾衣面色变化上,祐骋已看明她的心意,于是欣喜拥她入怀,这次沾衣不再挣脱,轻轻依偎在他的胸前。人世间最幸福之时刻,莫过于发现所爱之人也深爱自己,这感觉升腾起来,什么门第身份的担心,统统化为乌有,此刻唯两情相悦,共沐爱河,周遭万物似不存在。
良久,听得祐骋在她耳边一字一句轻声说道:“沾衣,做我的慎王王妃,好么?”这句问话如同一道霹雳,震得沾衣浑身颤抖,推开祐骋后退数步,背靠着墙站在那里,祐骋不禁愕然。
沾衣低声道:“奴婢出身卑贱,因沐皇恩,进宫侍奉,能得三殿下垂青,便是上天的莫大恩宠,又如何敢觊觎王妃之位?”稍停片刻又道:“三殿下若真中意奴婢,可让奴婢进府伺候,能时时见着殿下便足矣。而让奴婢做王妃之事,再也休提。”说罢已眼含泪花。
祐骋立时明白了沾衣的意思,历来皇子婚姻须由皇上做主,几乎无人能自行决定,纵然情浓爱炽,王妃为谁依然要看出身;而婢女则不同,只要皇子欢喜,任谁都可以叫进府来侍奉。可祐骋目前除了沾衣,对于其他女子是不肯闻也不肯问,若宠爱沾衣却不给名分,便免不了让她在日后遭人嫉恨,无异于将她推入火坑。再者祐骋毕竟年少气盛,自忖在父皇面前倍受宠爱,心想若破例一回,父皇也未必不允,于是说道:“我祐骋喜欢的姑娘,是万不可委屈半点的,又怎能让你屈居人下?区区出身,不足为怯,等他日我再立战功,便求父皇做媒,迎娶你进慎王府。”言语铿锵,掷地有声。
沾衣抬起头来,凝视祐骋,此时眼中深情一览无余:“只要殿下欢心,奴婢别无所求。”
祐骋牵着沾衣的手,解下腰间玉佩,道:“这玉佩是我四岁那年父皇所赐,今日有苍天为证,你我在此折玉为盟——石烂海枯,永不相负!”说罢将玉佩一折两半,一半揣入怀里,另一半放入沾衣手中。沾衣紧紧握住手中那半只玉佩,泪光盈盈。
此时忽听外面一阵喧哗,沾衣惊起:“糟了,皇上起驾回宫的时辰已到,奴婢得赶回娘娘那里。”匆匆夺门而出。出门没几步,迎面正撞见乔公公,沾衣禁不住心下忐忑,不敢抬头,轻施一礼,掩面飞奔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