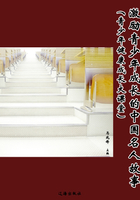竹笋
有人说,竹笋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种雅食。很符合文人雅士的心情与口味、松、竹、梅被称作岁寒三友,竹子自然成为清高的象征。中国有竹文化,竹笋是竹文化中脍炙人口的一个“零件”。它使竹文化的韵味进入饮食领域。或者说,构成竹文化的一部小小的世俗读本。苏东坡有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不俗加不瘦,竹笋加猪肉。”谦谦君子,总能为自己的馋找到种种借口。竹笋加猪肉,既解了馋,又不至于太失去境界。类似于“大隐隐于市”的说法。这样,鱼和熊掌就可兼得了。隐士们的自我安慰,确实比阿Q之流的精神胜利法更为高明。
人们经常拿竹笋与猪肉相提并论,在于它们是最佳的荤素搭档。李渔说竹笋:“以之伴荤,则牛羊鸡鸭等物,皆非所宜,独宜于豕,又独宜于肥。肥非欲其腻也,肉之肥者能甘,甘味入笋,则不见其甘而但觉其鲜之至也。”在这一搭配中,笋是唱主角的,肉纯粹为他人作嫁衣裳。“比蔬食中第一品,肥羊嫩豕何足比肩。但“将笋肉齐烹,盒盛簋,人止食笋而遗肉,则肉为鱼而笋为熊掌可知矣。”
苏东坡的妹夫,黄庭坚,也有诗:“南园苦笋味胜肉”。假如让他从二者中取舍,结果是不言自明的。早在唐代,白居易的《食笋》诗就表明态度:“每日逢加餐,经时不思肉。”笋能使嗜好者忘掉肉的,或三月不知肉味。在无肉的情况下,将笋单独白煮(略蘸酱油而食),或素炒,也能品尝到其真趣。“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此类是也。”(李渔语)看来笋与肉的关系,也能分能合。正如好小说,不见得都有或非有“性描写”。洁本”的竹笋菜,照样耐人寻味。
李渔认为笋之所以“能居肉食之上”,其至美之所在,仅仅是一个“鲜”字。有经验的厨师,连焯笋之汤都舍不得倒掉,每做别的菜,就兑一点进去,相当于味精了:“食者但知他物之鲜,而不知有所以鲜之者在也。”笋之调味,快达到魔法的境地了。连残汤剩汁都能画龙点睛,把一道新菜全“盘活”了。至于这种奇妙的笋汤(又叫笋油)的提炼办法,袁枚在《随园食单》里详细记载:“笋十斤,蒸一日一夜,穿通其节,铺板上,如做豆腐法,上加一枚压而榨之,使汁水流出,加炒盐一两,便是笋油。其笋晒干,仍可作脯。”
林洪的《山家清供》,给鲜笋起了个外号,叫“傍林鲜”:“夏初竹笋盛时,扫叶就竹边煨熟,其味甚鲜,名傍林鲜。”根据他的讲授,鲜笋最好现摘现吃,一分钟都别耽误,就在竹林边,用芳香的竹叶为燃料,当场煨烤;可见环境或氛围也能激活、增添新笋那天然的鲜美。这绝对是最正宗的“绿色食品”了,不仅就餐环境是一片绿林,烹饪方法也是返璞归真的。不知竹林七贤之类古老的隐士,就地取材,是否使用这种“叫化鸡”式的吃法?鲜笋之可口,堪称“植物鸡”(前面提到的笋汤,也堪称“植物鸡汤”)。
另一本书,《四时幽尝录》,也大加赞美:“每于春中笋抽正肥,就彼竹下,扫叶煨笋至熟,刀戳剥食。竹林清味,鲜美无比。人世俗物,岂容此真味。”想来只有超凡脱俗的人,譬如隐于山林者,才能体会到竹笋至真的味道。而所谓的“真味”,其实于平淡中见神奇。有一颗淡泊的心,才能遭遇这种潜伏的神奇。貌似温文尔雅的竹子,原也有尖锐且敏感的棱角,只不过藏戒得足够深、足够隐蔽。与竹笋未受污染的鲜明相比,我们生活中的诸多食物,堪称麻木的、愚昧的,甚至腐朽的。
竹笋因出产季节的不同,可分为春笋、冬笋。冬笋的味道比春笋还胜一筹。正如少妇与少女相比,女人味更深。郑权桥爱竹成癖,不仅画竹,还为竹笋写诗:“偶然画到江南竹,便想春风燕笋多。”
符中士先生向西方人介绍本土饮食,经常碰到一件难事:翻译们译不出竹笋这个词,只好勉强译成“竹子的嫩芽”或“很嫩的竹子”,以至洋人常常发出“竹子也能吃吗”的疑问。原来西方人不仅不吃竹笋,英语里甚至没有竹笋这个单词。而在中国,《诗经》时代,竹笋就成为食物:“其蔌维何,维笋及蒲。”
从竹笋的待遇,能看出东、西方饮食文化的巨大差异。中国有竹文化,或者说得玄妙点:竹图腾(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折射到餐桌上,吃竹笋也上瘾。而欧风美雨,盛行的是“肉图腾”(女作家潇语),譬如牛排,构成其精神之盾;法兰西人甚至连小不点儿的蜗牛都不放过。以草食为主的民族和以肉食为主的民族,各有各的崇拜,也就各有各的发现与收获。这是两张不可能重叠在一起的美食版图。
我在想,是否有必要教会西方人吃竹笋?我本人倒很愿意做竹文化的“传教士”。竹笋在饮食中堪称“国粹”(甚至无法翻译),也是我百读不厌的“圣经”。它与《诗经》同时诞生,并同时成为中国人的“必读书”。
南有年糕,北有饺子
春节是中国最大的节日。作为节庆的传统,年糕与饺子,各占半壁江山。大抵是南方人习惯吃年糕,北方人更讲究吃饺子。年糕也渗透到北方,但比较单调,只有南方人才能将其做出众多的花样。至于饺子,很明显属于北方的产物,南方也开饺子馆,一般都要打出“北方水饺”的幌子,以示正宗。这犹如某些店铺强调“手工饺子”,与流水线上生产的“机器饺子”相区别。古典的食物,制作方法愈原始愈好,仿佛这样才能保持原汁原味。在江南一带,卖年糕,包装纸上也常印有“水磨年糕”的字样。
虽然中国早就大一统,饮食风俗,还是有地域性的。正如“南米北面”、“南糕北饼”、“南甜北咸”之类演绎,说南有年糕、北有饺子,不能算错吧。尤其过大年之际,它们都是象征意味浓郁的符号化食品,堪称餐桌上的吉祥的经典。即使现有生活条件好了,山珍海味常常喧宾夺主,但因为年糕与饺子对节庆的意义远远大于其滋味,仍无法废黜。
想一想,祖宗八代都是借助这古朴的食物过年的,后人也就不太敢或太愿意叛逆了。哪怕在生活的其他方面,皆以“新人类”自命。估计全家老幼去肯德基、麦当劳吃年夜饭以庆团圆的,应该比较少见。像年糕、饺子这样的“文化遗产”越多越好,已彻底变成中国人的传家宝,不至于失传的。
年糕的名字起得好,喻示着“年年高升”。似乎多念叨几遍,以诚则灵。不仅听起来顺耳,吃起来,味道也不赖。唇齿之间,能咀嚼出南方稻米天然的醇香。而且因其黏性大,口感独特。江浙人家,大年三十晚上总要在八仙桌上摆一盘年糕,作为供品。我小时候,经常把蒸熟后又冷透变硬的糖年糕,切成片,放进嘴里,当时香糖来嚼着玩。奶奶说:“小耗子”又在磨牙齿了。甜年糕,以及一种荤油年糕,可当零食吃;做菜,一般选用清水年糕,无色无味的。
吾乡人办酒席,最后和盘托出一道炒年糕,既是下酒菜,又作为主食。用黄芽菜炒,用雪里蕻炒,如果再加上肉丝,更棒了。上海人把这道菜做到了“顶级”:螃蟹炒年糕。用螃蟹作配料,年糕够荣耀的。螃蟹的鲜香,通过滚烫的汤法,浸透了切成薄片的年糕。有人说:吃螃蟹炒年糕,打你耳光也不会放下。不信试试?
旧日北京春节风俗,也有热气腾腾蒸年糕的,呼应着包饺子,以示米面充足、家有余粮。我想,这作为陪衬的蒸年糕,恐怕是南方人带来的习性。那时候的北京城,南方人已不少了。他们不会因为饺子而忘掉年糕的。更不会因为来到天子脚下,就忘掉故乡。
包饺子,是惟一一处显示出北方人灵巧、南方人笨拙的地方。我指的是手工方面。即使苏州姑娘,能在丝绸上刺绣工笔的花鸟,也不见得包得好饺子。北方人,却能将饺子捏合得天衣无缝,有款有型,用熨斗熨过一般挺括饺子之吉利,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其造型,酷似古代作为“硬通货”的元宝;吃饺子,近似于仪式,象征性地在“招财进宝”。另一方面,借饺子的谐音,取新旧交替、“更岁交子”之寓意。
中国人相信饺子能带来财气,带来好运。如果这算作迷信,也是一种很美好、很积极的迷信。人生甘苦,总应该有一点点精神寄托的,如果它兼而给你带来口腹的享受,倒未必是坏事。人们还将抽签的习俗引进饮食中,包饺子时于馅里埋藏铜钱、银币、宝石、珍珠之类小小的吉祥物,占卜各自的时运。吃饺子的过程,跟抽彩票一样激动。瞧瞧谁能中大奖?更使通俗的饮食多了一份浪漫的憧憬。这才是最好的调味品呢。
在清朝乃至民国,水饺又叫“煮饽饽”。“夏令去,秋季过,年节又要奉婆婆,快包煮饽饽。皮儿薄,馅儿多,婆婆吃了笑呵呵,媳妇费张罗。”这是清代李光庭《乡言解颐》一书中收录的民歌。看来包饺子有助于融合婆媳关系。一笑!
北方还有谚语:“三十晚上吃饺子--没有外人。”以示亲密无间。可见饺子是除夕之夜各家各户庆团圆的必备之物。我的朋友伊沙,写过一篇针对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酷评”:《这锅饺子怎么煮》。他把老牌的春节联欢晚会,比喻为一锅“文化饺子”,是否有新意,关键还看包的什么馅儿。三十晚上北方人不吃饺子,会觉得没有过年的气氛。正如现在的中国人,假如不看春节联欢晚会,一定很空虚。
在节奏慢的时代,全家人围坐一桌包饺子,东聊西扯,是一项很有情趣的集体劳动。包似乎比吃还过瘾。尤其春节,家庭成员悉数在场,其乐融融;谁若缺席,会让大伙儿有“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感伤与思念。哥们姐们,新年钟声敲响之前,一定要赶回家里吃一碗饺子哟。这样的习俗很有人情味的。能遵守的话一定要遵守。
不仅平民百姓,连清代的慈禧太后,都把三十晚上包饺子,当成不可省略的礼仪。叶赫颜礼·仪民,写过一遍《清末宫廷过新年》,回忆前朝旧事。“除夕之夜十二点的钟点将过,太后命众人齐至殿上,排好长案后,由御膳房将事先预备好的各种素菜端上桌,众人一齐下手做素馅都饽饽,于是切的切,剁的剁,大殿之上霎时叮儿儿乱响。切剁好后,都交到太后面前,由皇后、妃子、大公主等人拌馅儿,口味咸淡,由太后决定。天到亮时,饺子已包齐。太后命众人退回更衣,重新梳头打扮。
不大工夫,众人回到殿上。太后坐在案端,皇后等人都站在案旁。太后命宫女把煮好的煮饽饽端上来,太后说:此刻是新年、新月、新日、新时开始,我们不能忘记去岁的今日今时,今天我们能吃一碗太平饭,这就是神佛的保佑,列祖列先的庇护。说完,命大家用膳。大家向太后叩头谢恩。吃罢煮饽饽,天才大亮。”
慈禧太后吃饺子时,确实挺虔诚的:谢天,谢地,谢祖宗。她恐怕想不到:大清帝国,这只包了两百多年的大“饺子”,捉襟见肘,不久就要“漏馅”了。一旦“漏馅”,再无法弥补。
火锅的褒贬
火锅是寒冷的冬天里的救星。因为它有一副“热心肠”。尤其大年三十晚上,热炒端上桌没多久,就变成凉菜了;一家人如果支起火锅,围炉而坐,弥漫的热雾中,顿时显得喜气洋洋。随便拍一张照片,都可命名为“全家福”。火锅带有自助的性质,只要备好了料,就不再需要专门的厨师,守在厨房里;筷子在空中你来我往,不是搛菜就是添菜,好不热闹。它自然是老百姓年夜饭的首选,或首席代表。可以自始至终热情洋溢地陪伴你们一家人看完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没有比它更耐心的了。
火锅的魅力还在于它的丰富性。荤的素的,生的熟的,都可同时或先后下锅煨煮。各种滋味,彼此渗透,又相互补充,反而诞生出诸多新味道。直至最后的那锅汤,变得像“鸡尾酒”一样繁复、醇厚。正好用来下粉丝,下面条,或盛碗热汤蘸着馒头吃。总之,精华全浓缩在里面。
中国的火锅,使人们省了许多事,又增加了很多乐趣。
四川有麻辣火锅,香飘八方,四季皆宜。还有种鸳鸯火锅,中间用铁片隔开,一半是红油汤,一半是清汤,正如王朔小说标题:《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泾渭分明,看上去像八卦图。在北京,最流行的是涮羊肉火锅;当然,也涮肥牛或其他肉类。来过北京的人,没有谁不知道啥叫涮羊肉的。
满街都是。一些店铺的玻璃窗上,都贴着纸剪的一个大大的“涮”字。十五年前,我自南方投奔京都,到到“涮”字,想当然地误念作“刷”羊肉。闹过笑话。相信以后,还会有外来户闹类似的笑话。北京,是我的一字之师。
涮羊肉,本来叫“野意火锅”,据说随清兵入关而传入中原。但绝非满洲八旗子弟首创。我曾猜测成吉思汗的时代,蒙古人就学会涮羊肉了。游牧时,或征伐昌,将金属头盔倒扣在篝火架上,烧开水,投入切成薄片的冻羊肉,边涮边吃,只需蘸一点盐粒。这样羊肉熟得极快,节省烹饪的时间。属于“战时快餐”。如果是真的,想一想也够浪漫:蒙古人靠涮羊肉充饥、御寒,发动了一场征服欧亚大陆的“闪电战”。
后来读到朱伟的《考吃》,才知道涮肉火锅早在辽初期即已风行:“内蒙昭乌达蒙敖汉旗出土的壁画墓,据考就是辽初期墓葬。壁画中有三个契丹人围着火锅,席地而坐,有的正用筷在锅中涮羊肉。火锅前有一张方桌,桌上有盛配料的两个盘子,两个酒杯,还有大酒饼和盛着满满羊肉的铁桶。“契丹人被满族的先祖--金人所灭绝,火锅这一遗产却被后世一代代继承。到了清代,乾隆是最爱吃火锅的一位皇帝,几乎“不可一日无此君”。他不用打仗了,四处游山玩水,各地“招待部门”知道他的嗜好,都提前准备好火锅。乾隆几次举办千叟宴,也以涮肉(包括羊肉、猪肉、鹿肉)火锅慰劳数以千计的“离退休老职工”。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的这首诗,我少小时即能背诵。也是听朱伟先生讲解,所谓“红泥小火炉”,原来指火锅。唐朝的火锅叫“暖锅”,系用陶土烧制而成。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可以边吃火锅边写诗,难怪豪情万丈。又有多少首唐诗,是在温暖如春的火锅边诞生的?
符中士《吃的自由》一书,说除了中国,世界上很少有人喜欢火锅,而中国人热爱火锅,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是火锅能够最集中典型地体现中国人大一统的思想。二是火锅可以使婚姻与血缘关系为基础组成的大家庭,几代同桌,长幼同锅。心往一锅想,劲往一锅使,融融和和,尽享天伦之乐。”他努力挖掘火锅现象后面隐藏的博大的文化前景。中国的每个家庭或氏族,都是以血统为汤料的“火锅”,讲究人丁兴旺、香火不熄。
中国的每座城市,都是三教九流汇集、包罗万象的“火锅城”。至于地大物博的中国,及其五千年文明,更是一口永远沸腾着的大火锅,什么都可以丢进熬煮,包括异族文化。但不管是最野蛮抑或最先进的民族文化,一旦丢进去,终归会被感染得本土化了,或汉化了。毕竟,这是一锅陈年老汤,混杂着最腐朽的东西,以及最神奇的东西。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理解,这口大火锅海纳百川、吞吐自如,吸收了古今中外各种营养。但在某些消极的时候,它又像一口大染缸。甚至,你都弄不清它的本色是什么。
鲁迅当年,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时候,恨不得把这口锅给掀了。他眼睛尖,看见阿Q、孔乙己、祥林嫂、华老栓等等,全在这锅汤里烩着。他觉得中国人不该只顾着喝酒了,应该吃药!虽然这口火锅已习惯了换汤不换药。鲁迅惆怅地放下筷子,把自己怒向刀笔丛中觅得小诗,作为一味猛药,丢进锅里。从此,这口大火锅里又多了一丝药的苦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