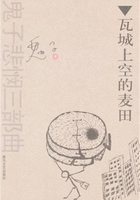霍怀勋满意,可不满足。
一半满意,一半不满足,造成的结果就是脸上阴阳怪气,欲求不满。
他自己不察觉,却看得柳嵩心头像挑了十五桶水七上八下,苦哈哈地劝些好话:
“霍爷,这种事,一次就算了,再来一回两回,草民可撑不住啊!您也体谅体谅小人,小人这不还待在郑家,还没自立门庭吗?别叫小人为难哇。再说了,草民家这姨娘打从遇着了您,可就没安生过,上回在家里为了爷,还被家中烧火的粗使老婆子踹了一脚,这回更是亲自来跟您道了歉……大人是个爱恨分明,心胸宽的真英雄,有仇报仇有怨报怨,可如今,什么仇什么怨都该是烟消云散了。”
霍怀勋眼睛仁儿一闪,摸摸下巴:“被人踹啦?”
柳嵩痴痴点了点头:“还摸了两把呢。”
霍怀勋不是滋味,老子都还没来得及摸呢。
欢娘与袅烟由良哥送回家,跟出门时一样,从后门进了宅子,良哥又将柳嵩吩咐的多说了两句,提醒欢娘休要乱说。
欢娘道:“妾身不乱说,就看舅老爷今后乱不乱做了。”说着拉了袅烟跨过月门,朝东边院子走去。
两人前脚刚离了后院,良哥也出宅回铺去了,对面布着爬墙虎的粉墙后头,却是人影一闪,一名丫鬟着了一身秋香夏布裁成的对襟小衫,探出身型,正是腊梅其人。
日日无事盯着欢娘这头,今儿哪会错漏了。她哪会不晓得良哥是那相好的跟班儿,只贴了门墙后,竖直了耳朵,隐约听见声音飘来:“……今天的事……姨娘主子可千万别……”
腊梅醋意大涌,见着那妖妖娆娆的小身影领着个丫鬟离了,又是说不出的怨恨,一个瘦马馆出来的,凭什么就能使唤上丫头了。
一个身份尴尬的妇人,跑到外头去料理夫主家的店务,还有不能说的事?能是什么好事!肯定是见不得人的事,也必定和舅老爷脱不了干系。
若夫人知道,舅老爷不怕有事,那贱人该有些苦果子吃。
腊梅被柳嵩喝叱过,自然不敢直接出面告状,一路想着又不大甘心,回了下人厢房,烦闷地蒙头盖被睡了,睡到一半被吵醒,门板乒乓作响,见是同住一屋的尤婆子进来,起身骂了两句:“我在睡觉,你大手大脚的,也不能顾忌着一些!”
尤婆子豁着漏风牙回嘴:“就你金贵!睡个觉旁人连出个声都出不得了?拿自己当成千金小姐少奶奶了不成?个丫头片子,不伺候主子,大白日里躲在房里睡大头觉,可甭叫我老婆子在你家小姐前头告一状!”
腊梅叉了腰,正准备下榻撒泼干架,脑子一闪,记起这尤婆子跟欢娘之前有过节,因为欢娘被柳嵩踢过一脚,那日回来还捂着心窝,叨念了一晚上。
告状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粗使活计,何必亲自上阵,留着嘴巴岔,脑子糊的人去做也好。
转了念,腊梅面色一宽,心情好多了,重躺回去,哼笑:“怎么着,你瞧不起下等人?我今天不是千金小姐少奶奶,明天可不一定不是,咱们家不是有开河先例了么。”
尤婆子一听,火引子立马被拉到另一处:“她那也算是主子?比咱们可高不出多少!”
腊梅继续激她:“你这话可就是吃不到葡萄了!你的卖身钱能抵得她一小撮的零头么?她怎么不算是主子了,如今连袅烟那疯丫头都有眼色,围着人家打转儿呢!帮着递东西,陪着铲土挖泥摘花,说一不二!刚还见着从后门进宅,搀得人家紧紧,一同回院子。不是主子能这般奉承?”
尤婆子浊目一转:“东院那人今儿出府了?跟谁?”
腊梅打个呵欠,卷了被子:“谁晓得呢,只见着家中香铺的良哥同她一道回来的。”说着扭过身子,再不多说了。
尤婆子果真上了心。
她想这姨娘出外的事情,家中全没个风声,今日又是从后门偷偷摸摸回来,定是没得过家主允许,找了一日,见欢娘一个人在后院的小圃里采采挖挖,袅烟临时被喊去做事,四周没人,冷笑一声,上前行了个礼。
欢娘打从进郑家那一日被这丑婆子欺辱过一次,之后还没见过面,来来去去的,早将这号提不上台面的人物忘了八八九九,见她主动过来施礼,晓得有些不对劲儿,果然,还没说两句,尤婆子就露了本相,说起那日欢娘从后门出外的事。
那日香铺跟霍怀勋碰面后,欢娘就是个傻子,也明白柳嵩将自己带出的这码事儿,绝对是没给上头回报,回头想想,也是一身冷汗,这会儿虽不知道尤婆子是打哪儿知道看到,只见她一脸的馋相,就晓得,这贼婆子,胆子不小,生了胁迫心。
哎,也不能说她胆子大,谁叫自己就是这么个尴尬位份,区区个烧火柴房婆子,也敢有这份骑头拉屎的勇气?
这婆子,当然是不敢要挟柳嵩等人,只有从自己这里捞油水了。
人善被人欺,位低也被人踩。
是个人就不爱被人威胁,欢娘也不例外,况且还有旧恨没消,那一脚踹了自己肚子,活活疼了三两日。
她来这郑家,可不是为了被个狗眼看人低的下三滥蠢钝婆子打的。
欢娘斜眼睨一下旁边佝偻着个腰的婆子,步履没停,款着编篓,沿了小径,继续查视叶茎,平心静气:“尤妈妈是有什么想法?”
想法可多了去!尤婆子也不遮了,大咧咧的黄板牙外翻:“我老婆子就说欢姨娘是个造化高的,一点就通,叫人省多少口水呢!”
省了你的口水,可别怪折你的寿。
欢娘将枝头一桠成熟了的花瓣肉儿掐下来,扔了篓子里。
尤婆子见她面无表情又没说话,更进一步,搓手道:“老婆子还能有个什么想法,欢姨娘这么个神仙人物,奴婢是肖想不得了,只好求个手头暖和。”
打劫也得看对象,老婆子不单猥琐,还真是栽钱眼儿里去了。
欢娘撩她:“要多少?”停下脚步,转头望住这婆子,看她得有多大野心。
尤婆子一听大喜:“天下人都像欢姨娘这么好说话,衙门都得关门了!”又见她睁着一双乌溜眸子望着自己,看着稚气,似是有几分哀求意,想她不足及笄的小女娃,好哄弄,如今竟还害怕地主动询起价来,也就挺起腰板儿,哼一声,狮子大开口:“奴婢近日手背,玩了两把小牌,输了一笔棺材本,割肉一般,这心哇,痛得很,那就先来……”说着,摊开两只老手,举起来。
十贯钱?还真是敢想。
这肇县县太爷的月俸银子也不到这个数啊。
还有个先呢,看来拿自己当成了长期提款机。
欢娘听那边有脚步传来,似是袅烟干完事儿回来了,轻声道:“十贯岂不委屈了妈妈,不如……”
尤婆子见她嘴皮子嗫嚅,说话极小声,竖了耳朵:“啊?说大些声!”凑近身子,却见欢娘一松手,将篓子甩了地上,还没回过神,肚腹被她一脚撞了个正,摔到地上,好容易直了腰,晓得受了她捉弄,一时大怒,想着如今就算给她点儿厉害瞧瞧,她回头为了遮掩出门丑事,也不敢说什么,正要趁没人,起身刮她两刮子,袅烟已经过来,大吃一惊,忙问:“这是怎么了?”
欢娘委屈:“正摘弄花儿呢,这婆子过来没见着人似的,一头撞过来,把我一篮子成果都弄散了。”又蹲下身去,一片片捡起来。
尤婆子不好说什么,嘴巴里叽里咕噜地骂骂咧咧,拍着屁股站起来。
人都免不了怜惜弱的,敌视强的,况且袅烟一贯就疯癫蛮气,又好打不平,今儿也不例外,见这当下人的婆子撞了人没个悔改,欢娘反倒还默默捡东西,一股子火气就冒上来,拉了欢娘手腕子,将篓子甩给尤婆子,朝欢娘道:“还搞反了吧!太欺负人!叫她来捡!不捡干净了,甭说我跟她没完,绣绣小姐那边沐身的玫瑰花露没得用,也得叫她不下地!”
欢娘却打发袅烟先走一步,将尤婆子喊住,笑眯眯:“刚出口气叫她跟自己单独回屋。
尤婆子刚受了一脚,毫不清楚你这不是拿了柳嵩支的那半吊子钱,给了尤婆子,
尤婆子经这一事,又添一笔仇怨。
如欢娘所想,尤婆子自然不敢去找柳嵩麻烦,柳嵩是夫人家的亲弟兄,夫人那头就算不知道,告状也是撞南墙,琢磨来去,去了瑞雪院,将这事儿私下告诉了高姨娘。
打从柳倩娥填了房,高姨娘下半生也没什么别事做,除了千方百计将老爷勾得死死,就是等着一个个叫主院那人不好看的机会。
平时的小打小闹,至多就是给柳倩娥添一口闷气堵着,无伤大雅,这事儿倒是能伤她元气。
自家弟弟住在夫家,还将买来给继子院内填冷寂,蓄香火的妾运出去,再怎么的,也是她这当主母和姐姐的,管制不严,败坏了家风。
郑济安岂能容。
这么一想,高姨娘坐不住了,拿定主意,给了尤婆子几锭银子,打发她回县郊的老姊妹家住几日,先不要回郑家,后脚打算跟老爷吹风去。
尤婆子得了银子,也就收了个包裹,找管家告了假,屁颠屁颠地出府,等高姨娘另行通知。
这些日子郑济安尚在养伤,本来快好了,孰料换季染了些风寒,脚伤化脓,有些缠绵之势,加上曹家庄在众人面前摔跤,脸面上过不去,又趁机躲霍怀勋,干脆暂在府门挂了回避牌,闭门不见客。
过了几日,嫌主院这边人来人往,闹人,拣了后头一处清净小院,搬了过去休养。
本来是高姨娘一直随旁照顾着,柳倩娥那日领了妙姐过去,说她照顾了这么多时,也该歇歇了,又将妙姐暂安置在主院的耳房内住下。
高姨娘无奈,当天回了自己院子。
次日她再晃去主院那边,见柳倩娥那个家乡带来的随从老妇焦婆子被放在门口照应,每回不是说老爷刚服了药睡下了,就是说妙姐正服侍着老爷,不便。
这日难得瞅准了时机,撇开妙姐,柳倩娥也不在,高姨娘终于进去同老爷打上照面,才说两句,散了性子,挨过病榻前,贴得牢牢,呢哝:“老爷,妙姐年纪小,不会照顾人,瞧这些日子把您都给伺候瘦了……”还没撒完娇,纱窗外头黑影一闪,那焦婆子又像个黑面神似的,在门口盯着。
高姨娘被她盯着瘆人,觉着自己像是个囚犯似的,心里毛躁得很,翻不出个浪花花来,慰问了两句,也就走了。
这次告状也不例外,高姨娘去了两回郑济安那边,还是被焦婆子挡了,只得暗下咄骂着,悻悻而归,再想法子。
焦婆子见高姨娘这几日来得特别勤快,每次还獐头鼠脑的朝里望,比前段时日还要迫不及待,一张脸还火急火燎,姜是老的辣,晓得肯定有问题,自然跟柳倩娥说了。
柳倩娥支了个口严又灵活的丫鬟,在高姨娘的贴身婢子那边三言两语暗中一盘一问,知道了大概,将弟弟叫过来,训骂了一通。
柳嵩自然不敢说是霍怀勋的意思,晓得姐姐也不得拿自己怎样,抹干净脸上口水,嘀咕:“不是姐姐允许将欢姨娘借给香铺么,我不过是请了出去用用,半日不到就叫良哥送回来了。”
柳倩娥回头坐了藤椅上,手捏瓷盅,直接戳破他心思:“我那弟媳没来,你馋女人,我支银子给你去找粉头都好,怎么非就是看上家里这个动不得的?”
柳嵩呵呵一笑:“还不是她生得好看。我也是想着姐夫哥如今卧床,姐姐家务事也不少,才没将这小事告诉姐姐。”
柳倩娥啐道:“小事?你倒是说得牙齿不碰舌头,轻巧得很!如今跟我对着干的人都晓得了,惟独我蒙在鼓里,这可好,那贱人准备去告状了,你当她不晓得你两年在店铺里私饱中囊,亏空营款的事?只没个机会借题发挥罢了!老爷本就一碗水端不平,要是晓得这事儿,那新人被几棍子打死不要紧,我都怕是得被你连累得连家务都管不得了,你到时被你姐夫赶出宅子,可别指望我给你送救济!他郑济安再懦弱再好说话,毕竟还是这郑家的一家之主,哪能叫你个外男随意帮他做主安排,谋他家的女人。”
这样一说,柳嵩也慌了,忙拉了姐姐取经:“那怎么办才好?”
柳倩娥白一眼弟弟:“你现在一路小跑,赶紧去灶房,找厨子拿一把磨得锋利的快刀!”
柳嵩疑惑:“拿刀?干什么?”
柳倩娥剜他一眼:“杀了高翠翠,杀了这屋子和香铺里晓得你将那欢姨娘运出去的人,岂不就好了!”
柳嵩挠头,苦笑:“这关口,姐姐怎么还有心跟弟弟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