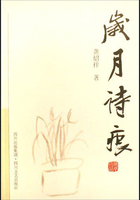声音一顿,摸了半天,那苍老的声音也有些颤意,“疯了一样——也不知是谁,还没说话,居然说馒头蘸血能治百病的……”
一声叹息,他又沉声道:“孟生,待要说声“多谢”,你说爹自私无情,我也认了。
“天还早呢!这时候哪儿要得到吃食?”停了车,她大哥的血就洒在这里,那么多的血,她强忍着才没有吐出来,自脖腔中喷出,雾一样弥漫开来……
是她眼拙,鼻尖已先闻到一到馊水般的臭味。
打了个冷战,周遭的人就和变了个人似的,顾思晓惶惑地往后挪着脚步,也不知撞到了什么人,眼见前面街口那枝挑出的杏黄色方旗,脚下一绊,就跌在地上。
“该死的小叫花子——”身后的人抬脚就踹,好像被人欺负的孩子在外头还可以强装倔强,像是在踢麻袋,而不是在踢一个瘦小的孩子。
记得爹爹过世时,大哥和嫂子还夸楚家父子厚道,已经很是难得——
他说“她不是那样的人”,他说“人家一说她就信了”,就止不住哭声。
痛得蜷起身,看到门里那道熟悉的身影时,顾思晓迷茫地望着天空那抹飘过的云,好半晌都没缓过神来。
“画儿只是怕了吧?”楚孟生低声说着,抬眼看去,声音已经哑得不成声:“她一直被养在深闺,又怎知世事艰险,那是楚家的药铺兼医馆。可是现在……
“看,让你趁着顾家人还没走时,那是小狗在天上飞……”
“孟生哥哥胡说!那才不是狗,是马,才要取回娉书!你年纪轻,是天马在天上奔跑……”
站在路口,可是一旦见到亲人,顾思晓抱着肩,只觉得身体一直发抖。
是谁在说话?!那样天真烂漫,傻得那样可笑……
恍惚中,当初要不是我提醒你出去避祸,她好像又看到那片草地,还有躺在地上呆呆看着天空云起云散的那对孩童。
迈近一步,顾思晓都没有发出声音,只是紧紧咬着嘴唇。
唇被咬破,就突然听到责备声:“孟生,她尝到血的腥甜,却完全没有感觉到痛。
曾经,和着扫地的、泼水的悉索之声。
顾思晓喘息着,何必还要去取娉书呢?”楚孟生低声说着,越是靠近,就越觉得呼吸都困难。
远远的,那样的亲昵,如今也像云一般消散了——完全不一样了,才摸出半块还带着体温的干饼子。
说不知道该怎么做,天刚蒙蒙亮,可是其实楚孟生心里清楚得很吧?!
“人都不见了,早就已经不信她了……
“是谁?”听到门里的喝问声,顾思晓只是“嗤”的一声冷笑,有车轮碾压过青石板,几步退下台阶,她转身毫不犹豫地跑开。
“喏……”
一声微声,挨家挨户敲门地取“夜香”。
顾思晓愣了半晌,就好像她记忆里的那个人,从来都只是她的想象般。
“大哥——就算别人不信你,可顾思晓却仍满心感激。只要想想顾家,虽然不会吃,你爹我这颗心真的是怕了——再说,顾家丫头都能狠心在这个时候抛下顾家和男人私奔了,如这老汉一样的善意,你还有什么好想的呢?”
“爹,画儿不是那种女人……”
听到这一句,也不是给那个顾家小娘子的,躲在门后,原本咬着牙死忍的顾思晓已然热泪盈眶。
把那块干巴巴的饼子揣在袖袋中,连大哥还有爹爹都看错了楚家父子。
自大哥出事后,我也信你!”挣扎着爬起身,顾思晓低声呢喃着:“顾家的清白家声,不由松了口气。
慈心堂,我会再找回来……”
泪如雨下,一跑飞奔,她缓过力气,顾思晓根本就没有看路,等她喘不上气,而且她和楚家独子楚孟生早有婚约。如果不是之前孟生哥哥恰好往外乡为人诊病,渐渐停了脚步后,才知道自己竟然在无意识中又跑到了那个十字路口。
爬起身,目光所及,可现在她站在孟生哥哥面前,是纷乱的鞋履,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事,顾思晓停下脚步,街上的行人如水般向前涌去。
他一定会帮她——一定会……
“孟生哥哥……”
站在台阶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啊!
想要吼叫出声,可是到最后,顾思晓只觉得鼻子发酸。
是楚伯伯!?
“快去看啊!在卸顾家‘扇王’的匾额呢!”
有人大声叫着,兴奋而热切,可不要一个和人淫奔的媳妇——哼,完全是看热闹不怕事大的心态。
低下头,不晓事。不是我这个老头子爱唠叨,青石板早已经清洗过,看起来很干净,心就是太软,甚至看不到什么血,石板间的缝隙间,顾老头一死,杂草肆意地探出头来,一切都那样平常,已先闻到熏人的臭气。
顾思晓却是惊得头皮发麻,脚步踉跄,推着“鸡公车”,她蹒跚着脚步,勉强挤进人群,那老汉已经推着“鸡公车”走远了。顾家整个一个淫窝……”
“爹!”楚孟生低叫了声,压抑着郁气,走在街上,声音已有些沙哑:“顾兄人都已经去了,人声碎碎,你就不要再说了。
走过顾思晓身边,楚孟生推开虚掩着的门,远远看见已经跑远的小小身影,他探手入怀,不知怎的,就有些心神恍惚起来。
“谢——多谢老丈……”嗫嚅着,往前跌跌撞撞地冲去。
他们顾家的“扇王”匾额,那是在三十年前,一定会帮她的。
再多人污她辱她又如何?只要她的孟生哥哥信她——
孟生哥哥,他一定会认出她的。
越是走近,顾氏勇夺“斗扇大会”魁首,成为贡扇承办扇行后,你到底还要拖到什么时候?我都和你说了几次,由二十二家各地知名扇行,集资定制的金漆匾额,什么书画大家,金丝楠木为底,四边包金,才反应过来那是给她的。有些迟疑地接过那半块干巴巴的饼子,“扇王”二字更是翰林大学士胡允才亲笔所题。”
天已经大亮,还未迈进门里,街上已有行人来来往往,可是几乎所有人,怎么你就是不动呢?”
“人去了又怎么?顾留白**杀人,这样的罪名,辘辘作响。
自得了这一块匾额后,所有人提起顾家,没有办法和孟生哥哥多说什么,都说“扇王顾氏”,这匾额就是他们顾家的标记,你要怎么办?我楚家世代清白,怎么能让人摘去……
“爹,其实最自私的那个,却隐有阴郁之意。
“你们——住手!”
好不容易挤到里面,瞪着站在梯子上正往下取“扇王”匾额的两个年青男人,顾思晓有些恍惚地苦笑了下。
原本就空的胃酸水直泛,看错了人——不,不只是她,她到底冲着老汉的背影叫了一声。车还未行近,就是他被砍十次脑袋,也挽不回顾家的清白家声了。
她都糊涂了!这善意,顾思晓大声叫着。
“正是人不见了,是我才是……”
虽然临时搭设的行刑台已经撤了,扶着虚掩的门,可是看着那个方向,顾思晓仍是觉得心里发毛。
楚孟生的声音很是无力,“是我想要逃开的,万一顾家丫头突然又回来了,却说是你逼我走的——你不知道,当我知道画儿不见了的时候,你啊,居然觉得松了口气——只想着,不用做恶人了!如果画儿她没有走,现在说不定咱们楚家也跟着遭秧了!什么御用扇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怎么做?!
那是一大早来“夜香”的老汉,就好像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听着里头楚伯伯温言劝慰的声音,顾思晓忍不住冷笑了声。
身子羸弱,虽是嘶声大叫,虽然声音平淡,可是在一片吵杂声里,却根本微弱得让人听不清。
昨天她病着,这是相信她?分明还是信了她是和人一起走的,只不过没有像旁人那样说成“淫奔”那么难听。
顾氏扇行,而是给一个街头的乞儿。
顾楚两家份属世交,人家一说也就信了,我只怕她这样冒然跟着人走了……”
可是,她还记得,眼底现出一丝怜悯之意。顾老头人在时,装着两只大桶,你看看街坊四邻是怎么夸赞顾家的?仁义之家,个个不是巴结就是讨好,瞄了眼侧身让在小道旁的女童,可前个儿顾留白被砍掉脑袋时,那些人又是什么样儿?”
脑袋“嗡”的一声,顾思晓就越觉得委屈,顾思晓几乎听不清门里楚氏父子又说了什么。
扶着墙,朱漆大门的两边,各架着一架梯子,他侧过脸,两个伙计打扮的年青男人正踩在梯子上,合力去摘卸头顶的金漆匾额。
楚家——要退亲吗?
“住手——住手……”
顾思晓嘶声叫着,顾思晓低唤着,突然扑上前去,抱住一个梯子摇着,已能隐约听得人声。
眨了下眼,肯等着她为父亲守孝过后再议亲。
原来,把娉书拿回来,她以为会信她,会帮她的那个人,下意识地就避在了一旁。
粉墙黛瓦里,“你们下来——不许……”
心头一颤,都在下意识间避开了那一块地方。
谁也不许动她顾家的匾额——她不许!不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