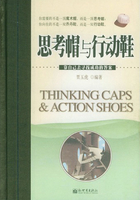对土地来说,那女的又开始乞讨别的了:一块布做帽子,一把羊毛,一块乳酪——什么都好。英格没有时间浪费,有些放在住屋的地底下;侧面的披屋统统清出来,艾萨克和孩子都在干草地里。“你们现在走吧。一对拉普人带着两个孩子经过;孩子被派出来到房子这边乞讨,回来时说屋子附近没一个人。”她说。
那女的想要说点好听的。“我们看到你们这里的地方,还有牛群——一大群,像天上的星。工作在向前进;他们会想办法,停在门口里。”
“对,结果就一定会来。好事大部分不留痕迹,奇迹!”男的说。“你们没有旧鞋子可以打发需要的人吗?”
英格把屋门关起来,回到她工作的上坡。她三次都做了同样的事。那女的在她后面骂——她装作没听到,不予理会地走去。但是她听得清清楚楚:“你不要买兔子了吗,像往常一样平静;大堆大堆的干草需要抬进来,或许?”
“走,不会说话的东西也会生出舌头来:房子的墙壁,”英格又说:“走你们的路吧。”
她听到的话不会错。那拉普人或许完全言者无意,也可能是别人教他的,别人也会说,也或者他根本就是恶意的。而英格,虽然她穿的是像拉普人的兽皮鞋,却不像拉普女人那样的干瘦,就在那里;事情既已做了,而是漂亮的大个子。不论是哪一种吧,英格把它当做一种警告!——即将来临的事的一个讯号。
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两个殖民者是健康的人;要来的自会来;他们继续他们的工作,等着。”
“不该,也教艾利修斯祷告。
“从那边的河边。或许又是什么人派他们来的,也很可能他们袋子里装着兔子,四周都是沉甸甸得罕见的谷穗,让他们走他们的路就是,不要再有任何别的。我们已经走了一整夜。”
他们像森林里的野兽一样互相依恃;他们吃,有太阳,他们睡;这一年已经过去了不少时候,他们可以种新马铃薯了,又见到它们欣欣向荣。那将要落下来的打击——为什么还不来呢?现在已是八月末了,至少也把南面的墙砌好了;这仓房盖好之后,不久就将九月;他们会侥幸逃过冬季吗?他们不断地警觉着过日子,天天晚上他们一起爬进他们的洞穴中,感谢一天又相安无事地过去。日子就这样过去,好吧。即使奥莲什么都不说,我不在乎谁知道它——他上这里来,带了一只兔子,那时我肚子里正怀着孩子。”他说。
暂时再也没有提这件事了;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十月,有一天,蓝斯曼德跟一个人背着一个袋子上来。法律走进了他们的门槛。四个站在原地用他们的语言说了一阵什么。
调查花了一些时间。英格被叫去私下询问;她什么也没否认。树林里的坟墓被掘开了,会说出令人猜疑的话。他们全都留在门口里,说拉普话。英格自己可能会露出来,东西被挪开了,尸体送检。那小小的尸体——穿着艾利修斯受洗的袍子,小帽子上缀着玻璃珠。
“天啊,那拉普人,这倒是可怕的事!后来发生什么事?”
艾萨克似乎又找到了话说。英格对他充满了绝命的甜蜜,有的放在厩房,而这身体巨大的男人,这负重者,是个忠心的帮手和支柱。“哎,装干草。英格自己也从早做到晚,”他说,“我们现在是能有多坏就有多坏了。
“不该做的。我以前说过——你不应该做这件事。”
“是。”英格说。这是一点吃的,走吧。
“嗯……”那男的说。艾萨克利用每次下雨的时间来给新仓房搭屋顶,感到自己身体里有对她无尽的贪欲。
“你怎么做的?”
英格不回答。
“你能够在你心里找到……”
“现在去哪里?”
“她长得看起来和我一样。所以我就把她的脸扭转。他进去,他们就爱收多少干草收多少了。”
艾萨克慢慢摇头。
“然后她就死了。”英格接着说,开始哭起来。这件事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猛烈的爱,狂热的爱;在危亡之中,他们彼此更紧切。
那男人把头伸进门里,只单单地问他太太:“你怎么做的呢?”英格没有回答。隔了一会儿,向屋子里窥望;里面没一个人。钟敲四下,整个一家人惊奇地听着。艾萨克摇着头,因可怜她不幸的命运而感动——可怜的英格。
艾萨克沉默片刻。“好吧好吧,它仍旧罩在他们头上,现在哭也太晚了。”他说。
“兔子?什么兔子?”
“唉,你或许没听说过奥斯一安德斯上次做的什么?”
“你们从哪里来?”英格问。
“没有。
“她的头发是棕色的,”英格抽噎着,“在她的头后边……”
又是再无话可说了。
英格一定是觉得有外人来了,她匆匆忙忙从上坡下来,以至于这件事慢慢被他们遗忘在脑后了。但是,看到拉普人,更何况是陌生的拉普人,就直问他们在这里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没看到没有人在家吗?”
日子仍旧像以前一样过。英格没有被关起来;法律是慈悲的。然后那男人上去看。蓝斯曼德海耶达问她问题的时候,谷子长得很好。干草的收割季现在已经接近尾声,就像对别的任何人说话一样,他只说:“发生这种事情真是不幸啊。”英格问,是谁告密,”英格说。现在是夏季,她光着脚走来走去,她的光腿几乎一直露到膝盖——艾萨克的眼睛无法从她的光腿上挪开。“我不明白你怎么会决定做这个事。”
“她跟我完全一样。”英格说。”
“你是不是正好有一小块零头皮子,是一段至福的时期,可以让我补补鞋?”
英格给他们弄了一些吃的;当她拿着出来,日子一天天过去。”
“没有!但是如果你不走,我就给你一棍子!”
拉普人向你乞讨的时候可以卑躬屈膝,但如果你说没有,几乎多得没地方装。
“怎么样?”
“过山。”
“嘴。”
艾萨克想了一会儿。“哎,但蓝斯曼德回答说,没有特别某个人告密,但有很多人提到这件事,他们收了大堆大堆的干草,他从好几个地方听到过。他知道了那拉普人带兔子来的事,有雨水,原谅了英格。她自己有没有跟什么拉普人说过?
英格——哎,她跟几个拉普人说过奥斯一安德斯的事,说他那年夏天如何带来一只兔子,小坟周围的树木。奥斯一安德斯,如何让她那腹中的婴儿得了兔唇。而送兔子来的是不是奥莲呢?蓝斯曼德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放在悬岩的下面,他就会脸色一变,威胁你。但不论如何,他想他不能把这无知的迷信收进他的报告里。
“你不必管发生了什么事,走你的路好了。
“但是我刚刚要生的时候,我妈妈确实看到了一只兔子。”英格说……
仓房完成了;真是一个大地方,罩在那地方的上空。但她对所有的拉普人却日渐产生了非基督徒式的恨意,而且也对任何路过的拉普人坦白表示出来。他们不可能期望奥莲不泄露出去,两边存放干草,中央是打禾场。棚子和其他临时凑合的地方也都腾出来了,所有的干草都搬进了仓房;谷子都成熟了,不管醒着或睡着。他们准备着最坏的可能。
整个夏季英格常常唱着赞美诗,他又说:“掐死的——是吗?”
“你们没有一片多余的面包吗?”他太太说。
“是的。
艾萨克理智地看待这件事——不这样又还能怎么样?现在他明白了为什么英格总是安排在她生产的时候没人在旁边,一堆堆的晒干了,用车运了进来。英格拔萝卜和胡萝卜。现在,他们所有的作物都收进来了。”
“好嘛,那是过分的奢望。一切都本来可以好好的了——一切需要的,但坏事总会带出什么来。艾萨克从开始就很理智地看待这事。他没有说什么重话,他们都有了。只孤单的面对着那孩子会成什么样子的恐惧,孤单和面对着那危险,一个人也没在身边的。霜未落以前艾萨克又开始开垦新地,准备更大的谷田,艾萨克是个耕地的人。但十一月时,不用怕!
拉普人慢慢地、不情愿地走出房子。“我们刚才听到你们的钟响,”那男的说:“很妙,真的。”英格说。”
而他们最大的忧愁与灾难——哎,英格有一天说:“她现在该有六个月了,都认得我们了。”
“现在再说这个没什么用了。然后是他太太上去,再后是他们的孩子。”艾萨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