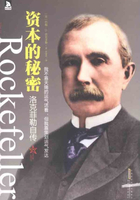但是,今天,火势并没有合作,跟克塞讲的一样。除非风再吹起来,否则人人都会去做清场工作。突击队员解开为便于直升机运输而绑起来的斧子、铁锹和锹背单刃手斧等工具上的胶带,并给链锯加上油——是大型的斯迪尔44及56型链锯,锯工们把链锯扛在身上,上面有垫子连在他们的吊钩上——然后最后一次大喝几口水。山脊上很热,而到了山谷底部以后,立刻就变得跟烤炉一样了,那里有火在燃烧,而风又吹不到。他们一个接一个很勉强地朝下坡路走去:海伦纳突击队的人戴着明亮的粉红色硬头盔;之后是平头突击队;来自蒙大拿北部地区的齐夫山突击队,他们全都是黑脚族人。克塞朝我打手势,我们也跟着朝下坡路出发了,走的是两天前由二类消防员开辟的一条隔离带。
隔离带看上去并不是那么吓人:就是围着山火挖到矿质土的一长条地面。有不同类型的隔离带,我们走上来的这条隔离带称为直达线,或者叫热作业线。这样的线有几英尺宽,就在火场的边上开挖出来。“一只脚踏在炭黑上”,他们是这么描述的。如果燃烧前沿真正冒起火来,突击队员会在几英尺外或几百码外开挖间接线。一般来说,这两条线之间的区域会用称为引信的火把烧掉。所谓的燃尽就是用光这条线与燃烧前沿之间所有的燃料,从而有效地制造出一条隔离带,宽达数百码。燃尽与逆燃不一样,它是有意消除火场发展路径上大片的可燃物质。一般来说,这是阻止树冠火的惟一办法,因为树冠火燃烧的余烬会随风飘到几英里外的地方。当然,逆燃本身时常也造成很大麻烦。突击队的队长一般可决定采取燃尽措施,但逆燃一般只能由事件指挥组来决定。
手线与猫头线不一样,猫头线是用推土机推出来的,所有手线都是用下面的方法制造出来的。首先,由线路侦察员先头用红带子标出路径,他可以利用所有的东西:溪流、岩石露头、山脊线等,只要是不能燃烧的东西都可以。之后跟上锯工,把沿途所有的东西都锯断,从齐漆深的山艾树到150英尺高的大树。每个锯工都分配有一个助手,助手将树枝拖到路边,将隔离带上的树枝清理干净。之后是突击队其余的人,他们利用耙子、铁锹、锹背单刃手斧,甚至自己的双手把落叶清理干净,把所有越过隔离带的灌木或树根挖出来。没有人动过的森林或山脉从这条线的起始处进入,无燃料的一长条路径从另外一头冒出来。这条线应该能够阻住火势,尽管表面上看上去不怎么样,在如此庞大的地理规模中,这条线又窄小又不起眼,但它往往就真能起作用。
隔离带的开辟和测量是以称为“测链”的66英尺线段来计量的,这个计量单位可追溯至土地丈量学的最初时期。一英里共有80个测链,突击队员应该能够在1小时内开辟20个测链,也就是1/4英里隔离带。如果是紧急情况,突击队还应该能够全天保持这样的速度,整晚上借助头灯保持这个速度,有时甚至第二天还能保持这样的速度。非正式的纪录是67小时,由加利福尼亚一个突击队的队长创下的,他同时还创下了30天没有冲澡的纪录。从技术上说,这两种行为都是违反机构政策的。
这条隔离带可以临时用作通往陡坡的很好的一条小路,我跟在克塞的身后朝坡下的突击队员走去。1,500英尺下面就是那条河。克塞作为一名安全官员的工作,就是全天到处走动,看别人工作,跟他们谈潜在的危险。如果火势蔓延起来,他们有安全区可以逃避吗?每个突击队是否布置了安全岗哨?是不是人人都穿着防火衬衣?大部分火都是慢慢烧的,在更多情况下,扑火像在园子里锄草而不像作战,但是,当火燃烧起来的时候,移动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如果人们没有做好准备,那是一定会死人的。
“1985年的巴特大火,有72个人没有及时跑出火场。”弗莱德·富勒说,他是各种内务操作组的成员之一。(“我们当中有一层层的人死在这里。”他承认。)他身材瘦长,说话慢条斯理,他陪我和克塞先四处转一会儿。“他们在自己的避火篷里躲了一个半小时。不过他们活下来了,哪怕没有带避火篷的那些履带拖拉机手也活了下来。他们只好爬到机器底下去。但他们活下来了。”
履带拖拉机手是火场死亡率最高的工种,因为他们一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机器,直到太晚为止。在巴特大火中,是别的消防队员强行将他们从机器里拖出来的。烧伤也被认为是灾难,哪怕没有人烧死,活下来的人必须在24小时内接受心理咨询。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那都是可怕的经历,在那么近的距离内,一场火风暴会发出喷气机起飞时一样大的轰鸣声,许多困在避火篷里的人都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他们能够做的一切就是等待,尽力不让对流风把避火篷从自己的后背撕扯走。
包勃·鲁特是伤害损失组的一位年轻领班,在我们的下坡工作,他的话说得比较生硬:“如果有人必须要躲进避火篷,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人倒霉。我是说真的。”鲁特千了7年的消防工作,从18岁就开始。他是科罗拉多州立森林学校的学生,也是当地治安官的搜查及救援队的成员。他的伤害损失组会在严重火灾时提前组成,一天24小时随时待命出发,一个小时内就可以上路奔赴火场。鲁特一头草黄色的直发,身上有晒斑,戴一幅暗色的博雷冰川眼镜。他意识到我跟任何人一样是很好的一个吃午餐的借口,因此就坐了下来,从他的火场背包中取出一个棕色纸袋。
“现在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称为城市界面的一种东西,也就是说那些建在森林里的房子,”他说,“如果事情涉及到抢救结构而不光是树木的问题,他们更愿意冒险。从基本上来说,如果你在保持一个结构而火又朝你的方向扑来,那你不会撤退。你会留在原处不动,想努力从两边把火挡住。”
鲁特吃得有板有眼,很是讲究方法,明显并不急着马上恢复清场的工作。他的袋装午餐是直升机运来的,看上去减档到了小学男生的胃口:大腊肠三明治、蜜饯、饼干,更多的蜜饯,还有几只苹果。我们谈话的时候,一只克罗曼气艇低低地飞过我们的头顶,慢慢降落在直升机临时停机坪上。挂在下面摇摇晃晃的是一个小汽车大小的囊状水袋,称为布利维特。飞艇操作员从侧窗朝下看,小心翼翼地把布利维特落在山脊顶上,之后把拴住它的系绳松开。鲁特的眼睛没有离开它。
“有时候,这些袋子会穿孔,里面装的水会流下山去。”他解释说。我意识到,我们事实上正好就在一吨半水下面。他吃着三明治,最后看了一眼那个大水袋。
“今天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事情,但昨天夜里很有趣。我们就在这个坡底——你永远也不想站在火的上头——岩石和树木都烧松动了,在我们身边滚滚而过。都可以听到石头滚来的声音。有人喊‘石头’之后一点声音也没有了,人们都想看石头在哪里,好让开一条道来。圆木会滚到谷底,把山坡点燃,火苗会跟在我们身后扑来。一晚上很快就过去了。”
按照鲁特的说法,在西部各地,火情要多危险就有多危险。燃料越是干燥,火烧得越是旺,传播的速度也越是快。燃料水分含量通常应该在15%到20%,现在都只有个位数的百分比。相对湿度低,空气不稳定(风)都会使问题复杂化。火一般是慢速移动的,一个小时只能移动几个测链。但有时候,火势可能在山坡上爆发,或者越过峡谷。我们四周的山峰已经因为7年的干旱而炙烤着,它们很容易跟过去一样产生这样的行为。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干得这么厉害的天气,”鲁特说,指着我们周围一些黄黄的旱雀麦,“这些东西,只需要一丁点火星就点着了。昨天夜里,每一块火星子都在发挥作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燃料往往比你在木材店里看到的木材还要干燥。现在,只要闪电击打在千小时燃料上,立即便会引起大火。这在以前是没有听说过的。”
千小时燃料是指3到8英寸粗的木材。“千小时”的意思是说,如果这种燃料全部浸上水的话,需要1,000小时才能通过蒸发而失去其63%的重量。反过来,如果非常干燥,它将需要1,000小时才能使其在水分中浸泡出63%的重量。之所以把63%当作一个标准,是因为它处在两个点之间——在78%的上面,又在58%的下面——在这个位置,水分吸收或者蒸发是以可预测的线性方式发生的。但是,在这个中间区域内,木材获取或损失水分的方式非常复杂,而63%正处在这种非线性范围的数学中点。草和树枝几乎立即干燥或浸满水,属于一小时燃料。山艾树和其他小型生长物被认为是十小时或百小时燃料。千小时及万小时燃料包括别的一切东西,大到直径6英尺的西黄松。千小时燃料跟一小时燃料一样干燥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但它们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形。人人都很担心。有一位突击队员说:“再没有什么小型山火了。”任何能够点燃的东西,现在都倾向于产生爆发性的发展了。
燃料水分含量可以通过现场测试或基于国家气象服务局的信息而进行的推断来确定。燃料水分含量可进行因子分解而成为一个指数,包括气候条件、风速、燃料负荷(区域内所有燃料每英亩的总烘干重)和干旱情况。信息由国家火灾评级系统进行处理,这个机构确定全国气象区的火灾风险,预测诸如火灾密度、雷击的可能性以及称为起燃构成条件的项目,如落入干燥燃料的单根燃烧木头引发需要采取行动的火灾的可能性等。另外,小到1/4英亩的区域里面准确和相当精确的“火场”预报也可以通过国家气候服务局获得。火场预报也许声称,博伊西国家森林内的某一处峡谷的温度范围将在华氏28度至80度之间,湿度在12%至14%之间,风速将达到每小时10英里。突击小组布置在高风险情境中时,这样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个范围的常量一端,是总体的干旱状态。1988年,全国经历了一个酷热的炎夏:密西西比河上的泊船都搁浅了,新泽西州的铁轨都变了形。干旱最终导致黄石国家公园的大火。从6月下旬到11月上旬,大火总共烧掉西部120万英亩的森林,其中一半是在黄石国家公园以内。8月20日这一天是一个黑色的星期六,仅在这一天内,每小时70英里的狂风在一共165,000英亩的范围内煽起300英尺高的大火。虽然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在当年冬季恢复正常,但是,西部各州的干旱却从来都没有真正结束。因干旱而死亡的树木数以千计。干雷雨继续引燃大火。燃料水分含量下降至2%和3%。帕尔默干旱指数——某种测量既定地区水获取和水损失的水统计报告制度——指示,整个西部正在进入自19世纪70年代所保存的纪录以来最干燥的时期。在帕尔默干旱指数上,0是正常,+4是极度的洪涝,-4是极度的干旱。1988年夏天,黄石公园登记的指数为-5.8。在弗里克溪大火中,国家气象服务局宣布博伊西地区已经达到-6.5。
在这个地方,那可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这个数字可以把人吓晕。在另一场大火中,我把这个数字重复给一位部门负责人听,他猛地一下缩回头去,好像被人扇了一巴掌。
鲁特吃完了最后的糖块,我们两个都站了起来。我谢谢他的谈话。直升机吊着邦比桶不停地在头顶轰鸣,各突击组在陡峭的山坡上扑腾出一缕缕的灰尘。8月的太阳高挂在天上,克塞在我身后慢慢爬坡,跟在我后面赶,最后他终于爬过来了,我们沿着等高线翻过了山脊,然后直奔西边,齐夫山和平头突击队正在砍倒死树,把我们的火场抬高到河流上面。无论是否有起火危险,死树都得要砍倒,有些死树完全中空,一推就倒。死树倒下的时候,不会发出很大的声音,有时候正好就有人就站在下面。在1988年的雷德奔奇大火中,一名突击队员在公路边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就被一棵死树压死。“死亡从天而降。”一名突击队员警告说,他解释为什么自己走路的时候总是把头仰起来。
我们停下来跟平头突击组的人交谈一会儿,其中两名队员曾出现在亚里桑那州著名的杜克大火的火场上,当时,一个罪犯组在自己的避火篷里被烧死了。梅利莎·瓦格纳斜躺在旱雀麦地上吃午餐,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记得在无线电里听到罪犯们被烧死时的尖叫声。其中一名幸存者太早跑出避火篷,结果从火苗中冲出来,头发在冒烟,全身47%的皮肤被烧伤。另外6个人烧死了。瓦格纳之所以继续做消防工作,因为她需要一笔钱支付法学院的费用。
我和克塞继续朝齐夫山小组走去,可以看见他们在远处的一个山脊上,浓烟从他们身后冒出来,还有直升机在他们头顶盘旋。我们在尘土中跋涉,天热得像烤炉,走到一半的时候,克塞突然向后猛地一跳,差点将我撞倒。在隔离带的中央,一条极大的响尾蛇盘在一块岩石上。它没有动,也没有发出响尾声。事实上,它已经没有头了。20分钟后,我们到达黑脚族突击组。他们坐在一棵小西黄松的树阴里吃午餐。在下面的山坡上,一棵孤零零的树正在燃烧。
“这么说,大家都明白那边那条响尾蛇是怎么回事吧?”克塞问。
没有人出声。小组里面的每个人都扭头看别处。
“响尾蛇?”最后,突击组的组长格伦·斯迪尔斯摩金问道。
“王八蛋。”克塞咕哝一声,一边摇着头,一边却露出微笑。
我们在树阴里坐下来,一边喝水一边看周围的情景。其中一名队员从口袋里摸出一柄黑曜岩箭头。他说是在巴贝尔平地的直升机临降落点发现的。斯迪尔斯摩金欠过身子来看一看。“我们是相当不友好的一个民族,”他承认,四顾看看他的队员们,“我们把约瑟夫酋长赶跑了,我们是最后一批安居下来的人。但现在,我们成为相当出色的消防队员。我父亲是灭火队的头,我本想去上飞行学校的,但是,灭火却吸引了我。我去过阿拉斯加、弗罗里达,都是带薪度假——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工作——哪里都去。在弗罗里达的安全事务介绍材料中,他们要我们小心鳄鱼。”
在下坡道上,两位锯工——他们管锯工叫锯木狗——正在放枯树。斯迪尔锯的声音传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已经是微弱的哀鸣声。一棵孤零零的西黄松在我们身后一英里的地方懒洋洋地燃烧着,在我们身下的峡谷底部,河水闪闪发光。这也许跟隔离带上的情形差不多安详,突击队员看来并不特别急于破坏当前这一刻时光。我仰头靠后,尽力不再希望这场大火弄出更大的事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