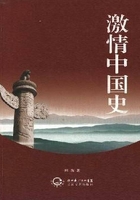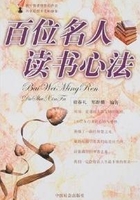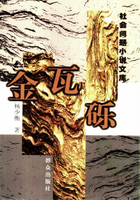我从几位觉得无聊的森林服务处守林人员身边逃走了,从21号公路上开走,到了山区。
弗里克溪是数百条切开博伊西国家森林陡峭和干燥山地的小溪之一。这一片山地的大部分是草和岩石及三齿蒿,北坡上和排水流域是厚重的西黄松。弗里克溪倾入博伊西河的诺斯福克,之后很快汇合米多福克,并继续向前,流入阿罗诺克水库和拉基皮克水库。整个西部处在连续7年的干旱中,而且是自187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干旱,因此,两个水库都严重缺水。阿罗诺克水库已经变成了一条泥泞的小河,人都差不多可以跨过去。
经过20英里颠簸,公路在博伊西的诺斯福克附近平整起来。这里水量充足,或者看起来是如此,河水湍急,沿岸有很大的西黄松,彼此隔得很开。救火营在很大的一片草地上,叫巴贝尔平地,跟诺斯福克是齐平的。数以百计明亮的尼龙帐篷扎在变成黄色的草地上。山脊线上,一架直升机发出低沉的声音,后面拖着一个装有阻燃剂的桶。水车来回开动,把灰尘压下去。快车组的人员来来往往,成一路纵队,或者在树阴里睡觉,或者在打磨自己的工具。有些人一身泥污,另外一些人好像刚到。他们都穿着跟我身上一样的绿色和黄色诺梅克斯服,还有鞋帮上带挂耳的大皮靴。
我把车停在卡车和水罐车之间,之后去找信息处。公共事务处的人知道我要来,因此有人指着一个大个子要我去找他,此人声音低沉,名叫弗兰克·卡罗尔。“如果你想去隔离带,得换上一双皮靴,”他告诉我说,“你需要水瓶,你需要食物,你需要手套。晚饭后我帮你准备好。你随便找个地方搭帐篷吧。他们早晨5点左右就出发了,你要做好准备,到那时就应该已经吃好早餐准备动身了。”
我谢谢他,之后就去做准备了。在我周围,个子高大的、身体瘦削的男人和几个女人各在忙自己的事情。我把自己的帐篷支在一个作为指挥部的小屋后面的高草里,之后四处走动,朝配餐的帐篷走去。在帐篷的后面,是一辆长长的卡车,已经改装成一个厨房。突击组的人排队经过这个厨房,从窗户后面那位年轻妇女那里端走几盘子食物,之后坐在帆布陆军帐篷下的折叠餐桌旁边就餐。那位妇女很漂亮,皮带上扎着一把鞘刀。我努力装出自己就属于这里的样子,她就在我的盘子里堆满了牛排和胡萝卜,还有土豆泥和色拉以及两片白面包。
我在边角上一个餐桌旁边一个人坐下来,看着那些人来来往往,他们大声谈话,吃得很快。大部分消防队员都是年轻的白人,他们强壮有力,都没有刮脸。他们当中还有几位妇女,但是,这里的妇女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并没有特别待遇,至少我看是这样的。除开一些男子以某种形式献殷勤以外,我觉得不会有人歧视她们的。但是,他们没有献殷勤。大家好像都太累了,也太饿了,根本没有时间去注意异性。(结果证明这根本就不是实情。)另外,人人都穿袋子一样的裤子,脸上都脏兮兮的,也很难看出到底谁是谁。
印第安人和拉丁人一般都有他们自己的救火人员。这里面反映出的人口统计学上的问题多过其他任何领域:蒙大拿州布朗宁有20人,他们多半是黑脚族而不是白人;从斯奈克河谷的农场员工中抽调的20名男子多半是拉丁人而不是印第安人。配餐的那个女人告诉我说,只有印第安员工才能真正把一卡车食物弄干净。“只要没有钉牢的东西,他们都吃。”她说。罪犯吃甜食和辛辣食品,因为他们在监狱里吃不到这种食物。白人突击组是最有健康意识的:他们吃很多水果和蔬菜,有些人甚至都不沾肉。
这是很难想像的,因为政府的食品合同是根据有多少蛋白质一一换句话说就是有多少肉——来确定的,而蛋白质的量又是根据每餐为每人提供多少来计划的。早餐每人4盎司,午餐7盎司,晚餐10到16盎司。别的一切,包括蔬菜、水果和谷类,都被认为是一种调味品,根本都没有包括在这个方程式里面。这比以前强多了。在灭火的黑暗时代——没有女消防员,没有洗澡的地方,没有诺梅克斯防火服——消防队员完全是靠火腿生存的。火腿炒鸡蛋、火腿三明治、煮火腿。配餐卡车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大的肉库,里面挂着火腿,也许还有些“神奇”面包。远在那些日子里,突击队员们穿的T恤衫上都写着这样的字:“森林一着火,猪死一大群。”
晚餐过后,我也列席参加计划会。会议在一棵西黄松下进行,就在没有铺水泥的停车场上。整个内务操作组都在那里,这些人都不脏,也不穿诺梅克斯服,因此容易认出来。他们是一起参加训练的,在弗里克溪大火中,他们是作为一个称作事件命令系统的网络的可替换部件使用的。那个系统基于这么一个想法:为某一个工种而接受训练的人,比如后勤负责人、信息官员、直升机基地管理人等,可以在任何情形下为任何一个机构做同样的工作。内务操作组的人来自十多个不同的政府机构,而且是从全国各地抽调来的。你也许会发现来自佐治亚州的一名紧急事件指挥官,来自科罗拉多州的一名空中作业分部的指挥人员,或者来自别的某个城市的一名安全官员。全国共有17个一类内务操作组,它们主要用于灭火,但也有时在别的灾难中发挥有效作用:阿拉斯加的油田井喷,弗罗里达的飓风,墨西哥的地震。例如,内务操作组被派往处理法尔戴的井喷,整个系统运转极其灵活,结果艾克森石油公司和美国军方都复制了他们的运作方式。事实上,灭火营加上内务操作组可以做到每提供一名后勤支持人员就投入两名灭火人员到火场,这个比例比军方的效率高出近20倍。
天黑以后,500名消防队员睡觉了,我也去睡觉。惟一的声音就是发电机持续不断的嗡嗡声。计划会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坏消息:火势发展得太快了。30英亩的飞火是在南线的轻燃料上开始的,但3名消防队员已经将火扑灭。7名二类灭火人员——他们的经验不如突击队员丰富,一般也只是用于做扫尾工作——把隔离带一路逼到河边,比预期的远得多。风也快停了,除非再次刮起来,否则,大火将在几天内得到控制。
灭火营永远都没有一个安静的时候。我整晚上都听到有人走动的声音。他们走过附近,整理设备、咳嗽、吐痰。到早晨4点左右,声音开始连续不断了,因此手表闹钟还没有闹响我就起床了。天还没有亮,营地已经有人影在浮动了,时不时还会出现头灯的晃动。灭火人员在捆扎自己的绳具,朝配餐厅那边移动,围在间隔一定距离排在地上的立式煤油加热炉旁边。天很冷,也许只有华氏二十几度。我从睡袋里爬起来,穿上了好几件毛衣,穿上了皮靴——不知什么原因,在直升机里,我非得穿上皮靴不可——然后朝帐篷亮灯处走去。
派给我的那个人叫比尔·克塞,是二类安全官员,来自博伊西地区。他身体强壮,目光清晰,年近50,他指挥当地的土地管理局,也有资格指挥二类内务操作组。(二类小组处理较小的火灾,但操作的原理是一样的。)他说,过去32年以来,他一直在打麇鹿,一共打到30只。他父亲跟他一起打,现在还扛得动50磅重的麋鹿肉,都71岁了。克塞属于半边黑脚族,他有笔直的灰头发和褐色的眼睛,还有一张漂亮和宽阔的脸。
“我们派来的人太多了,因为火势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发展。”我们坐在直升机基地他的卡车里的时候,他承认说。
“你们原来预计火势会怎么发展的?”我问。
“嗯。”他在小心选择自己的用词,“这些人也不想让森林一直烧下去,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希望有一个多产的好夏季。他们喜欢在一个火场工作两到三个星期,之后再移到另一个火场。从这个角度说,火情很快结束对他们来说是让人失望的。”
我们在等候飞往隔离带的直升机,卡车里面的取暖器也烧得正起劲。在开阔地里,一些男子在检查直升机,填写飞行报告单。火灾的头几天一般总是组织不好的,经常会发展到混乱的程度,克塞说。之后就会好一些。克塞利用等候的时间给我讲了更多灭火的事情,不是从灭火现场,而是从指挥的角度。
“博伊西火灾协调中心只是一个后勤中心,满足火场提出的各种需求。”他说,“假如X单元出现火情,如果火情没有逃出最初的攻击,博伊西火灾协调中心一般不会介入。如果没有扑灭,那么,地区协调中心会牵扯进来。如果地区协调中心没有足够多的资源扑灭大火,博伊西协火灾协调中心就会介入。今年夏天,我们已经扑灭好几场山火,而这次是博伊西火灾协调中心第一次介入的大火。”
他说,最初的攻击有许多种形式。跳伞灭火者是最初的攻击。从直升机上顺绳索爬下来的人是第一波攻击。突击队员可能是第一波攻击,也可能是后续攻击。空中打击——飞机和直升机上撒下来的阻燃剂——也可能是第一波打击,或者是后续打击。初期打击的意思是说,早早给予火势以有力打击,这样可以避免大规模调动人马。如果攻击人员无法扑灭,则会纠集内务操作小组来灭火。真正的大火会把全国各地的突击队员调集到火场。全国共有60个突击灭火队。如果这还不够,或者如果别处也有这样的需求,则会征用二类灭火员,这些灭火员受过灭火训练,但经常为森林服务处和土地管理局做其他工作。再下面就是一些罪犯灭火员了,还有斯奈克河谷的一些劳工,警笛拉响后,他们会在市中心的广场上集中。还有就是临时组了。临时组的人一般是指只要有一双结实的鞋,身体健康到能通过训练的人。火场上如果有临时组的人,那就是相当严重的火灾了。弗里克溪大火的火场上没有临时组的人。
大约一个小时后,直升机准备好了。是一种贝尔喷气巡航机,这架飞机是从亚里桑那州一个私人承包商那里租来的,每小时租金2,000美元。巨大的克拉曼伐木业飞艇是这个价格的3倍,底下可以挂上两万磅重的阻燃剂桶。一名机组乘务员给我们念了安全注意事项,之后问我们各自带上用具后重量多少。答案输入了飞行记录表,以便计算一旦我们脱离地面效应后直升机可以装载多少。直升机到达一定高度后,因机翼所产生的下降气流再没有可以推动的地面基础了,因此能够负载的物品就会少一些。如果把高度、气温和相对湿度考虑在内,你会得到密度高度的数字,这个数字确定一架直升机可以装载多少。阻燃剂桶,也称为“邦比桶”或者“西姆斯桶”,这取决于不同的制造厂商,可以通过捆扎松紧来改变容器的大小,用以补偿每天有所变化的密度高度。
机组乘务员又一次做说明:进出直升机时头要低下来。永远不要把直升机停在上坡道上。永远不要到直升机的后端去。永远不要走到驾驶员看不见你的地方去。如果违反上述规定,机组人员有权用武力强迫你照章执行。
“我会抓住你。”他说。
这是本架直升机今天第一趟飞行,因此,我们登机的时候,机翼并没有转动。手套戴好了,头盔戴好了,护目镜也戴好了,袖子也放下来了。机组安全员确认我们大家都系上了安全带之后关上门,机翼开始转动起来。
“顺便问一句,为什么在直升机里不能穿胶底帆布鞋?”我朝克塞喊话。
“因为如果发生坠机,尼龙会熔化在你的皮肤上。”他也在喊话。
在我前面,副驾驶的头盔上写着这样的字:“防坠帽”。坠机的技术用语叫“硬着陆”。有一名驾驶员说,他认识的半数以上的飞行员都有过坠机经历。有些人摔死了,大部分却没有死。这些日子以来,许多直升机都设计了自动翻转功能,意思是说,如果引擎出现问题,飞机不会呼啸着直接坠落下去,而是会勉强模仿一种滑翔动作。博伊西国家森林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多岩和陡峭的山地,因此,很难想像这样的事情最后会是个什么结果。
贝尔巡航机升起来了,几分钟后,我们就把营地抛在身后了,我可以看见烟雾从远处的一个山脊上冒出来。并不是我想像的那种桔黄色的冲天大火,而是750英亩的一片浓烟,如果没有人加以处理,或者如果有风吹来,很可能就会燃烧起来,揭掉北面山坡上的重型木。直升机在巴贝尔平地上来回飞动,把阻燃剂撒下去。阻燃剂是铁锈色的,你可以看到山坡上有斑斑点点的阻燃剂。在我们身下,一只大克罗曼飞艇在一个深谷里下降,好把邦比桶伸进河水里。(突击队员们喜欢说,木桶里舀上去的鱼,扔到了山坡上还在跳。并没有人真正看到这样的情景,但是,这个故事广为流传,因此,渔业及山火服务处雇用一架直升机,看看驾驶员是否能有意抓住一条鱼。结果他们没有成功。)克塞大声说,克罗曼飞艇携带的药桶太大了,无法伸进巴贝尔平地上的阻燃剂药箱,因此只好用水了。它会在火场与河流之间全天来回飞动,突击队员用无线电操纵飞艇。驾驶员非常准确,可以让飞艇把水倒在具体某一棵树上。
我们沿着山脊低空飞行,之后升起来,倾斜转弯,再转圈,然后继续前进。我可以看见穿黄色衬衫的突击队员在我们下面,他们包裹在一片浓烟之中。火在谷底。多名突击队员在下坡道上,他们一条线排在爬行的黑线上,还有几个人刚刚降落在山脊上的直升机降落基地,正在等待下一步行动的命令。直升机再试一次,好不容易降落在一个山脊上,两边都是陡坡。突击队员在机翼的下降气流中蹲下身体,此时,临时降落场的那名穿绿色飞行服,戴有硬头盔和护目镜的工作人员却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平躺起来,好像有人要朝他射击一样。直升机降落下来,但机翼还在转动,那名工作人员蹲伏着急忙赶上前来,打开了我这一侧的门,拉着我的胳膊让我下来。之后,他转身去接克塞。有时候,人们会退到机尾的机翼处,或者朝上走到主机翼处,因此,总会有人在机坪上充当安全护送人员。我从草丛后面伸手抓住我的行李包,头转过去蹲下来。直升机在我们头上吭吭直响,再后就继续在火场附近运送物资。
太阳已经很热了,将会有很长的一天扫尾工作。突击队员们认为自己是精英,这些清场的活儿——搜寻烧过的火场,扑灭里面没有燃尽的余烬——在他们眼里就不怎么刺激了。也许任何人都不会觉得这样的活儿有刺激性,但是,二类人员却必须要做这样的工作,因为在这样的时候,突击队员多半已经坐飞机赶往别的火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