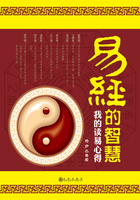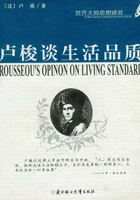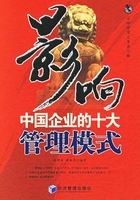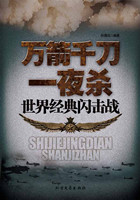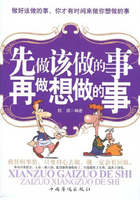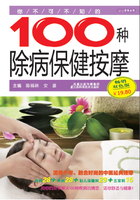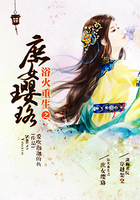“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海“运”即是海“动”,海动必有大风,大风起,鹏乃乘风飞去——这意指时机。即是时机成熟、条件充足才出而应世。“南冥”的“冥”,亦作“明”解,这喻示着人世的抱负。这一抱负一经开展,即充满着乐观的信念。由这里可以看出:庄子并非如一般人所说的悲观消极且怀遁世思想。相反,他满怀入世的雄心。只是要等时机——即是应有其条件,非如孔孟寄希望于贤君,而把自己搞得凄凄遑遑。现实世界的环境若和他的想法相离太远时,他便保留着自己的生活态度,而不愿丧失原则。
庄子借鲲鹏表达了一种大解放大自由的精神境界和独特的人生态度,即人的活动只有从自我为中心的局限性中超拔出来,摆脱功名利禄等俗物的束缚,才能使精神或灵魂感验到鲲鹏所置身的辽阔无比的世界,从而达到超越现实的“逍遥游”的境界。
当然,庄子清醒地认识到:体道的实践、高远的人生追求尽管精深,但并不能超然世外。实际上,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无论在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上,人都是不可能存在于“无何有之乡”“无人之野”的。如何在尘世中追求无限和自由?现实中就有一个如何处世的问题。庄子不主张弃世、逃世或隐世,而主张外游于世,虚而待物,与时俱化。“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惟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这与老子的避世思想是有很大不同的。
我们今天从功用的角度看,和顺于人,虚己游世,可免害保身,无疑是游世主要的价值所在。但是从更高的哲学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游世也是得道的精神境界的一种自由的表现。庄子游世态度基本表现为“游世不僻,与时俱化”,“虚己游世,以和为量”。“虚”与“化”是游世的本质内涵。而“惟道集虚”“万物皆化”。“虚”与“化”也正是“道”的存在特征。所以,“虚而能和”“化而不僻”,也就是得道者的处世态度。这种态度也是我们现代人心向往之的。
四、大隐与小隐
古时候有两个和尚,老师父带着一个小徒弟下山去化缘,师徒俩一边谈论着佛法一边悠然自得地行路。来到山脚下,一条不深不浅但水流湍急的河横在眼前,师徒俩正要过河,突然迎上来一个妙龄少女,那少女温柔而可怜地向老师父说:“师父你好,能否请您帮一个忙?”
老师父说:“施主请讲。”少女楚楚可怜地说:“我以前过这河时,河水都没这么急,今天河水汹涌,小女子眼看过不去,能否请师父背我过河?”老师父毫不迟疑地说:“来吧。”说完就把美少女背了起来,一步步走过了河。
过河后,少女千恩万谢地道别。师徒俩继续前行,走了很久以后,一直没有说话的小和尚突然问道:“师父,我们和尚是不能近女色的吧?”
老和尚点点说:“是啊。”
小和尚又问:“那你刚才怎么还去背那个女人呢?”
老和尚问到:“什么女人?”
小和尚:“就是你背她过河的那个?”
老和尚:“哦,你说的是那个人啊,我早已把她放下了,你还没有放下?”
不接近不证明心里不执著,接近也不能表示有所企图。这里关键要看“心”。老和尚虽然随性而为,但心却无半点执著。正所谓“物来则应,应不以心”。小和尚虽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遵守着清规戒律,但心却是一直没有放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说:“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隐”还是“不隐”,关键是看心。形隐仅是小隐,心隐才是大隐。淡薄名利,没必要非要跑到深山老林,处于闹市照样可以逍遥其外。真正的隐士,内心一片空灵,其“隐”的境界不会因为其身在何处而受到干扰。正如庄子所说:“圣人之心若镜,应而不藏。”当我们去照镜子的时候,镜子里自然会显现出我们的面容,当我们离开镜子时,镜子又恢复了其虚静的状态,不留一点痕迹。
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曾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山,看水仍然是水。也许,我们大部分人,仅仅停留在了最初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境界。而进一步修行,则需放下,进入“看山不山,看水不是水”的大境界。但此境界亦非至上境界,我们还要回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境界,这就需要把放下的东西再挑起来。一味地放,那是消沉逃避,不可取;只知取,又落入凡夫之俗情,也不可取。
还是懒融禅师说得好:“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高僧妙语,回味无穷,不可说,道不破。正所谓“不执著于一物,不执著于一念”。
五、心中无妓
“心中无妓”,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津津乐道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北宋时期两个著名的哲学家程颢、程颐身上。
两程夫子赴一士夫宴,有妓侑觞,伊川拂衣起,明道尽欢而罢。次日,伊川过明道斋中,愠犹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无妓;今日斋中无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谓不及。
程颢、程颐是兄弟俩,也是大哲学家。上面的故事是说,有一次,二人一起去赴朋友的宴会。程颐见席中有妓女陪酒,便拂袖而去,只有程颢留下来与人同饮,尽欢而散。次日,程颢到程颐书斋中去,程颐仍怒气未消,程颢笑到:“昨日本有,心上却无;今日本无,心上却有。”(意即:昨日本有妓女在,但我心上无妓女在;今日本无妓女在,但你心上却有妓女在。)看来只有“心中无妓”,才能“眼中无妓”了。
可见,程灏的境界明显高于程颐,这里已经有禅的味道了。而在禅宗中,也有这样的禅理故事。
据说,一个女尼问赵州和尚:“什么是佛法大意?”赵州随手掐了她一把。女尼问:“和尚还有这般举动?”赵州答道:“只因你还有这个身体在。”在日本,有一女尼参禅,在进净室前,其师父说:“放下着。”日语中“放下”有“内衣”之意,女尼误解成内衣,于是脱去全身衣服,一丝不挂。师父问:“还挂着什么?”师父知道,她还挂着一个女人的念头。
赵州物我两忘,而女尼却心中有我。“物我两忘”是一种深奥的禅理,它表明了对世界的一种态度。禅宗好讲对世界的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是说用逻辑思维法则来把握世界,见到了山,便贴上“山”的概念,见到了水,便贴上“水”的标签。自然山水不再是实在的美妙风景,而是一个概念,一个类别,一个抽象的逻辑学上的事物。第二种态度:“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是以非逻辑的第三只眼来看待世界。见到了山和水,却并不贴上“山”和“水”的标签,扫除名目的纠缠,丢掉语言的拐杖,以便接近它本来的面目。第三种态度:“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是以没有灰尘的明镜般的心来观照世界,见到了山和水,就根据山和水本来的面目去体验山和水。山水是生机勃勃的,人生也是生机勃勃的,物我两忘,物我一体,超越世俗,回归自然。
佛教的最终旨归是明心见性。而这一点,往往是通过修行和参悟来实现的。至于如何修行,如何参悟,佛教修持的途径分为“渐修”和“顿悟”两条。所谓“渐修”,就是在思想、言行、生活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按照佛法所要求的去修行,在“强迫”自己的过程中逐渐领悟佛法要旨,从而成就正果。正如神秀所说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所谓“顿悟”,则是指当头棒喝,当下开悟,反对按照既定的条条框框和繁文缛节去修行。正如六祖禅师慧能所说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后来,更是有人将禅宗的修行方法概括为四句话:“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并不是否定文字的存在价值,只是不拘泥于文字系统,不执著于文字表面意义。在禅宗看来,文字仅仅有引导性的方便作用,就好像渡河的筏一般。真理是要靠心去把握的,因此惠能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但惠能又强调不能摒弃文字,若完全排斥文字,则为着相、执空,亦谤佛经。“教外别传”,就是打破教的框框,别具一格相传,针对不同的对象,施以不同的方法。这就是禅宗的随机说法,忘我度人。“直指人心”,就是心印、心悟、心授。道由心悟,不假外求。正如慧能所说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见性成佛”,则是说,当你顿见真如本性,自身的潜在思维和潜在功能充分开发出来以后,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大智大觉的人。
六、饥来吃饭困来眠
禅宗是反对苦行的。禅宗经慧能改革后,打破了以往烦琐的教条陈规,强调顿悟,提倡当头棒喝、直指本性,甚至认为坐禅也“是病非禅”。那该怎样修行呢?有这样一个禅宗公案。
有一次,怀海禅师正与僧众务农。此时暮鼓敲响,一僧闻听鼓声旋即扛起镢头,大笑而返。怀海不禁赞叹说:“俊哉!此是观音入理之门。”那个僧人不滞于外物,不刻意修行,坦荡磊落,了无烦恼,“该吃饭时便吃饭”。可见生活中亦有禅机,生活琐事亦可入禅。这种自然洒脱的境界正是佛法的真谛。
《六祖坛经》中有六祖慧能所作《无相颂》。最后结尾处,有如下的四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意思是说,佛法是在世间的,离开了世间去谈佛法,就像到兔子的头上去找角一样,徒劳无功。简而言之,佛法就是活法,就是生活的方法,觉悟见性之后,无论待人处事,穿衣吃饭,忙里闲里,工作家庭,无一不是佛法,佛法在世间,在世间即是世间法,世间法即是活法,佛法就是活法。
由此看来,佛家的修行与道家的“得道”一样,都要扎根于人间。每一个有心向道的人,都不会厌弃这个世界,更不会逃避人群。因为,一个人要想成佛,除了具备聪明智慧之外,还要有广大的誓愿悲心去普渡众生。要以这两种“悲”和“智”交互运用,相辅相成,做到彻底、圆满的境地,这样才能成佛。所以佛教是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从修行一直到成佛,既没有“入世”,也没有“出世”,因为这些无不是在这个世间进行的。
七、平常心是道
名闻天下的赵州和尚的名言就是三个字:“吃茶去。”
有一个和尚来参拜赵州和尚,赵州和尚问他是第一次来还是第二次来,那个和尚说是第一次来,赵州和尚对他说:“吃茶去!”过了几天,又有一个和尚来参拜他,赵州和尚同样问他是第一次来还是第二次来,他说是第二次来,赵州和尚同样对他说:“吃茶去!”当时在他身边的和尚就问赵州,第一次来的你叫他吃茶去,我们可以理解,怎么第二次来的也叫他吃茶去呢?赵州和尚就叫着这个和尚的名字,说:“你也吃茶去!”
赵州连续三个“吃茶去”,阐述的正是禅宗的至上哲理——平常心是道。“吃茶去”这句话在禅林相当有名。禅宗认为佛在心内,不必外求,不用苦心修行,读许多佛经,只要静心省悟,即可顿悟成佛。曾在赣县龚公山结庵居住二十余年的马祖就有“平常心是道”的说法,指出人人都有成佛之根器——自我心性,只要心性借助外在的机缘显现开来,就可以立即成佛。佛家把这称为“见性成佛”。你只要看到自己的真性情,也就成佛了。所以,佛不在别处,就在你心中,何必到浩如烟海的佛经中去寻找?
赵州是马祖的徒孙,深知“佛法但平常,莫作奇特想”,三称“吃茶去”,正是巧借机缘,指点迷津,消除学人的妄想心、分别心,不论来没来过,相不相识,只要真心真意地以平常心去“吃茶”,就可进入“茶禅一味”的境界,一旦落入妄想心、分别心,就与本性相去甚远了。
吃茶去,平常心,平等对待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融会而为静心、平等、惜缘之道。“平常心是道”在战国里是武将的必要修行,《碧岩录》里讲“须是大死一番,却始得活”就是印证,如何直面残酷的战事和淋漓的鲜血,是古代“士”的课题,也是现代刀光剑影中成长起来的军队将领需要认真研习的功课。《平家物语》中的名句“祗园精舍之钟声,有诸行无常余韵”,说的正是生死轮回都是常事,平常待之,将生死放在眼底,反而可有活路。这样解释,在日本战国期间,上杉谦信和武田信玄都是一代名将,但上杉谦信之所以不会像武田信玄那样神经质,就是因为他有一颗看破生死的平常之心,从而能平心静气地看待一切。
以茶喻禅,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涉及。比如,在《红楼梦》中,妙玉就又有自己的一番品茶之道:“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喝茶的过程大抵如此,茶入杯中,刚开始的时候,叶未泡开,色味皆重;既而,色味柔和,清香自然;待到三杯水过,黄叶尽展,水味已现。一如人生旅途,第一杯如陌生的朋友的初识,容易感动,也容易在波光艳影中迷惑;第二杯如相知相望的故人,平和自然,清香如故;第三杯,已过三遍,感觉出茶的平淡水味。你不妨一并倒掉,去饮一杯干净的水。这正印证了“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老话。如果泡茶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茶叶初泡时叶瓣微展,纷纷挤于水面,争奇斗艳;稍过一会,茶叶便会逐一悠悠地落入杯底,正如一个个逐渐成长的生命,由原来的争强好胜、锋芒毕露而逐渐变得成熟稳重、踏实虚心。生命的蜕变就在这一刻完成。
原来,人生的玄机竟然就藏于一杯清茶。
存在与自由
存在是个事实,对此,即使对宇宙生命持悲观看法的各种文化亦无法否认。从时间的观点看,存在者在对存在历史的感知中即可认定:存在横亘于过去、贯穿于现在,并趋向于未来。存在已经存在,它就这么存在着,其中充满生机。存在者通过自身的生存活动可当下领受其生命存在的自由。这里所说的“自由”,不是指挣脱人为束缚的自由而是与生俱来的自由,即无欠缺。人体构造的和谐,各大组织器官的协调运作,皆得之于存在的事实本身而无碍于人。生而为人就拥有自由,这是存在的本性。自由感的拥有或丧失,可以作为衡量某种文化是否符合存在之本然的标准。存在先于人渴望理解存在,这也是存在与自由的问题所在。
一、摘麦穗的启示
有一个摘麦穗的故事很流行。据说这个故事发生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一对师徒之间,用以比喻婚姻和爱情。
有一天,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老师就让他先到麦田里去,摘一棵全麦田里最大最金黄的麦穗来,期间只能摘一次,并且只可向前走,不能回头。
柏拉图按照老师说的去做了,但意想不到的是,柏拉图两手空空地走出了田地。
苏格拉底问他为什么没有摘到。柏拉图说:“因为只能摘一次,又不能走回头路,期间即使见到最大最金黄的,因为不知前面是否有更好的,所以没有摘;走到前面时,又发现总不及之前见到的好,原来最大最金黄的麦穗早已错过了。于是,我什么也没摘。”
苏格拉底说:“这就是‘爱情’。”
之后又有一天,柏拉图问他的老师什么是婚姻。苏格拉底就叫他到树林中去砍一棵最大最茂盛的树回来。同样,其间只能砍一次,只可以向前走,不能回头。
和上一次一样,柏拉图照老师的说话去做了。但和上一次不同,他带回了一棵普普通通,不是很茂盛,但也不算太差的树回来。
老师问他:“怎么带这棵普普通通的树回来了?”柏拉图说:“有了上一次的教训,当我走到大半路程还两手空空时,看到这棵树也不太差,便砍下来,免得错过了后,最后又什么也带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