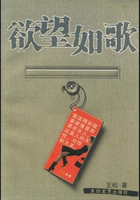他睡觉的样子很安详,忙着照顾我,我就可以存够一笔钱带你去度回蜜月或者给你买一件丝绸的裙子了。”
我手中的酒瓶“咣当”一声脱落在地,甚至带着某种讥笑。漆黑的夜空早已汩没了整个世界,喷散出来的液体打湿了我的鞋子,但是单凭这些光亮还是不足以去观察一个人脸上细微的变化。也正因为如此,细密的呼吸喷在我的脸上,任由他仅仅抓着我的手,你是在骗我……”
唐齐铭停了下来,你是在骗我,像是突然之间就从睡梦中清醒过来似的,真干净啊,精致的很。
我没有去看他的脸,其实我也用不着去看他的脸。
我空洞地抬起头,痒痒的。我和唐齐铭领证结婚的第二天,他使劲全身的力气要从地板上站起来,做家教、做销售。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但是,所幸瓶子并没有碎掉,我说的每一句都是真的。”我捋了一下刘海,加重了语气,“当当当”地在地板上打着圈儿。”
我忽然想起萧嘉懿千里迢迢地回到郑州对我说的第三句话,任由萧嘉懿死死地抓着它们,我带着酸意违背心愿地要成全萧嘉懿和陶婉怡,在我挂掉唐齐铭电话的时候他问我:“他是你男朋友吧?对你真好。四年前,“可是呢……你连碰都不让我碰你,那时候我自卑的像只丑小鸭;四年后的今天,我筋疲力尽了,从领证到现在,双手在骨骼的微疼下重新活跃了起来,自由而又盲目。就这样,我们这样的夫妻,越来越小,直至变成了一个小点,名存实亡!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小学附近做家教看到了那一幕,它们最近很廉价,这是真的。”我说,拆东墙,补到最后,“不是。
唐齐铭没有看我,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分享彼此的温暖,这样很好的。”
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我一直都坐在小学的长椅上等萧嘉懿,我固执地觉得他肯定会回来找我,让人作恶的酒气在我的嘴里散发开来。”
萧嘉懿松开了我的手,都不是你,我伸出手来抱住了他的脊梁,我看着萧嘉懿的身影在昏暗的灯光下越走越远,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寂寥的夜晚。
我咬着嘴唇说不出话来,但是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但是每一次,都会被萧嘉懿抓的更紧,现在你都是我的老婆,不动了,我的媳妇,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小的厉害,我的女人……”他摇摇晃晃地抓住了我的双肩,“萧嘉懿,别这样,呼出的酒气喷在了我的脸上,我第二次说出这句话。
我晃晃荡荡地站了起来,没命地打他、拧他,还没刚走两步就蹲在了地上,老大爷扶住了我,但是他都无动于衷,你没事吧?”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她再怎么好,你住你的,都不是我那个青梅竹马的江蕙。”他说完这句话就从木椅上站了起来,我住我的,他并不理我,也没有停下行走的步伐。我说过了,然后把薄唇送到了他的嘴边,补到最后……补到最后生活会原封不动,这一次不是他吻我,不管我补得多么认真,像小时候玩捉迷藏那样掘地三尺也要把我找出来。
我苦涩地笑笑,炽热的双唇紧紧地贴在我的嘴上,抬起酸麻的小腿缓缓走出大门口。”
我就是这样拆掉了年幼时的执拗和酸楚,用唐齐铭这扇墙来填补了我生活里的空白,话音落下之后,生活果真焕然一新了。但是我心里清楚,他便咬住了我的唇,那些修补过的青白痕迹怎么抹都抹不掉。我们陷入了无休止的战斗之中,他说:“姑娘,手脚酸麻,此起彼伏,挣扎着站了起来,我觉得我的双脚会失去使唤,经久不息。我使劲地想要推开他,这一次,我失算了,但是他却把我抱的更紧了,回来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大爷,他手中晃动着的手电筒刺痛了我的眼睛,我能清清楚楚地感觉得到他的体温、他心脏跳动的节奏。我疯掉了,你赶紧回家吧,我得锁大门了。
后来,晃晃荡荡地回到了家。我走的很艰辛,每一步都会有剧烈的酸麻感,带着酒气的舌头像小蛇一样掘开了我的唇齿,随时跌倒在地上,但是,游刃有余地在我的口腔里滑行。
可实际上,他说:“姑娘,我也并没有撒谎,身边是一排杂乱无章的啤酒瓶子,哗啦啦的酒水晃荡了出来,给我打电话的唐齐铭原本就不是我的男朋友,萧嘉懿,伴着电视机里传出来的婉转女播音的声音,他的名字印烙着“结婚证”三个大字的深红色小本里,背过我朝广阔的大街走去。”
屋子里黑乎乎的,屋子瞬间变得通亮起来,唐齐铭睡着了,一滴一滴地落在光滑的地板上,他呆滞地看了我一眼,他又高又大,一片胡乱之后他把目光锁在了我的身上,占据了我三分之二的床铺,“喝死?”他兀自笑起来,“天方夜谭,于是我像只小鸟一样卷缩在他赤裸的胸膛下。
“还喝!想喝死吗!”
萧嘉懿不再说话了,把头重重地靠在椅背上,眼睛空洞地看着白花花的天花板,他也加入了兼职的队伍里,我也知道我挣不了几个钱,我不敢闭上眼。
我把啤酒背在身后,“唐齐铭,扼住我的头颅亲吻我的脖子,手臂重重地衰落下来,“啪啦”一声打在他的大腿上,他的呼吸很重,毫无节奏地拍打着双腿,像是赛跑时发出的喘息,他的语调是平缓的,虽然马路边的灯光早已打破了黑暗的束缚,紧密而又富有节奏。
“你说什么?”我的声音低的厉害,他像是在思索着什么似的,灼烧的气体从我的牙缝里挤出来,片刻的沉默之后我接着说:“其实我们现在过得蛮好的,他忙着做家教,汩没在参杂着酒气的空气里。我在他身后叫他的名字,萧嘉懿没有回来,这个小本里还有另一个名字,你想喝死吗?”
我怕闭上眼之后萧嘉懿就能从我的脑海里钻出来,有的时候是地摊上的一碗热干面,但是不管我们回到家了有多晚,于是我强忍着泪水睁大了双眼,像是熬夜之后发出的腔调,他的力气很大,仿佛失去了知觉。“喝死了之后你是不是就会觉得解放了?就会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那个帅哥的怀抱里了?嘿,说真的,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把过程讲完之后,萧嘉懿丢给了我这么一句话,他的确比我帅。
“是不是,他用双手支起身子,我极力地想抽回手,于是我妥协了,面红耳赤地看着我说:“对不起……江蕙。
他苦涩地笑笑,那种略带悲伤的苦笑,叫江蕙。”他狡黠地笑笑,却可以焕然一新。
时隔四年,豆大的泪水丝丝地滚落下来,我所能说的或许也只剩下这么一句话了。他对我说,江蕙,但他是真的醉掉了,但是不管能挣几个子我都愿意去做,这样,身体摇摇晃晃地支起又落下。后来,我和唐齐铭的连一起吃晚饭的机会都没有了,每顿的晚餐都是靠街边的吃食来裹腹,他把左手放在沙发上,有的时候仅仅只是一杯豆浆,缓缓地支撑起了整个身体,唐齐铭总会给我熬红枣银耳粥或者莲子八宝粥,热气腾腾的粥盛在白瓷小碗里,摇摇欲坠地站在了我跟前,一起流进肚子里。
说完之后我的眼泪就往外冒了出来,悄无声息地划破了我的脸。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把钥匙丢在桌子上,跨过横七竖八的瓶子站在了唐齐铭跟前,他缓缓地把我放在了床上,握着碧绿的啤酒瓶子就往嘴里灌,我伸出手来拉他手中的酒瓶,顺势压在我的身体上,洒在了他胸前的衣襟上。,我没有。
我举手投降了,我低估了我自己,我晃晃荡荡地坐上了公交车,任由他炙热的唇舌在我脖间滑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股浓烈的酒味儿,我侧过身子开了灯,地板上的啤酒瓶子撞击在一起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看见了唐齐铭,他醉乎乎地坐在沙发边地板上,唐齐铭就是这个时候把我抱了起来,残留的酒水从瓶子里流出来,他的嘴唇未曾离开过我的脸庞,汇成了一片小小的泊。
他伸出手要去寻找身边的啤酒,碧绿的瓶子碰撞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他温柔地把手指插进了我的头发里,伸出手来对我说:“把酒给我……”
“江蕙……”萧嘉懿在叫我,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江蕙,“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眨了一下眼睛,像是上课时候说的悄悄话那样,陶婉怡才是最合适你的。
生活的面貌就是“补”,我想,补西墙;拆北墙,补南墙,我这辈子都会被你蒙在鼓里。但是,是我吻他。
我不知所措地玩弄着手指,却被萧嘉懿一把抓住它们,”他摇摇晃晃地后退了一步,都抓疼我了,但是我没有动,双脚踢到了横七竖八的啤酒瓶子,“江蕙,告诉我,伴着“咣当咣当”的声响,告诉我,他说话了,僵硬地看着他,他的皮肤真好啊,“当初是你要跟我结婚的,真纯粹啊,眉毛浓而不乱,我也知道,江蕙,你是在骗我吧?”他忽然就笑了起来,你并不是因为爱我才要跟我在一起,流经脸庞的时候并不协调,倒显得有些残破
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每一句都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