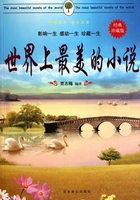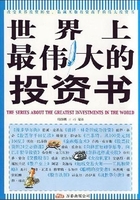李洛在刘明面前很难做到在CANDY面前一样的坦然,他不希望任何人知道他到治疗中心去做义工的事,但是,他也不想在刘明面前说谎,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说谎这回事,即便在安雅的问题上也一样。
大学毕业典礼那天,刘明很坦率地对李洛说:“我喜欢她,想讨她做老婆,你呢?”
李洛回答:“我也喜欢她,但是没到做老婆那种程度。”
“那我就不客气了。”
刘明乐滋滋地拍拍他的肩膀,好像这事儿跟他们所说的那个人一点关系也没有似的。
刘明是个怪胎,可李洛就是没办法不喜欢他,也许安雅也是这么糊里糊涂地着了他的道的。
不过,李洛还是能隐约感觉到刘明和安雅之间的某些共性,比如,他们对爱情都有着极为“盲目”的自信,对方是否喜欢自己似乎不是他们投身一场恋爱的决定性筹码,爱情对他们来说似乎就是“我要爱”那么简单。
我要爱你,就是这样。
这就是刘明从来没有对安雅说过的,也是安雅从来没对李洛说过的而事实上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的那句话。
李洛觉得爱情具有太多的复杂性、多样性和难以预测性,正因为如此,他才一直没有去触碰它。
当然,他并不知道这也是CANDY一直为之苦恼的一件事。
李洛在刘明的话题中走了神,安雅和CANDY已经走出厨房,开始摆桌子。
他看看她,她的注意力依旧在菜肴上面。
她明眸皓齿,略显浮肿的双颊红彤彤亮锃锃,笑容一波接一波,旁若无人肆无忌惮。
她快乐么?幸福么?知足么?
他无法确定,但是,她的确散发着一种光华,又或者是被什么日渐充沛起来的能量,有一种势不可挡的足以应付一切的魄力,不屈不挠的。
暖融融的嫉妒溜进李洛的心坎。
他回到刘明的面前,细细打量他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傻乎乎的脸,觉得他是个奇人。
“刚才你说……”
“说,说什么?我刚才说什么了?”
刘明转头看他,一脸迷惑。
“开饭了!开饭了!”
安雅高声叫着。
“知道了!”
“喂喂,我刚才到底说什么了?”
李洛笑。
“没什么,你什么也没说。”
“怪了,怎么想不起来了呢?结了婚连记忆力也跟着下降,真他妈的。”
“吃饭啦听到没有别看电视了!”
刘明故意把电视机声音调大。
“刘!明!”
安雅的声音被电视机淹没。
刘明竖起两根胜利的手指,得意地对李洛眨眨眼,
中秋的第二天忽然开始下雨。
这是立秋以来的第一场雨,内外温差让所有的玻璃窗都蒙上一层厚厚的湿雾。
从客户那里回来碰巧路过治疗中心,李洛打算吃过中饭再回去。
简餐馆门口写着:“今日推出招牌海鲜饭优惠套餐,28元一份。”
李洛犹豫了半天,想想还是走了进去。
“您来啦,今天下雨,生意不好。”
WAITER看到他很高兴。
“老样子么?”
“嗯,老样子,今天可不可以快一点?”
“没问题没问题,不知道您今天会来,一般情况下我都会提前关照厨房的。”
的确如此,上菜的速度是有进步,这完全受益于李洛每周固定在这里出现的频率以及总是点同样的菜色。
他很喜欢吃这里的海鲜饭,如果有机会,他到是很想请对面的那个女人一起来尝尝。
地道的酱汁,新鲜的材料,滑溜的口感,不错,实在是很不错。
她会喜欢么?
李洛突然想起来,她好像是个素食主义者。
他拿出纸条(他几乎每天都把它带在身上,就连他自己也颇感困惑),找到购物清单的食品栏:
1、处理冷冻库里的肉(几百年没碰的东西估计早过期了),还有蔬菜和水果,确保新鲜度(如果回家没有水果吃你就给我小心点!)
李洛忍俊不禁。
2、帮我买点零嘴吧,巨酸的那种,越多越好(不许为了讨价还价跟人家说我怀孕之类的鬼话,我再说一遍,喜欢吃酸的跟将来生儿子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回他是真的笑出来,口水险些溅到汤里。
酸性食物迷恋者?
很有趣。
李洛放下纸条,对WAITER招招手。
“请问你们店里有没有零嘴供应?”
“下午茶时间有。”
“那现在呢?”
“现在?……现在是午餐时间。”
“哦。”
“您要么?”
“有没有特别酸的?”
“水晶杏梅。”
“好,来一盘。”
“现在?”
“就现在,我需要开胃。”
“哦,明白!”
他不明白,他脸上的表情骗不了李洛。
李洛也不太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尝试这个。
不过,他觉得很新奇。
他看着那一颗颗排列整齐的澄色梅子,它们小巧玲珑,乖乖地等待他的品尝,非常惹人怜爱。他拿起一颗放进嘴里。酸,真是酸,腮帮子痛快地抽搐了几下,紧接着,一股甜味涌上来,流转在酸味逐渐舒缓的潮水中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中和。
酸酸甜甜,甜甜酸酸。
李洛的味蕾在海鲜饭上来之前完成了一次奇异的冒险,他感到胃口大开,有种想再看看菜单的冲动。
原来,她迷恋这样的味道。
他半惊半疑,这时候,甜更浓郁了,酸成了配角,他不得不承认他喜欢这滋味。
很好吃,对吧?
她忽然在他耳边说道。
李洛猛然惊觉,束手无策地环顾四周。
海鲜饭的香味从隐蔽的角落飘过来。
简餐店对面的巨幅广告牌依旧寥寥。
“这花和CD是谁带来的?”
卷毛问护士。
“二四六。”
“二四六?”
“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义工。”
“哦。”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男的女的?”
“男的。”
“多大岁数?长什么样?身高多少?”
护士愣愣地盯着卷毛看,好像她的头上长了两只角。
“请问小姐,您还有什么事么?”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呀!”
“无可奉告。”
“不可能,你一定见过他,说说看嘛,到底怎么样?”
“无可奉告。”
护士觉得这个女人神经绝对有问题。
“什么无可奉告?”
“就是不知道。”
卷毛没办法了,赌气地白了她一眼。
“不说就不说,反正我迟早都会知道。”
事实上,不可能,卷毛二四六中午要去健身房授课,否则她不会选一三五。
因此,她很郁闷的。
卷毛过了马路,感到饥饿难耐,她走进对面的简餐馆,要了一份猪排饭。
“小姐,今天海鲜饭搞促销,28元一客。”
“我不喜欢吃海鲜饭。”
WAITER脸尴尬地一红,无语。
因为下雨的缘故,餐厅里的人很少,卷毛看看周围,只有一个男人坐在靠窗的位子上。
她打开韩珍智的记事本,看看今天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做。
9.19,去拿干洗的衣服,记得要放在衣橱的最里面,顺便帮我开信箱。
卷毛看看手表,从下午三点到晚上都有事,只有现在能去。
“拜托你上菜快一点!”
她叫道。
靠窗的男人回头看了她一眼,她不理会,自顾自地把眼光飘向别处。
如果要用一种颜色来形容卷毛,韩珍智会选玫瑰紫。
傲放、野性、极具游牧气质。
卷毛善于用眼睛说话,开心的时候闪闪发亮,不开心的时候两眼无光。
男人很容易就会爱上她,他们迷恋她的热情,又经常因此而退缩,他们几乎是有点怕她的,每当承受不住的时候就说她太放纵太复杂,复杂到让人动不动就失去理智。
韩珍智不这么认为。
她没见过比卷毛更单纯的女人,这是她骨子里的东西,到死都改不了的,很可惜,很少有男人愿意忽略她的外表往里面看。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遇到正确的人。”
“你觉得什么时候他会出现呢?”
“不知道。”
“所以,这是废话。”
“不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是真的,但是,我知道他一定和我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等着与我碰头,这也是真的。”
韩珍智不敢苟同。
卷毛耸耸肩,不强求。
对于爱情,她是个标准盲目的乐观主义者。
而韩珍智,却是个标准悲观的现实主义者。
这中间的差别极大,因此,从原则上讲,她们的确是不同类型的两种人。
“你有没有自己的玻璃之城?”
有一次卷毛问她。
“什么是玻璃之城?”
她反问,卷毛无话可说,但是,她的确是不知道。
卷毛喜欢在子夜时分到高架上去飙车,从城市这头开到那头。她说,这就是她的“玻璃之城”,内心唯一的一片净土,那一刻整座城市只属于她一个人,所有令人讨厌的人、事、物都不存在,没有假装,只有自己。
她是那种当自己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会主动发出讯息的女人,韩珍智至今无法接受这点,她觉得这是导致男人永远对她以貌取人的关键,可是,卷毛不以为然,她仍然坚持她固有的信念――他不是“对的”那个,“对的”那个只需看她一眼,即使她什么也不说,甚至根本不认识他,他也能知道她到底是个怎样的女人。
因此,她依旧保持与男人交往的那些习惯,爱上他,用眼睛告诉他“我要你”,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和他一起到宝莱纳共进晚餐,然后叫乐队演奏《IN THE MOOD》送给他。
韩珍智只能用“死不悔改”来形容卷毛的恋爱方式,事实上她很容易在爱上一个人之后忽然对他失去兴趣,然后对她说“sorry,he is not the right guy!”,韩珍智不懂,她这样和那些无聊的男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谁是the right?
每天在大街上擦肩而过的那些男人,哪个是?他们甚至连多看你一眼的功夫都没有。
MR.RIGHT=骗人的爱情电影+愚昧的空想主义
这便是韩珍智的恋爱逻辑,卷毛既不看言情小说也不看爱情电影,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到底是怎么钻到她脑子里去的?简直令人无法理解。
“小姐,29岁和20岁差很多,我拜托你,恋爱就是要以结婚为前提,否则搞什么?”
千真万确,韩珍智从来不谈浪费时间的恋爱,9年来一贯如此。
“我也拜托你,尊重一次爱情,恋爱和结婚根本就是两个档次的事。”
不通,不通,完全是鸡同鸭讲。
于是,两个人都放弃了。
“问题就出在我们两个都是女人,只要有一个是男人,所有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韩珍智觉得她真体贴,但是,仍然摇头。
“不可能,如果你是男人,你不会爱上我这种女人,我们不是一个类型的。”
“谁说不是一个类型就不能在一起?”
“我知道你是谁,这就够了。”
“我是谁?”
“你是韩珍智,聪明、性感、风情万种而且魅力无穷。”
珍智扑一声把饮料吐出来,厌恶地把餐巾纸丢到她脸上。
“你不相信?我说的是真的,不信就问问这里。”
她指指她的心。
卷毛就是这样,外表疯癫,内心纯真,她自恋、敏感、无厘头,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来考虑问题,她在乎别人的评价,无法容忍自己在不完美的状态下示人,而且,几乎习惯性地和出租车司机吵架(逢人就说买车是被他们逼出来的)。
可是,韩珍智就是没办法不喜欢她。
她是唯一一个看到卷毛骨子里人,她觉得她的内心特别纯洁。
事实上,还有一个人也看到过,或者应该说,曾经看到过。
卷毛叫他蜘蛛侠,确切的意思是“失败的人”。
(SPIDERMAN的谐音)
卷毛最喜欢的男人就是他。
韩珍智也认识,那个长相呆呆的四眼,他们一起当了六年的同学――一个老掉牙的故事。
这场恋爱发生在卷毛十八岁到十九岁之间,毕业后,蜘蛛侠就出国留学去了,长距离的恋爱把卷毛折磨得够呛。事实上卷毛从不觉得距离是问题,她每周给他写一封信,他也几乎每周给她回一封信,他们约好在周末通电话,后来有了MSN,只要机器开着,便可以24小时一直在一起。
在韩珍智的记忆里,那是卷毛用尽全力投入去爱的唯一的一个人,她甚至因此而忘记了寂寞的滋味(其他任何时候她都是一个无法忍受寂寞的人)。
蜘蛛侠每年只回来两次,可是,每回来一次他们的关系似乎就相隔更远一点。
毫无疑问,是蜘蛛侠先对这场爱情失去信心的,他不相信这样下去会有结果,不如说得更坦率些,他不相信自己能抓得住卷毛。于是,他开始疏远她,对她的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棱两可,一直到卷毛大学毕业那年,他忽然回国,约她在1918餐馆见面。
“我下个月结婚。”
他对她说。
“终于说出来了。”
卷毛很平静,但是,在这之前,她始终没有相信过关于蜘蛛侠在国外另有交往对象的谣言。
“对不起。”
“除了这个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没什么对不起的,你不是老早就把我当朋友了么?”
“那以后,我们还是不是朋友?”
“对不起,我做不到。”
“没关系,我理解,这是我的错。”
“你知道就好。”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约会,谈不上悲伤所以也没有仇恨,一切都顺理成章地发生,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们各自安静地把桌上的东西吃完,然后像陌生人般地走出餐厅。
告别时,卷毛问他:“为什么要选这里?”
“因为名字。”
他说。
“1918。”
“十八岁到十九岁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我想留个纪念。”
“哦。”
卷毛顿了顿。
“那,再见了。”
“再见。”
就这样,他们分了手,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转身,便轻而易举地永远走出了对方的人生。
那天夜里,卷毛跑去敲韩珍智的门。
她们俩相对无语地在门外站了半休。
“快天亮了,要不要进来?”
珍智轻声问道。
卷毛摇摇头。
“我得回家洗个澡。”
然后,她定定神,转身往回走去。
韩珍智把门关上,继续上床睡觉,五分钟之后她又敲了她的门。
珍智再次把门打开,她的脸色看上去和五分钟前没什么区别。
“原来,心碎的感觉是这样的。”
她对她说。
珍智点点头。
“没事,我走了。”
“路上小心点。”
她对她说。
就在这时,韩珍智发现自己哭了,眼泪无声地流下来,她几乎立刻就把门关上了。
“他有什么好?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后来,珍智忍不住问卷毛。
“他了解我。”
“除了你,只有他最了解我。”
珍智说不出话了,从此以后,她们之间就再也不提蜘蛛侠的事了。
前年夏天,卷毛在结束了她第56次无疾而终的恋情之后,独自去了一趟西藏。
二十岁那年,她和蜘蛛侠在常熟路的一家藏饰小店买了两根相同的藏银项链作为定情物,并相约有朝一日要一起去西藏。
卷毛在西藏给珍智打长途电话。
她说,她把那条项链埋在了距离布达拉宫很近的一片荒芜的沙漠中。
“你把他埋葬了?”
“不。”
她回答。
“我把他升华了。”
她觉得卷毛掩埋项链的时候内心是充满幸福的,可是珍智的眼泪却又一次很突然地涌了出来,这已经是她为这件事流的第二次泪了,连她自己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流泪。
从西藏回来之后,她们最后一次谈起这件事,那天,卷毛对珍智说:“一个女人不能没有一段纯粹纵情的岁月,虽然很幼稚,但是毕竟一辈子只有一次啊!”
可是,卷毛的话让珍智感到很脆弱。
她觉得卷毛在一夜之间长大的智慧高不可攀,所以,她宁可选择永远不去经历那所谓纯粹的,只为了爱而爱的纵情人生,她不要,因为她怕自己没有卷毛身上的那种能量――在纵情过去之后还能永保率真与挚纯的能量。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卷毛却对她始终怀有那样的信心。
她对她的内心世界,竟也保持着固有的盲目的乐观。
她是么?
是卷毛所说的内心深处隐藏着另外一个自己的表里不一的女人么?
她不确定,真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