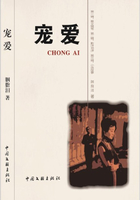最后病危,往古晋诺玛私人医院留医,眼看着似乎不行了,可我仍不死心,三更半夜煮了她最喜爱的碎肉粥,就带着到她病床。谁知她遂然坐起,见粥眉飞色舞,一口气吃了个干净,一边还在有一搭没一搭的和我闲话家常,又侧头嗅着空气,问我是否关好煤气以免火患等等,然后惬意安枕睡下。我满怀希望回家,隔天,母亲即与世长辞,那碗粥,是她回光返照最后的晚餐。
“粥”对于海外华人来说,饥时不亦乐乎,饱时也不亦乐乎。吃粥成了一种华人的食文化。梁实秋承认:“我不爱吃粥。小时候一生病就被迫喝粥。”但他仍然专门写过一篇雅舍小品,题目就叫《粥》。文中写道:
一说起粥,就不免想起从前北方的粥厂,那是慈善机关或好心人士施舍救济的地方。每逢冬天就有不少鹑衣百结的人排队领粥。“粥不继”就是形容连粥都没得喝的人。“NFDA2”是稠粥,“粥”指稀粥。喝粥暂时装满肚皮,不能经久。喝粥聊胜于喝西北风。
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某些粥还是蛮好喝的。北方人熬粥热,有时加上大把的白菜心,菜烂再洒上一些盐和麻油,别有风味,名为“菜粥”。若是粥煮好后取嫩荷叶洗净铺在粥上,粥变成淡淡的绿色,有一股荷叶清香渗入粥内,是为“荷叶粥”。从前,北平有所谓粥铺,清晨卖“甜浆粥”,是用一种碎米熬成的稀米汤,有一种奇特的风味,佐以特制的螺丝转儿炸麻花儿,是很别致的平民化早点……
梁实秋只作了客观叙述,也只谈了中国北方的粥。其实,“粥”不仅是一种食品,一种文化,更有它的历史,内含许多学问。在中国,华人吃粥的历史,可能要追溯到上古三代以前。《周书》就有云:“黄帝始烹谷为粥。”把创造粥食归功于黄帝,大概只能聊备一说,不可尽信;但《礼记》上确有“NFDA7粥之食”的记载,稠粥稀粥的“粥史”可谓悠久。不仅如此,又因中国历史如斯悠久,幅员如斯辽阔,物产如斯丰茂,东南西北中诸地的粥食定然百花齐放。清人黄玉鹄在光绪年间悉心搜索,编过一本《粥谱》,收载的各地粥食达240多种。现今着名于华人世界的,要数鱼片粥、对鸡丝粥、白粥、小米粥、猪肝粥、瘦肉粥、皮蛋粥、艇仔粥、绿豆粥、莲子粥、紫米粥、玉米粥、南瓜粥等等等等,自然还有作为粥之“综艺节目”的腊八粥。烹粥也成为一件乐事。明朝一位自号为“戒奄老人”有首《煮粥诗》:“煮饭何如煮粥强,妈同儿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三升用,两日堪为六日量。有客只须添水火,无钱不必问羹汤。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长。”
有的海外华人用“粥”怀旧,称“粥者,中国人的国食也”。此说一时难以评定,但从“民以食为天”的角度去看,“粥”的确构成中华传统文化在生活领域的一个元素。中国古代文人对“粥文化”颇多赞叹。宋人费衮《梁溪漫志》中引苏东坡一帖有云:“夜坐饥甚,类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致新,利膈养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之。粥即快美,粥后一觉,尤不可说,尤不可说。”是何等的悠哉快哉。陆游也曾为粥赋诗一首曰:“世人个个学年长,不知长年在面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是何等的清明致远。还有那个“扬州八怪”领头人郑板桥,在《范县署中寄含弟墨弟四书》中,绘声绘色地描写晨起食粥的情景:“暇日咽碎足饼,煮糊涂粥,双手拜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又是何等的谦良之态!可以想象,那稠稠糊糊、热热腾腾的粘粥进入肠胃,“难得糊涂”的此公更感应着人与大地同在,与知足同在,与世事无争,到了一个安贫乐道的境界。同理,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对于先祖粥文化的念想和现实人生中食粥习俗的维系,已远非果腹的功用,恰似承传着中华文化的一份实在的经验。
这种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对接,在“食文化”上,还表现为对于“茶”的心态上。
直到现在,在海外华人的后代中常常有喝咖啡还是喝茶的争论——如同早餐吃面包还是喝粥的争论一样。自然,咖啡与茶可以并存,吗啡与海洛因则必须禁止;但“茶”(tea)毕竟是中华文化形象的一个标识,是造物主特别替中华民族安排的清香、高雅的饮品。
旅美的华文女作家刘于蓉,三十年的域外生涯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但她之所以喝咖啡,“除了品尝那浓郁的香味外,主要原因是想借咖啡因来提神醒脑”,而在美国,“一般餐馆里供应的廉价咖啡,恰如此地的中国餐馆里给咱们喝的免费茶一样,一分钱,一分货,当然考究不起来”①① 刘于蓉:《咖啡情浓》,《人生舞台在美国》,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不过,女作家还是要考究一下,要进“粤宫酒楼”去治疗一番乡愁。她的短篇小说《春宴》①① 刘于蓉:《春宴》,同上。,就写了主人公念华(注:“思念中华”之简称也),总要抽空在星期六的早晨,带着两个“咖啡族”的女儿,趁着春浓去饮早茶:
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是她们的侍者,他很快地端上一壶清香扑鼻的菊花茶,殷勤地为她们斟入小茶盅内。依惯例,两个女儿双手举起小茶盅,齐声向母亲说:“祝妈妈永远健康美丽”!然后故作天真状,啜饮着滚烫的花茶,啧啧有声,以表示她们多么的欣赏中国茶。
“唉,菊花茶,是立场(注:念华的已故丈夫)。生前最爱唱的,又是一个没有你的春天……”念华陷入沉思中。
念华很高兴两个生长在美国的女儿没有忘记中国文化,茶,成了她们对亡父的牵挂的引子。世界上最孤独的情感不在于相隔多远,而在于离自己最近的人能否理解你的所爱。人和人之间的联系纽带总是那么脆弱,人们又总是容易迷失在彼此的心灵中。在女作家笔下,一小盅清香的茶,可以触动相通的思念之情,可以使代际的内心亲近起来。
华人喝茶,不像日本人严肃于茶道,而是倾心于茶艺。旅居加拿大的华裔诗人洛夫悟到吃茶本身是一种艺术,一种心境:
一杯在手,饮者的谈话通常会突破世俗的樊篱,天南地北,中外古今,无所不涉,而评骘世事,月旦人物,更成了话题的焦点。……一面吃茶,一面不伤筋骨地骂骂你所厌恶的人,或社会上不合理的事,未尝不合卫生之道,因为畅饮中可以把胸中的郁积,在热茶的氤氲中逐渐化去,而换来一片祥和清穆的心境。
酒属感性,茶则富于知性;酒是诗,茶则近乎哲学。我们可以从李白的诗中闻到酒香,引杯就唇之际,总不免会想起“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的自我调侃之句。但饮茶犹如读庄子,读尼采,让人沉思,对生命有所感悟。如饮的是好茶,甚至可以使你提升到《大观茶论》中所谓的“致情达和”的境界。①① 洛夫:《吃茶二三事》,《经典美文三百家·母题卷》第15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正因为吃茶是一种艺术,所以中国文人有“请到寒斋吃苦茶”的嘉言,也所以华人开的茶馆不叫“茶道馆”而命名为“茶艺馆”。茶往往成为刻画“中国”的重要形象,其实可真是历史悠久。相传远古的神农氏“尝百草”,最早发现了一种常绿灌木茶树,品尝过可以止渴、提神的茶叶。于是,数千年来无数的无名氏,由嚼青叶而发明为采叶焙制,再由采叶焙制改良为煎烹饮啜,成了深具民族性的一种饮料。说到茶名,据《神农本草》考:“一名茶,一名选,一名游,冬生贫州谷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诗经·谷风》有句:“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荼”就是现在的茶,《康熙字典》解:“世谓古之茶,即今之茶,不知茶有数种,惟荼,苦茶之茶,即今之茶”。“茗”则是古代茶的另一名称,如《桐群采叶录》载:“西阳、武昌、庆江、晋陵,如茗,皆东人作清茗。茗有饽,饮之宜人。凡可饮之物,皆多取其叶。”唐代白居易如此描绘《茶舍》:“乃翁研茗后,中妇拍茶歇。相向掩柴扉,清香满山月。”南宋鲍令辉更作《香茗赋》,称颂“茶为芒茗”。中国人饮茶,讲究的是情趣,“夜深共语”、“小桥书舫”、“茂林修竹”、“严溪之畔”、“酒闸人散”乃是品茶的最佳环境和时辰。“寒夜客来茶当酒”。蕴含着高雅的情致。“茶热清香,客至最是可喜;鸟啼花落,无人亦自悠然”,不啻是生活的艺术,是心灵的无形的陶冶与抚慰。饮茶往往以饮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有碍品茗的雅兴。《红楼梦》里妙玉谈到茶以少喝为佳,宜品饮而不可牛饮:“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三杯便是饮驴?”此说也旨在喝茶要注重情调和情趣。自然,华人还讲究茶艺与茶具的完美结合,文人雅士都寄情于壶。壶之厚薄、高低以及几何图形之变化,可谓百花齐放,无论是名器的摹仿、雅物的塑就,还是壶身的铭诗画词,都达臻境,且为世界之最。
“临水卷书帷,隔竹支茶灶,绿缘一壶寒,添入诗人料”。清代女词人吴藻的这一诗句,融茶道、茶艺、茶境于一体,“茶”成为山川灵气诗情吐纳的交点。有论者总说中国人长于史而短于哲,其实,中国文化传统不仅长于史,也长于艺,同时又并非不长于哲——只是不同于黑格尔们那种求大、求体系之“哲”罢了。由“茶”亦可得知,此“哲”在“道”,在“悟”,并和“艺”体合无间。“道”之生命进乎“技”,“技”之表现启示“道”,这是艺术境界的精妙阐发。天地氤氲可秀结于“茶”,经“实用”而“传神”、而“妙悟”、而“添入诗人料”,茶文化也就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千年百代,“润物细无声”地漫淫于华人集体潜意识。这样,无论是“茶”还是“粥”,都构成了一种可以生长出“中华性”母题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氛围,而不像十七世纪以前的外国人,只惯饮白开水,甚至到了十九世纪,英国有的政治家和律师还闹过呼吁立法,列茶为禁品的历史大笑话。
“茶”与“粥”自然只是一种普普通通的饮食习俗,但一滴水见太阳,那是“种族记忆”的投影,是“飞鸟犹知恋故林”①① 丘逢甲:《愁云》,见《岭运海日楼诗钞》。的心绪。正如中国大陆一首流行的歌曲所唱的: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的心依着你;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的情牵着你;
无论我停在那片云彩,
我的眼总是投向你,
如果我在风中歌唱,
那歌声也是为着你。①① 王健词、谷建芬曲:《绿叶对根的情意》。
习性之缘连通着“乡土中国”,表达了一种人生与艺术的情韵。海外华人可以把“粥”、“茶”此类日常生活习性,抬高到诗化的倾向,倒也并非表现有多高传统学养,恰恰说明了在文化认同问题上,他们毫不含糊地站在了中国文化一边。中国文化、风物、民俗,正是通过了再平凡不过的具体细节被诉说了出来。因而在“我是谁”这样一个根本性的身份问题上,没有走失一种记忆,一种皈依。不论走到哪里,总有身处边缘对故国的远望与缠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