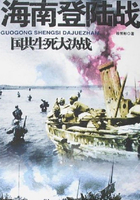记得也是在一个夏天,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次主题词为“多元之美”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动情地说:“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西方思想文化界近年来盛行“互动认知”的思考方式,据悉,他们把孔子和老子、庄子、墨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列为人类古代最杰出的思想家,六位中中国就占了四位。强调“和而不同”,除孔子以外,老子的道义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的理想是“太和万物”;载于十三经的中国最早的美学着作《乐记》,集“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的学与术之大成;另一部《礼记》,也从礼乐相成的角度,力主“以多为贵”,其达道乃“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凡此种种经典论说,莫不以和谐与发展为追求。“和而不同”因之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它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影响世界文明进步的文化观念。这一观念也为华文文学带来智慧和器度,即便是流散于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都在同一天空下呼吸,都有特异的姿态,都可以各擅胜场,对于不同的思想观点、创作流派、艺术风格乃至新生事物,此道中人都应该持一种能坚守母体又包容他者的态度。此一文化之脉,如今也如汩汩清泉,潜在地流淌于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展开之中。
(二)意识之链
文化之脉又接通意识之链。
细心阅读海外华文文学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作家的意识深处与中华文化的链接。
当鲁迅把中国视为一个革命和和改造的对象时,在马来亚出生的华人辜鸿铭对中国的思考与意识又有所不同。辜鸿铭是上个世纪初少有的对中西两种文化均有透彻了解的学者。正值国内五四精英们大力宣传西方文化时,他却礼赞传统中国文明和儒家学说的优秀。他知道如何运用西方的语言,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弊端进行攻击,说明只有东方文明才在世界上最具有发展的前途。当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被无知、偏见和歧视所笼罩的时候,他力推中国文明的价值,称之为有着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辜鸿铭把精神作为文明发展的基本条件,认为一种文明的成功,并不在于看这种文明是否产生了城市、贸易、汽车和其它物质的财富。对文明的评估,最重要的是要看这一文明产生了什么样的人。中国文明的博大,也正是因为中国的君子风度和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创造了中国文明的灵魂——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从这些男人和女人的个性里,他看到了有着和西方人一样的沉潜(deep),豁达(broad),纯朴(simple),并且还有着他们所不具备的优雅(delicacy)。这几种优良素质的总合,使中国人给人一种温良的印象(gentle),在有“赤子之心”的同时,又具备“成年人的智慧”。他所阐发的“中国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义”,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上,无疑写下了独特而醒目的一笔。他通过比较文化的方法对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精神的把握和强调,是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明放在同一平面加以对照分析。这种弘扬中国传统精神而抵御西方“妖魔化”中国的文化策略,无论从方法论本身还是它反映的社会情绪上,都体现出了某种二十世纪思想界的前沿意识。
中国意识往往哺育着炎黄子孙的心智,启发着华文作家的创作灵感。苏雪林在192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棘心》,是赴法国留学历程的自叙传录,小说题名《棘心》,就出自《诗经·邶风》中的《凯风》一诗:“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和煦的风从南方吹来,抚摸一丛丛枣树的幼苗,幼苗感激地睁开眼睛,思念着辛苦操劳的母亲,《棘心》以刻骨的疚心和长长的哀慕,纪念自己最敬爱的有着刻苦耐劳、敬老爱幼、怜贫惜弱传统美德的母亲,作品似歌似泣地沐浴在博大的母爱之光里。
旅居加拿大的洛夫,在长诗《漂木》中化用李白《将进酒》的诗章,也以“朝如青暮丝成雪”起兴:“朝如青养成雪,发啊/我被迫向一面镜子走近/试图抹平时间的满脸皱纹/而镜子外面的狼/正想偷袭我镜子里面的狈”,生命有“狼狈”之说,时间追逐着一个寂灭,这种人生感悟,与中国古代诗人的生命浩叹遥相呼应。
旅美的白先勇,在《台北人》的扉页上,引录的是中唐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头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纽约客》的卷首,白先勇又引录了初唐诗人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浪迹天涯,漂流他乡,因时空的迁移、变化,面对沧桑与旷远,不免生发陈子昂式的生命浩叹。空间的迁徙固然是对人生难以应对的困惑的一种回避,但生命仍有无法承受之重,成败难定,得失难辩,尤其在新境中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纠葛更是如此。白先勇的《纽约客》系列包括了九篇短篇小说。在开篇《芝加哥之死》中,主人公吴汉魂赴美拼打六年,刚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然而在博士帽到头之日,恰是他人生悲剧之时。生命之“始”与“终”于同一天完成,倒不是小说家的刻意安排,而是无法逃避的必然。吴汉魂属自费留学,租了潮湿阴暗的地下室一住就是六年,恋人离去,母亲病逝,一连串的打击已不堪忍受。当他学业有成,冲出自囚般的“地牢”,来到地面之后第一次“性”的放纵,竟浑然不觉地跟别人买醉,最后倒在了妓女萝娜的床上。他有意无意地拿生命作了抵押,终于一次性地投入湖中,结束了年轻的自己。我们可以注意作家给主人公起的名字叫“吴汉魂”。这是“无汉魂”的谐音。“无汉魂”并非生来就“无”,恰恰是赴美以后才失去的。学了六年西洋文学,既视祖邦为畏途,又见美国不是理想的天堂,他生命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旧“魂”既失,新“魂”不得,一个空壳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成为一种宿命。在另一篇小说《冬夜》中,白先勇为主人公取名“无柱国”,也如“吴汉魂”一样,是“无祖国”的谐音。没有祖国的吴柱国,尽管已是美国大学的资深教授,但他仅仅表面的风光,老伴过世,无儿无女,与外国弟子无法沟通,孑然一身地承受着故国之思的心痛。
我们还不难发现,有的作家引录古诗起兴,喜欢发思古之幽情,浇心中之块垒,启灵感与遐思。如瑞士的赵淑侠《举头望明月》:“翻开唐诗宋词,举目皆是月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满月撩人乡愁,残月陷入孤绝。元曲西厢记里‘云破月来花弄影’,却又把月亮形容得鲜活香艳,一派风流体态。”①① 赵淑侠:《情困与解脱》第109页,台北健行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而有的作家则采取汉语修辞中的“谐音”技巧,可以说是巧用汉字同音异字的特点,以近音表达双关义,既是谐趣的联络,又有隐含的谐音字义,述事精当,耐人寻味。
不独如此,更有一些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甚至在作品的布局、结构上,干脆运用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作为叙事方略。旅英的虹影,受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启发,开掘家藏之宝,写了《垂榴之夏》——男有刚、女(镇长的女儿)有烈的现代笔记小说,用她的话说,是“将传统连接现代,有意与冯梦龙、纪晓岚等大师握手言欢。以古今辉映的手法,营造出穿越时光、前世今生的魔幻之感。”①① 参见胡辙:《解读虹影》,《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年第2期。旅居荷兰的林湄,在其长篇小说《天望》①① 林湄:《天望》,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中,由弗来得的传道和荣微云的移民两条线索互动,全书则借助五行之说,分“水”、“土”、“火”、“金”、“木”五大部分,以“水”象征传道者、移民者之漂泊,以“土”象征人在红尘中之污染,以“木”象征枯木逢春之希望,以“金”象征拯救与自赎之淬炼;以“火”象征心灵枯竭的人们所承受之火浴,从而把五行循环相克相生的自然观,融入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和求索之道。可见,中华文化思想和审美意识,如此深深潜入了海外华文作家的灵思。
(三)习性之缘
无论是祖辈“过番”下南洋,还是今世“西渡”去欧美的华人,总会装一缕乡情在心间,传一代又一代的连绵。这种乡恋,这种文化情结也可以从作为物的“食文化”中体现出来,化作经常书写的内容。
孔子曰“食色性也”,“食”是摆在第一位的;鲁迅说“先有温饱后有发展”,“食”是人生的前提。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田思有一篇题为“父亲与粥”①① 田思:《父亲与粥》,《马华文学大系·散文(二)》第392—页,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的散文,写于1993年3月。文中提到,那时他的父亲已八十多岁了,仍保持着每天早餐“吃白粥”的习惯——
(每天清早)总见母亲在灶边添柴煮粥,脸庞给灶火映得红彤彤的。有时在干柴爆裂的“噼——啪——”声中,听到屋外鸡鸭的呱噪声,那准是母亲到小寮子捡鸡蛋去了。而我知道,当天父亲吃早粥时,会多了一碟煎得黄澄澄的荷包蛋,父亲经常买了三分钱的马来糕给我当早餐,但他自己和母亲还是天天吃粥。他说这种习惯在唐山祖家就养成了。父亲过番之前,曾干过好几种行业,包括卖熟食。他兴趣来时也可以烧得一手好菜,特别是五香春卷更是他的拿手绝技。但他坚持以吃白粥来作为他日常的早餐,几十年来绝不改变。在日本占领时期,米粮缺乏,他就在海外渔村的内陆自己种谷子,用自己椿出的白米混和着番薯熬成浓粥来吃,就这样挨过了三年八个月的黑暗日子。
“饥者易为食”,如果说田思所写的父亲食粥是因饥饿而养成的饮食习惯,那么,另一位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沈观仰笔下的母亲食粥,已是养生求存的不二法门。他在《粥之糊涂乐》①① 沈观仰:《粥之糊涂乐》,《马华文学大系·散文(二)》第360—363页,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中写到这样的细节:
(母亲)年老时体弱多病,又择食,唯独对粥有天生的喜爱,每餐无粥不欢,就着丁点小碟的酱瓜酱菜咸蛋咸鱼腐乳等,舌间“的”、“得”有声地享受晚年的清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