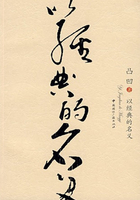(第一节) 燕卜荪的《含混七型》
1930年,燕卜荪才二十四岁,在剑桥大学取得数学硕士学位后转攻文学,他在瑞恰慈批改的一份作业启发下写出了《含混七型》一书。他在此书中以大量例证为支持,证明复杂意义是诗歌一种强有力的表现手段。他沿用了一个旧名称,称这种现象为“含混”(ambiguity)。
在初版中,他对“含混”下的定义为:“能在一个直接陈述上加添细腻意义的语言的任何微小效果。”在后来的版本中,他把这句定义改成:“任何语义上的差别,不论如何细微,只要它使一句话有可能引起不同反应。”
因此,他所说的含混,面是很宽的,而且我们看到,这定义并非严格新批评式的。
燕卜荪把含混分成七型,我们每型举一例说明一下。
第一型:“说一物与另一物相似,但他们却有几种不同的性质都相似。”燕卜荪举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第七十三首中的句子:
荒废的唱诗坛,再不闻百鸟歌唱。
鸟歌唱的树林,被比成教堂中的唱诗坛——为什么两者相似?燕卜荪列举下列各相似点:一、因为教堂中有歌声,树林中也有歌声;二、因为教堂唱诗班与林中鸣鸟都是排着队唱歌;三、因为教堂唱诗坛是木制的;四、因为唱诗坛被教堂建筑的墙掩蔽着,像树林一样,而彩色玻璃的窗子和壁画又如花和叶;五、因为现在教堂荒废了,灰墙就像冬天的树林,可漏进天光;六、因为唱诗班少年冷漠又顾影自怜的美色与莎士比亚对《十四行诗集》受赠者的感觉相合;七、因为其他各种各样现在已难以追索其分量的社会和历史原因。
燕卜荪说,仅此一型就“差不多把文字上有价值的东西全包括在内”,足以说明“含混的机制存在于诗的根基之中”。比喻性复义的确广泛地存在于文学语言中,因为形容词往往是个压缩的比喻。海外华人学者郑树森曾将“清辉玉臂寒”的多种英译加以比较,发现有人译成“白臂”(white arm)。有人译成“纤臂”(delicate arm)。想保持这复义的唯一办法是译成“玉的臂”(jade arm)。但在英语文学传统中这就会令人不知所指(见《奥菲尔斯的变奏》1979,42页)。这是个很有趣的例子,说明复义存在于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在翻译时才让人悟出。
第二型:上下文引起数义并存,包括词义本身的多义和语法结构不严密引起的多义。这类含混在翻译中很难保存,只有他引的艾略特的诗《不朽的低语》译成汉语仍可保持原文的歧解结构:
魏伯斯特老是想着死,
看到皮肤下面的骷髅;
地下没有呼吸的生物,
带着无唇的笑,仰身向后。
燕卜荪说第二行尾的分号作用不明,若当句号读,“生物”就是第二句主语,不然,“生物”就是与“骷髅”并列的宾语。“这微小的怀疑使这首诗的主旨——超越知觉的知觉——变得更加怪异。”也就是说,两歧义复合起来了。
燕卜荪这里谈的实际上是语法性复义。马拉美曾怨叹法语不如英语之语法关系松弛,法语诗不得不被束于单解之中。他为追求复义只能破坏语法:略去标点,颠倒主宾,将分词与谓语动词混置。破坏语法实际上构成了西方现代派诗歌的最大特色之一。燕卜荪也指出:“在法语和意大利语当中,次层意义(subsidiary meanings)大都来自弄糟的语法。”燕卜荪很为英语语法“含混性”而得意,他的二百个例子中很大一部分是语法性复义。由于汉语,尤其古汉语,语法关系之松弛比英语相去不可道里计,所以语法复义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数量大得多。这种例子顺手可拾: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尽人皆知的例子。
第三型:“两个意思,与上下文都说得通,存在于一词之中。”显然,双关语是这一型中最明显的,但是难得能找到一个可译的例子:托马斯·胡德的一段讽刺诗:
厨娘,用不着我告诉你,
今天新鲜的肉,冒着热气,
明天就变成冷冰冰。
我们的肉一样,渐渐地
深如石头,厨娘,你也得死
这是锅中应有之义。
这里的“肉”(flesh),是“肉体”的双关语。
第四型:“一个陈述语的两个或更多的意义互相不一致,但能结合起来反映作者一个思想综合状态。”燕卜荪举的例子中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第八十三首:
我从来不觉得你需要打扮,
所以从不用色彩给你化妆,
我发觉(或自以为发觉)你远胜于
感恩的诗人敬献的贫乏诗章。
这一段中有许多复杂意义。就拿第二行来说,是说“我们初次结交时,我没感到你如此好恭维”?是说“我没称赞你,是因为你不需要称赞”?也就是说,是褒是贬并不清楚。
第五型:“作者一边写一边才发现他自己的真意所在”,所以一个词的意义在上文一个意义,下文又有一个意义。雪莱有诗可为例:
大地就像蛇一样
更新敝旧的丧服。
爱挑雪莱岔子的艾略特说这段诗不通,蛇并不更新(renew)其皮,燕卜荪指出这正是一种含混英语。“丧服”(weeds)一词又指野草,大地更新草木,蛇更新“旧装”,weeds一词为了照顾两头,就出现了含混。
第六型:“陈述语字面意义累赘而且矛盾,迫使读者找出多种解释,而这多种解释也互相冲突。”燕卜荪举的例子中有英国小说家麦克斯·比尔蓬(Max Beerbohm,1872—1958)的小说《苏列卡·多伯森》(Sureka Dobson)中的句子为例:
苏列卡严格说并不漂亮,她眼睛有点太大,睫毛长得超出需要……她的嘴不过是丘比特之弓的复本。
“读者不知道他们是应当着迷,还是害怕。”这种复义,我们将在第十章中再次讨论,它是一种复义兼反讽,因为并存两个意义正相反。
第七型:“一个词的两种意义,一个含混语的两种价值,正是上下文所规定的恰好相反的意义。”燕卜荪称这一型是“可以想象得出的最含混情况”。他举德莱顿的诗为例:
军号的高声呼叫
号召我们拿起武器,
声音中充满愤怒
也有死的惊悸。
那雷鸣般的军鼓
连续敲击敲击敲击,
吼叫着,听!敌人来了
冲,冲,现在已无余地。
这是大无畏,是战斗的热狂,但却有恐惧。燕卜荪说:“恐惧本身是英雄精神的一部分。”也许济慈的《忧郁颂》是更好的例子:
当忧郁猛然从天而落
好像来自哭泣的云彩
那云滋润了垂首的花朵
用四月的尸衣把青山遮盖。
春山被裹在灰色的尸衣里;四月淫雨霏霏,却又充满希望;使花复苏的美事却是云的哭泣所成。这是种什么忧郁?
在西方文学批评中,含混传统上被认为是一种弊病。黑格尔说:“在艺术的领域里没有什么是幽暗的,一切都是清晰透明的。”十九世纪英国批评家哈兹列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也说过:诗人的任务是“解开自然界组织在本题周围之网”。英国传统派诗人布里治斯(Robert Bridges,1844—1930)甚至抱怨英语中有过多的词其名词、形容词、动词形式一样。他告诫说这些词在诗中应当使用得当,使人清楚它究竟是什么词性,不然的话“诗句的力量就会被破坏”。燕卜荪引以为骄傲的,布里治斯认为大患。
这些人的观点当然不是没有受到过文学实践的挑战,但在燕卜荪之前,没有人从理论根本上推倒这种成见,可以说,燕卜荪这本书提出了迄今最有力的论证,这种挑战的力量主要来自他的例证之面广量大。他仔细分析了三十九位诗人、五位剧作家、五位散文作家的两百多段作品。这些人几乎全是古典诗人,尤以文艺复兴时代为多。他这种选择当然是有意为之的,人们总以为只有现代派诗作才是充满含混,而古典诗人是清晰的,他们没想到耳熟能详的古典名作中竟充满“含混”。
燕卜荪指出,从严格语义学角度来看,任何句子都可能有歧解。我们所关心的只是具有审美价值的含混,诗的含混,而不是作为语言必然性质的含混。而燕卜荪在对三百多页的例证作了详细解读之后,得出一个直截了当的结论:“这些含混我觉得大部分是美的。”
(第二节) “含混说”之含混
燕卜荪在书的开头不多几页处,就扬扬得意地写道:“我相信我的一些读者会体会到我写作此章时的激动心情,会体会到它对语言之本质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看法,这种看法假如不是纯粹胡说,就是极其惊人,十分新颖。”
的确,这本书给现代文学理论界一个久久回荡不息的震动。美国“新批评”派主将兰色姆说:“没有一个批评家读了此书还能依然故我。”而瑞恰慈在三十年代不断地为他这位高足欢呼,声称:“一个符号只有一个意义”的“迷信”时代已经结束。
于是许多批评家都来搜捕含混。法国的于贝(J.DHubert)用同样方法处理波德莱尔的诗,美国的斯坦福(W.BStanford)把从荷马到欧里庇德斯的希腊古典作家全篦了一遍。新批评家们则欣喜若狂。R·P·布拉克墨尔1931年写信给著名现代派诗人斯蒂文斯,谈到他读此书的激动,他说他了解得很清楚,燕卜荪描述的正是斯蒂文斯多少年来自觉地应用的诗歌语言技巧。因此他分析斯蒂文斯(1931)和哈特·克兰(1935)的文章主要是在作含混词意的分析;F·R·李维斯在批评中也不放过一个追捕含混的机会;L·C·奈茨拒绝用含混一词,但却在分析乔治·赫伯特的文章中作燕卜荪式的分析。
而且,不少新批评派设法推进燕卜荪的理论。布鲁克斯认为“非此即彼”的传统是“缺少思想的灵活性,更谈不上反应的成熟性”,只有“亦此亦彼”才是“细腻”的辨别力和微妙的含蓄。有论者甚至推而广之,说艺术想象(即我们说的形象思维)就是“设想和辨认矛盾或含混情景的能力。”
布鲁克斯三十年代末把他的反讽论直接溯源于含混论。他认为,“找出复杂性并非读诗的目的”,这复杂性必须“在发展诗的整体效果”中起作用。因此,他把反讽称作“功能性含混”(functional ambiguity),正如他把象征称作“功能性隐喻”(见六章一节)。
在燕卜荪之前,当然也有人论及这个问题,例如1922年普莱斯柯特(Frederick Prescott)用心理分析法分析诗歌得出相似结论,格雷符斯(Robert Graves)的《现代诗述评》(A Survey of Modern Poetry,1925)中对一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分析直接给燕卜荪以启发,而燕卜荪的教师瑞恰慈则早就直接论述了含混问题,他说:“诗中大部分词是含混的,要靠读者自己选择一个最能满足被诗歌形式所激起的冲动的意义。”这后半句话显然还没达到燕卜荪的理解水平,因为他认为读者在诸歧义中必须选一个。所以在燕卜荪的书出版后,瑞恰慈就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但是,对燕卜荪这本书的批评并不比赞扬少。斯多弗(Donald Stauffer)认为这种理论偏袒复杂的诗而排斥单纯的诗;休·肯纳讥之为“小孩拆表”;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人物奥尔森更以燕卜荪为靶子,展开对新批评派的全面攻击;甚至兰色姆也写了一篇题为《燕卜荪先生之糊涂》的文章,责怪他“把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与读者的主观感觉混为一谈。”
对燕卜荪的攻击出发点之纷乱本身就表现了现代文学批评各派意见之对立分歧。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搁开不谈。平心而论,读《含混七型》此书时,不能不认为燕卜荪有理。但读后仔细思考,就可以发现燕卜荪的论述,漏洞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