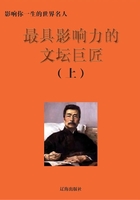手指几乎不受控制的靠向前,他们的距离本就很近,只是一伸,就已经近在咫尺,指尖轻轻一勾,沈墨的衣角便落入了她的手中。
沈墨似乎感应到,微侧首对她微笑。
景笙恍惚了一瞬,手指收紧。
不管景笙想不想承认,都得说,那确实是她一直想要的温暖。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只是,却不知能否做到生死契阔,与子成说。
一念而起,再难终。
街上妻主揽着自家夫君来看花灯会的比比皆是,两人拎着一盏或两盏花灯,点上荧荧火光,在被映得通红的天际边笑得简单幸福。
明明该是怪异的画面,蔓延出的却是意料外的温存。
景笙的心口一滞,忽然就软了,恍惚间听见自己的声音飘出。
“小墨,虚岁你也十九了吧。”
“嗯。”
“那你有没有想过终生大事什么……”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母亲尚在前线,至于媒妁……大家族恐怕不会喜欢舞刀弄枪的男儿,对于男子而言还是温婉贤淑的更讨喜些吧。”轻笑声,“更何况我的手工……”
沈墨千般万般好,偏偏手工差的一塌糊涂,在宁岚逼迫下沈墨拿出绣好的锦帕,那副牡丹图看得宁岚当场笑得岔了气,厚道如景笙也忍不住暗笑实在人不可貌相。
念头一转,景笙想起自己做的护腕,再一想,因为手臂受伤,锦盒丢在家中已经多时,心中略有些遗憾,但以后总有机会,她想。
一缕碎发自沈墨绾好的发髻边溜出,景笙小心抬起右臂,手指轻轻捻起发丝,发丝柔顺的滑过景笙的手背,柔滑润泽。
景笙的声音越发的低:“我并没有问那些,小墨,我是说如果……你想嫁会嫁个什么样的女子?”
沉吟片刻,沈墨道,声音似乎也低了下去:“大概是个能和我志同道合的人吧,父亲在世时,我就一直很羡慕他们之间那种相濡以沫的感情,如果真的要生活在一起一辈子,那至少不能相看两相厌吧。”
“这样的要求未免太简单了吧。”
沈墨笑笑:“好像是的。但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还该有什么要求。”
“比如长相,比如身材,比如家世,比如性格,再比如……”景笙一股脑说出一串要求。
沈墨仍旧笑:“这样规定有何意义,婚姻之事又并非单方抉择,姻缘到了就是姻缘,半分强求不得。”
“小墨,你信缘?”
“为何不信?”
“你不像……”平日里的沈墨恬淡安静,性子沉稳,根本联系不上信缘这种唯心的事情。
“我信。母亲能在万千人海中寻到父亲,珍爱一生,这就是缘。说起来,佛曰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们能一起走在这条大街上,又何尝不是缘?”
难得听到沈墨说出这种感性的话。
景笙攥紧了手指,温润的布料在指间摩擦,无声微笑,她也信。
凤仪亭里宁岚已提着花灯等待,仍旧是一番嬉闹,胡天胡地的乱侃闲聊,好酒与清风作伴,闲适非常。
翻墙回府时颇费了一番周折。
晚间喝多了酒,到了府里难免就觉得有些饿,摸摸肚皮,景笙带着岭儿到厨房觅食,不想竟然看到同样来觅食的景清。
景清身上的文士衫微微发皱,自己也神色恹恹。
景笙本以为景清会来找她麻烦,不想景清只是看了看她道:“以后不要老是往外跑了,有心的话就去念念书,到时候考个功名回来才是正途。”
那模样,倒真有几分长姐的架势。
看着景清远去的背影,景笙拿起锅里留给她的半笼包子,笑了。
那之后几日景笙也只呆在家,看看书,喝喝茶,写写字,吹吹笛,下下棋,偶尔发发呆,却不知帝都此时已是风云变幻。
皇王朝历,仁女帝太平二十一年。
那场浩大战争的导火索拉开了序幕。
西凉国七公子牧云晟在帝都花灯会以容颜绝色惊艳全场,无数女子趋之若鹜,牧云晟所住西凉国行馆一时门庭若市,前来拜访送礼者络绎不绝。
西凉使臣四皇女牧流芳特设宴发帖款待来客。
晚宴当日,宾客爆满皆以收到请帖为荣,牧流芳特命人奏响西凉民族乐以庆贺,高亢乐声响彻夜空,一夜不绝。
谁知第二日清晨,宾客无一人出门。
有人疑窦进行馆一看,行馆内血流成河,浓烈血腥味刺鼻扑来,数百宾客横死宴会会场,尸首交叠,无一人幸免,而牧流芳和牧云晟业已消失,人去楼空。
全城为之哗然,那一夜的乐声竟是为了遮盖这漫天的惨叫而奏,而春闱刚过不久,不少举子滞留帝都,这一晚死去的竟多为帝都一代青年才俊,直接导致皇王朝近五年乃至十年人才匮乏。
这一事件,史称七公子事件。
女帝闻之,当即震怒,下令全国通缉二人。
同时派人八百里加急赶去西凉国问讯,两国多年邦交,贸易往来,向来关系和睦,虽边关多有摩擦,但都只是局部小型争斗,却不知这次西凉是何意思。
几乎女帝的命令刚下,又传来消息,牧流芳在晋王府设伏,重伤晋王世子,刺客虽都被抓住,却在问出牧流芳下落前自尽。
晋王自请追杀牧流芳,女帝获准。
整个帝都随即戒严,随处可见灰衣的巡城司守卫握剑四处张望,看见可疑对象便上前盘问,帝都内人心惶惶。
各个茶肆酒楼里说书人将七公子事件传的神乎其神,不仅死亡人数死亡惨烈程度次次翻倍,也将牧云晟的美貌跟着翻倍,一时七公子牧云晟倒成了美艳修罗的代名词,不久后甚至能小儿止啼,如此这般,皆为后话。
却是不知,序幕已拉开,收幕之人尤未入戏。
景笙充耳不闻窗外事,只在家养伤。
岭儿不放心她的伤,也未出门,忙前忙后端茶倒水熬药,连字画也没去卖,以致所谓七公子事件景笙也是在多日以后巡城司上门搜查时方才知道。
回忆起当日见过的船楼,景笙感觉微妙。
一则看那船清减朴素的模样,实在难以想象船主会是残忍嗜杀之人,二则,却是有些遗憾,倒真该看看那位七公子长的什么模样,这也算是祸水类的男人了吧……
这样的念头不过一闪而过,真让景笙意外的,倒是那句晋王世子重伤,晋王应该只有一位世子吧,联想起绑匪的那块西凉国令牌和那日在婚宴上遇刺之事,景笙不禁有些狐疑,那位西凉四皇女牧流芳怎么就对刺杀君若亦这么感兴趣,怎么说君若亦也该和她牵扯不上什么杀父杀母杀兄杀父的仇恨,难不成是牧流芳求爱被拒,恼羞成怒,因爱生恨?
只是这么一想,就让景笙止不住捧腹。
再想想,人家这么重伤着生死未卜,自己这么开心还胡乱腹诽人家似乎不大应该……
果不其然,幸灾乐祸是要遭报应的。
第二日还没等景笙睁眼报应就来了。
一早晋王爷派人前来,特请景家二小姐去探望未婚夫。
说是特请,实际却带着半胁迫的意味。
十来个家丁围在秋竹院门口,只等景笙换好衣服洗漱完毕,就簇拥着上了轿子。
景笙坐在平稳的轿子里,颇有种被赶鸭子上架的感觉。
连探望未婚夫这种事情晋王爷都想得出,果真敬业,景笙该说是封建迷信在古代效力太强么,只不过求了一支签,晋王爷居然真就信了,也居然真就把自己最心疼的小儿子嫁给一个家世普通功名全无的庶女?
轿子停在晋王府那个无比气派的大门口,两座石像雄健挺立,银钩铁画的牌匾气势赫人,景笙一下轿子,就有人领着她向府里走,穿过一道道曲折回廊,渐渐弥漫起一股淡淡的中药味。
煮过中药的人应该都知道,那实在不是什么好闻的味道,甚至有些刺鼻。
景笙见周围人具是一副习以为常的模样,深吸口气,继续往前走。
看来君若亦还真是伤的不轻。
这时景笙倒是真有几分探病的心思,好歹相识一场,君若亦也确实不是坏人,即便平日不怎么对盘,来看望看望总不是什么坏事。
这样的念头还未消下去,“砰”一声脆响惊醒了景笙。
距景笙不足五步之遥的墙砖上褐色的液体顺着墙壁流下,墙角是一堆已经碎掉的碎瓷片,片片锋利。
房间里小厮冲跑出来,满脸懊恼收拾着地上的碎瓷片。
瞧那粉碎程度,景笙大约能猜出房间里的该是谁,也猜出房间里那位……估摸病的应该比自己想象中的要轻。
无奈跟着人走进房间,景笙暗自祈祷,君公子此时应该发泄够了。
不想,进去之后首先映入景笙眼帘的倒不是君若亦,而是个约莫二十来岁的女子。
女子盘着发髻,露出修长的颈脖,一身绯红的长衫更衬肌肤如雪,身姿窈窕,此时正背对着门口靠坐在床侧,看起来很是温婉。
自然,声音也是温婉的:“若亦,你这是做什么?”
“我不想喝。”
“气话!不想喝伤怎么能好。若是觉得药苦,我这里有带蜜饯,你喝完药,可以吃一点甜嘴。”
“不喝我的伤也会好的。”
“咳咳……你是要气姐姐是不是,快点乖乖喝药。”
“我不想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