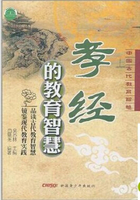(日本)原田愛
時至宋代中期,文集刊刻漸趨風行。其中,去世文人之子孫刊刻先人之文集,使其聞名於世,亦宛然成為時俗。北宋大文豪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的文集就存在着兩種形態:一種是其生前自己所編纂的,而另一種則是其死後由子嗣所編纂。蘇門子弟中主要承擔蘇軾文集之編纂工作的是其幼子蘇過(字叔黨)。本文主要聚焦於蘇過在蘇軾晚年的文學活動中所發揮的作用,以及蘇軾死後,經歷了元祐黨禍的蘇過及其子嗣又是如何來保存刊刻蘇軾文集這一問題上,力圖通過事實之考證,勾示出現在不甚明瞭的兩宋時期蘇軾文集成書與傳承的經緯。
一、蘇過與晚年蘇東坡的文學活動
從紹聖元年(1094)被貶惠州到元符元年(1098)再貶海南島,晚年的蘇軾在嶺南渡過了七年的流放生活。直到元符三年(1100)纔迎來了久違的恩赦,卻又因精癉力竭,在第二年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不幸逝世於常州,享年六十六歲。為了彰顯兄長的英名,蘇轍(字子由)所作墓誌銘中,還特意對蘇軾所留下的煌煌大著作了詳細的叙錄,其文如下:
先君晚歲讀《易》……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説》,時發孔氏之秘。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絶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嘆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為詩、騷、銘、記、書、檄、論、譔,率皆過人。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晩年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欒城後集》卷二二。本文所引蘇轍詩文均用《蘇轍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下同。
蘇轍叙錄的書名有解釋經典的《易傳》、《論語説》、《書傳》和詩文集《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等等。其中一部分為蘇軾晚年所作,大致為草稿,其時並未成書。如元符三年(1100)七月,蘇軾在北歸之途叙其“所撰《書》《易》《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别本”蘇軾《東坡志林》卷一《記過合浦》,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同年八月又云:“《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蘇軾《與鄭靖老》第三簡,《蘇軾文集》卷五六,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下同。由知蘇軾晚年的這些文稿都沒有公諸於衆。毫無疑問,這些文集不得及時刊刻乃緣於朝廷禁令何薳《春渚紀聞》卷五《張山人謔》云:“紹聖間,朝廷貶責元祐大臣,及禁毀元祐學術文字。有言《司馬温公神道碑》乃蘇軾撰述,合行除毀。於是州牒巡尉,毀折碑樓及碎碑。”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下同。,因此纔會有蘇軾撫摩草稿嘆云:“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不求今世,唯願死後這些書籍能重見天日,流傳人世。
在上文中蘇軾雖沒有明確其所託之人,但從現存文獻記錄來看,當是指其幼子蘇過關於蘇過的先行研究;有曾棗莊《三蘇後代考略》、《蘇叔黨與他的〈斜川集〉》(《三蘇研究曾棗莊文存之一》收錄,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版),舒大剛《三蘇後代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版),楊景琦《蘇過斜川集研究》(北京:文津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紹聖元年(1094)蘇軾被貶惠州之際,特地從三個兒子中挑選了最年幼的蘇過隨行。紹聖二年(1095)八月一日,蘇軾在惠州回顧此事云:
軾之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諱閏之,字季章,享年四十有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於京師,殯於城西惠濟院。過未免喪而從軾遷於惠州,日以遠去其母之殯為恨也。念將祥除,無以申罔極之痛,故親書《金光明經》四卷,手自裝治,送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中,欲以資其母之往生也。蘇軾《書金光明經後》,《蘇軾文集》卷六六。
從上引蘇軾文章中可知,元祐八年(1093)八月一日,蘇軾的繼室王閏之在開封去世,蘇軾被貶之時,蘇過正和其兄長一起為母親服喪。蘇過隨同父親一起去惠州,在表期將滿時,還特意書寫了《金光明經》四卷“手自裝治”,由此亦知蘇過還擅長裝裱書卷。
那麽蘇過又是如何來具體協助蘇軾的呢?對於此,晁説之談到:
惟是叔黨,於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之所須者,一身百為,而不知其難。翁板則兒築之,翁樵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為能須臾樂乎先生者也。晁説之《宋故通直郎眉山蘇叔黨墓誌銘》,《嵩山文集》卷二〇,《四部叢刊續編》本,下同。
可見蘇軾在嶺南的生活,無論大事小事都是由蘇過來打理的。甚至連蘇軾“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不僅如此,蘇軾所要閱讀的書籍也多由蘇過抄寫:
兒子到此,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為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蘇軾《與程秀才》第三簡,《蘇軾文集》卷五五
蘇軾被貶海南島時已經年過六十了,所以文中自稱“目昏心疲”。抄寫這種相對辛苦的事,就全部交給了蘇過。其時,蘇過對蘇軾文學活動的幫助還不僅抄書,蘇軾作詩撰文後,其文中用典的確認也無疑需要得到蘇過的協助。蘇軾對於自己詩文中所引用的詩文典故非常謹慎,對於此,何薳在《春渚紀聞》中談道:
秦少章言,公嘗言:“觀書之樂,夜常以三鼓為率。雖大醉歸,亦必披展,至倦而寢。”然自出詔獄之後,不復觀一字矣。某於錢塘從公學二年,未嘗見公特觀一書也。然毎有賦詠及著譔,所用故實,雖目前爛熟事,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何薳《春渚紀聞》卷六《著述詳攷故實》。
秦覯(字少章)是蘇門四學士之一秦觀(字少游)的弟弟,也是蘇軾的弟子。元豐二年(1079)的烏臺詩案以後,蘇軾雖變得“不復觀一字”,但寫作詩文時,其“所用故實,雖目前爛熟事,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蘇軾被貶嶺南之後,其他子弟均未隨行,這個工作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蘇過頭上。
正是對晚年蘇軾的詩文寫作有過直接的參與,蘇過纔有可能展開對《東坡後集》二十卷的編纂工作。對於蘇軾文集,南宋胡仔云:“世傳《前集》乃東坡手自編者,隨其出處,古律詩相間,謬誤絶少。……《後集》乃後人所編,惜乎,不載和陶諸詩,大為闕文也。”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八,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認為《東坡集》是蘇軾自編的文集,所以誤謬很少,但對《東坡後集》稍有微言,認為其“不載和陶諸詩,大為闕文也”。其實這是一個誤解。據現有資料可知,《東坡後集》編纂於海南島。同時期與蘇軾同年及第的好友劉庠的孫子劉沔編輯了蘇軾文集二十卷,蘇軾曾明言如下: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所編錄拙詩文二十卷。……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刳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為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蘇軾《答劉沔都曹書》,《蘇軾文集》卷四九。
考慮到在嶺南時蘇軾的身體狀況,極有可能蘇過就是文集再編工作的具體承擔者。而且從上文可知,對於蘇過的文學素養,蘇軾也有過不菲的評價。將自己的晚年文集編纂工作託付給自己最信任的兒子,可以推測出,蘇軾之所以在三個兒子中唯獨挑選了蘇過隨行,並不單單是因為蘇過年輕而已,其中確有一番良苦之用心。再回到胡仔批判“後人所編”《後集》的這個問題上。很顯然,其批判乃是源於對蘇軾晚年生活不甚明瞭的誤解之上。其實,並非蘇過故意將這組詩落於《東坡後集》之外。《和陶詩》一直到蘇軾死之前都沒有定稿,最後是由同樣參與了這組詩創作的蘇轍編纂成書張耒《和歸去來詞》題自注云:“子由先生示東坡公所和陶靖節歸去來詞及侍郎先生之作,命之同賦。耒輒自憫其仕之不偶,又以弔東坡先生之亡,終有以自廣也。”《柯山集》卷五,《張耒集》上下册,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版。《東坡後集》未收其詩乃是事出有因的。
二、蘇東坡去世後的蘇過
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蘇軾病故後,蘇過和侄子蘇符(蘇邁次子)在葬地汝州小峨眉山為其服喪。崇寧二年(1103)七月服滿以後,蘇過沒有立即仕宦,而是去了叔父蘇轍所居住的潁昌府(今河南許昌),一直到政和二年(1112)六月,蘇過在潁昌府住了將近九個年頭。
蘇過服滿之後一直賦閑於蘇轍處,需要整理亡父蘇軾的筆墨遺稿是一個原因,據大觀二年(1108)蘇轍所云“及自龍川還潁川,侄過出子瞻遺墨”蘇轍《追和張安道贈别絶句并引》引,《欒城三集》卷一。,可知蘇過之處保存了許多蘇軾的遺澤。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受到了元祐黨禍的牽連,無法立即出版蘇軾文集。崇寧元年(1102)五月,蘇軾等元祐黨人開始遭到貶責。八月,宋徽宗下旨禁止黨人子弟任官京師。九月,修建了有一百一十七位元祐黨人姓名的“元祐黨籍碑”,以示天下。元祐黨禍大約延續了二十來年,其間屬於元祐黨人的詩文都被禁止公開流行。其中尤以蘇軾詩文為最,當時曾再三下詔嚴令蘇軾詩文流傳於世,將《東坡集》歸為禁書。但事情往往是適得其反,如朱弁《曲洧舊聞》所言:“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夸。”朱弁《曲洧舊聞》卷八《東坡詩文盛行》,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民間之人願出重金購買蘇軾詩文,還往往以此為榮。作為蘇軾的兒子,蘇過就更有必要保存先父的遺稿了。
由現存資料來看,蘇過主要負責的是蘇軾的經書類以及《東坡後集》校正與編纂。蘇過首先和其兄蘇迨一起編輯了一部《先公手澤》,也就是《東坡志林》的原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云:“《東坡手澤》三卷,蘇軾撰,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謂《志林》者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據蘇轍“政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之語蘇轍《老子解》卷末《再題老子道德經後》,《四庫全書》本。,蘇過的編纂活動大約結束於政和元年(1111)。蘇轍雖然沒有提到蘇過,只言及了蘇軾長子蘇邁之名,但蘇邁從大觀元年(1107)至政和二年(1112)一直在嘉禾赴任,不太可能直接參與編纂活動。
另外,蘇過自己也非常注重對先人遺著的保存與流傳,如開封的藏書家蔡氏所藏李之儀《仇池翁南浮集序》云:“蔡君家世輦轂之下,軒輊無所系,而能以退為進,父子之間,自為知己。獨於(東坡)先生南遷已後,所見於抑揚者,博訪兼收,所較他日之得為備。”《姑溪居士後集》卷一五,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在《夷門蔡氏藏書目叙》一文中,蘇過寫道:
嗚呼,讀其書,論其事,想見其人,凜然於千載之上,修身立言,可以垂訓百世之後。……予惟古之逸民,未嘗以一藝自名於世,雖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以其所踐履者絶乎流俗故也。龐德公隱於鹿門,妻子躬耕。或疑其不仕,以為何以遺子孫也。龐公曰:“我遺子孫以安,不為無所遺也。”今居士口不談世之爵祿,身不問家之有無,所付子孫者獨書耳。龐公之意,殆無以過此。蘇過《夷門蔡氏藏書目叙》,《斜川集》卷九,舒大剛等《斜川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6年版,下同。
蘇軾也“所付子孫者獨書耳”,蘇過尊重先父的遺志。而且,因為當時蘇軾詩文被高價買賣,所以僞作橫行,魚目混珠。蘇過在《書先公字後》一文中云:
昔之人有欲擠之於淵,則此書隱。今之人以此書為進取資,則風俗靡然,爭以多藏為誇。而逐利之夫,臨摸百出,朱紫相亂十七八矣。嗚呼,此皆書之不幸也。……過侍先君居夷七年,所得遺編斷簡皆老年字,落其華而成其實。……公昔為《藏經記》,初傳於世,或以為非公作,其後知之者以為神奇。在惠州作《梅花詩》,有以為非,至有以為笑。此皆士大夫間以文鳴者,其説能使人必信,其謬妄如此。乃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可為流俗痛哭。過謹書藏於家。蘇過《書先公字後》,《斜川集》卷八。
蘇過在蘇軾的身邊受教七年,對當時“爭以多藏為誇”“臨摹百出,朱紫相亂”的世情非常不滿,“謹書藏於家”。對於保存蘇軾遺稿,蘇轍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對於此事,蘇轍曾賦詩如下:
少年喜為文,兄弟俱有名。世人不妄言,知我不如兄。篇章散人間,墮地皆瓊英。凜然自一家,豈與餘人爭。多難晚流落,歸來分死生。晨光迫殘月,回顧失長庚。展卷得遺草,流涕濕冠纓。斯文久衰弊,涇流自為清。科斗藏壁中,見者空嘆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蘇轍《題東坡遺墨卷後》,《欒城三集》卷二
元祐黨禍之後,蘇轍把蘇軾的草稿隱藏在家中。當蘇轍次子蘇适到西京(洛陽)赴任時,蘇轍令蘇适將蘇軾“詩書”轉移至西京保管。正是由於蘇氏一族的努力,蘇軾的詩文纔能被保全至今。
另一方面,直接參與了蘇軾文學活動的蘇過,還為後人留下了一些對蘇軾詩文的講釋。譬如,後來為蘇軾詩作注的趙夔,就曾請教過蘇過。趙夔在《注東坡詩集序》中云:
頃者赴調京師,繼復守官,累與小坡叔黨遊從至熟。叩其所未知者,叔黨亦能為僕言之。僕既慕先生甚切,精誠感通。趙夔《注東坡詩集序》,《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首,《四部叢刊初編》本。
對於這段話之真僞雖然還有些爭論《四庫提要》云,鑒於趙夔及蘇過的生死年代、經歷,這篇序文是書肆假託的。西野貞治《關於東坡詩王狀元集注本》(《人文研究》第十五號卷第六號,大阪市立大學文學部,1964年版)認為,如果解釋“頃者”不是“近來”,而是“以前”的意思的話,他們還是有會見的可能性。,但毫無疑問的是可以從這則材料推測出,在時人的心目中,蘇過纔是對蘇軾詩文最熟悉最有解釋權的第一人。晁説之在為蘇過所撰的墓誌銘裏也大筆特書:“則(東坡)先生之立言者,叔黨之功業也。惜乎,不及使人有見於此”。對蘇過在傳承蘇軾詩文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予以了非常高的評價。
三、蘇過的孫子——蘇嶠與蘇峴
繼承蘇過的“功業”,為蘇軾文集流傳於世而作出貢獻的人還有蘇過的孫子蘇嶠與蘇峴(蘇過長子蘇籥的兒子)。蘇嶠的生卒年不明,蘇峴則生於政和七年(1117),但兩兄弟的年紀不會相差很大。蘇峴出生時蘇過四十六歲,正在郾城上任。宣和二年(1120)後,蘇過學晚年蘇轍自號“斜川居士”隱居潁昌府,和當地朋友們互贈詩文,以教兒孫家學為樂。宣和五年(1123),蘇過重新被朝廷任命為中山府通判,同年十二月暴死於赴任途中,終年五十二歲。對於其子孫,晁説之《宋故通直郎眉山蘇叔黨墓誌銘》云:
(叔黨)娶范氏,蜀忠文公之孫,承事郎百嘉之女。男七人:籥、籍、節、笈、簟、篴、笠。女四人,長適將仕郎常任俠。孫男二人:嶠、峴。晁説之《宋故通直郎眉山蘇叔黨墓誌銘》《嵩山文集》卷二〇,《嵩山文集》原闕這部分,從《永樂大典》補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