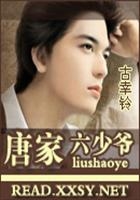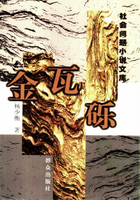按,在先秦文獻,“文”既有作為“禮樂制度”之義的用例。而“時文”連用,指當時之禮樂制度,則是自晉始。如《藝文類聚》卷三九《禮部》中引陸機《侍皇太子宣猷堂詩》:“時文惟晉,世篤其聖。明明隆晉,茂德有赫。”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三九《禮部中》引陸機《侍皇太子宣猷堂詩》,第2册,第714-715頁。又,陸雲《大安二年夏四月大將軍出祖五羊公於城南堂皇被命作此詩》云:“時文惟晉,天祚有祥。聖宰作弼,受言既臧。有赫斯庸,勳格昊蒼。景物臺暉,棟隆玉常。”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卷六,上册,第699頁。按,此兩處之“時文”皆是指當時之禮樂制度。此二條引文之大意皆是頌晉世禮樂文明之盛。又“群氓反素,時文載鬱。耕父推畔,魚豎讓陸。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此處之“時文”,《文選六臣注》卷三五中呂向注曰:“時文,謂禮樂也。”《文選六臣注》卷三五張協《七命》,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影印,第546頁右上欄。又郭茂倩《樂府詩集·郊廟歌辭六》之《豫和》:
於昭上窮,臨下有光。羽翼五佐,周流八荒。誰其饗之,時文對揚。虞經夏典,茲禮未遑。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六《郊廟哥辭六》,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册,第82頁。
按,上引之郊廟歌辭中之“時文”,其指“當時之禮樂制度”甚明。又如《全唐文》卷二四八李嶠《宣州大雲寺碑》:
立最上之乘,不棄於聲聞小道;用無為之理,猶存乎禮樂常教。辟四果之門闈,訓三雍之典業,然後遠心近行,俱得所聞,傾樽酌蠡,各滿其量。憲章乎法寶,而度律既周;經緯乎時文,而綱羅畢備;登一世於解脱,躋群生於仁壽。《全唐文》卷二四八,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第3册,第2509頁下欄。
按,上引之碑文前以“聲聞小道”與“禮樂常教”相對而言,故可知後與“法寶”相對之“時文”,即指“當時之禮樂制度”而言,言要以“法寶”為憲章,以“當今之禮樂制度”為經緯。又《全唐文》卷五〇四權德輿《朝議大夫洋州刺史王君夫人博陵縣君崔氏祔葬墓誌銘》:
先是洋州猶子興平尉源長,受夫人之理命,曰:“吾與爾二門,積德奕代。銘表必咨時文。先舅之碑,吏部趙郡李公實為之,先君之志,從翁大傳文貞公實為之。”《全唐文》卷五〇四,第5册,第5131頁下欄。
按,上條引文中之“銘表”關乎喪葬祭祀之大禮,故必咨“時文”。由此可知此處之“時文”亦當是“當今之禮樂制度”,謂“銘表”之制,必定咨於禮制。又鄭絪《享太廟樂章》:
於穆時文,受天明命。允恭玄默,化成理定。出震嗣德,應乾傳聖。猗歟緝熙,千億流慶。《全唐詩》卷三一八,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0册,第3582頁。
按,此中之“時文”,即是“當時之禮樂制度”,謂當今之禮樂制度,受自天命。此處以“禮樂”代指大唐,蓋有言大唐禮樂繁盛、文明隆興之義。又《全唐文》卷四〇九崔祐甫《齊昭公崔府君集序》:
公嗣子宗之,學通古訓,詞高典册,才氣聲華,邁時獨步。仕於開元中為起居郎,再為尚書吏部員外郎,遷本司郎中。時文國禮,十年三月,終於右司郎中,年位不充,海内歎息。《全唐文》卷四〇九,第5册,第4191頁下欄。
按,此處“時文”與“國禮”並列,其義蓋相近,“時文”即指當時之禮樂制度。又《全唐文》卷七八九劉蛻《上禮部裴侍郎書》:
及今年冬,見乙酉詔書,用閣下以古道正時文,以平律校郡士,懷才負藝者踴躍至公。蛻也不度入春明門,請與八百之列,負階待試。《全唐文》卷七八九,第8册,第8256頁下欄。
按,此處“以古道正時文”,此“古道”即是“古之禮樂”,而“時文”即“當時之禮樂制度”,謂“以古之禮樂”以正“今之禮樂”,始合於古聖先王之道。
四、文章意義上的“時文”
在文章意義上的“時文”一般作為“時下流行之文”解,但是在一般的辭書上,其後往往會多加上一句“舊時對科舉應試文體的通稱”。當然,這個解釋本身是沒有什麽太大的問題,但是卻容易讓人誤解,以為“時文”在“舊時”就只是對“科舉應試之文的通稱”。但是,將“時文”認為是舊時對科舉舉業應試文體的通稱,則是甚為不妥。然而,這一認識卻並不少見,除上所説的幾部有影響的辭書外,持此説者尚有不少著名學者。如程千帆先生的《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中談到《行卷對推動古文運動所起的作用》中説:“古文家應舉時,雖然遵守功令,必須以時文——甲賦、律詩應試,卻往往以古文行卷。”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8-69頁。程千帆先生之稱唐時科舉之文為時文,未知所據。又,朱瑞熙在《宋元的時文——八股文的雛形》一文中説:“宋元時期的時文,是專供貢舉和學校考試使用的一種特定的文體。”朱瑞熙《宋元的時文——八股文的雛形》,《歷史研究》,1990年第3期。但是,在考察了宋元的文獻發現這一説法並不符合實際。就筆者所知,在“時文”有“時下流行之文”的意思之初,並非指“科考舉業之文”,也非一種專供貢舉和學校考試使用的特定的文體。更非“八股文”,而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時下流行之文”。即便是在科舉考試這一制度確立以後,因科舉考試的影響而使科舉舉業之文盛行,成為“時下流行之文”,而使科舉制藝與“時下流行之文”合二為一。但是在這層意義上,“時文”也是隨不同的時代而變,遠不止《漢語大詞典》和《中文大辭典》等辭書所列的“唐宋律賦”、“明清八股”。
(一)科舉考試確立之前的“時文”
在科舉考試這一制度正式確立以前,“時文”一詞與“文章”相關的解釋即是一般意義上的“時下流行之文”。就目前的文獻可知,這一層意義主要是在漢魏以下至唐前期,而唐武則天以後,隨科舉制度的完善,科舉的影響加大,“時文”一詞指“科舉舉業之文”的意思逐漸掩蓋了“時文”早期一般意義上的“時下流行之文”的意思,但是這並不是説科舉完善後“時文”的意義就不再指一般意義上的“時下流行之文”,而是出現的情況漸少而已。一般意義上的“時下流行之文”,如江淹《傷友人賦》:“既思遊兮百説,亦窮精兮萬里。愛時文之綺發,賞賦豔兮錦起。磬古今之寶贐,彈竹素之琛奇。”俞紹初,張亞新《江淹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頁。此中的“時文”與“賦豔”相對,又此文前部分多懷友人之才,盛贊友人之文,故由此可推知,此處指“時文”,蓋指“時下流行之文”,亦即當時所流行之浮豔華麗之駢文。又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卷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上册,第673-674頁。其中的“時文”即純指“當時之文章”而言。此處即以建安“當時之文章”,而觀出其時“雅好慷慨”之風格。又《全唐文》卷五一八梁肅《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既薨之來載,皇上負扆之暇,思索時文,徵公遺編,藏之御府。於是公之文辭,光大一門。近歲肅以監察御史徵謁京師,始得集錄於公子繁,且以序述見託。公之摯友諫議大夫北平陽城亦謂子曰:“鄴侯經邦緯俗之謨,立言垂世之譽,獨善兼濟之略。藏在册牘,載於碑表。唯斯言不可以不傳於後。”嘗謂肅曰:“吾子辭直,盍存乎篇序?”既詠歎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貽諸好事者。凡詩三百篇,表、志、碑、贊、序、議、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獨著其目云。《全唐文》卷五一八,第6册,第5259頁下欄。
由上引材料可知,文中盡言李泌之詩文,又“思索時文”句後緊接“徵公遺編,藏之御府”,故亦可推知,其中之“時文”亦即指當時之文。
當然,“時下流行之文”之一意思的稱呼,在唐及其以前多有“今文”“今體”之稱。如梁簡文帝蕭綱《與湘東王書》:“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擠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全梁文》卷一一,《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影印本,第3册,第3011頁上欄。李商隱《樊南甲集序》:“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為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敕定奏紀,始通今體。”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文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4册,第1713頁。但是,將其稱作“時文”的亦是有的。
(二)科舉考試舉業之文
“時文”由作為一般意義上的“時下流行之文”進而指科舉考試的舉業之文,大概出現在唐代。在唐代,科舉制度得以完善,科考大興,科舉制度為寒門士子打開了仕途之門,故而大量的讀書之士趨之若鶩。既然如此,針對科考應試的各種文體,莫不成為士子所傾心的對象。故,當時的讀書人對這些應試文體的大量寫作流傳,而流行於世。故而“時文”由一般意義上的“時下流行之文”而受科舉舉業之文的影響,遂轉為“科舉舉業之文”。在唐代的孟郊《擢第後東歸抒懷,獻座主呂侍御》:
昔歲辭親淚,今為戀恩泣。去住情難並,别離景易戢。夭矯大空鱗,曾為小泉蟄。幽意獨沉時,震雷忽相及。神行既不宰,直致非所執。至運本遺功,輕生各自立。大君思此化,良佐自然集。寶鏡無私光,時文有新習。慈親誡志就,賤子歸情急。擢第謝靈臺,牽衣出皇邑。行襟海日曙,逸抱江風入。蒹葭得波浪,芙蓉紅岸濕。雲寺勢動搖,山鐘韻噓吸。舊遊期再踐,懸水得重挹。松蘿雖可居,青紫終當拾。孟郊《孟東野詩集》卷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07頁。
按,孟郊及第後獻主座,此處之“時文”即是指的唐時科舉之文。唐代科舉進士科考試多用詩賦,但是此處之“時文”是確指何種科舉文體則不詳,若就後來明清之時文指“八股”而言,即推唐宋為“律賦”則甚為不妥。
在宋代,進一步完善科舉制度,增加取士人數,科舉更盛,且宋代因“偃武修文”,對文人優待,故而使士子對科舉更是趨之若鶩。故而,在宋代的“時文”很多時候是就科舉舉業之文而言。而在宋代,“時文”所具體的指的對象也不盡相同。在宋初,“時文”最開始是就“西崑體”而言。歐陽修《記舊本韓文後》:
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卷二三,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據世界書局1936年版影印,上册,第536頁。
按,此處之“時文”是與作為“古文”的韓文相對的,但同時因其“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故而亦有“科舉應試之文”的意思在内。但是此處之“時文”還並非完全指科舉考試之文。在某種意義上説,其還是側重在“時下流行之文”。歐陽修《與荊南樂秀才書》:
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麗彼,以為浮薄,惟恐不悦於世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采,屢以先多士。及得第以來,自以前所為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為,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為彼則獲譽,為此則受禍,此明效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為功,亦不易也。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四七,上册,第321頁。
由材料可見,此處之“時文”不僅流行很盛,而且對科舉也產生很大影響,且在此,“時下流行”與“科舉舉業之文”開始合二為一。但是需要指出,這裏的“時文”所指的“西崑體”並不是一種文體,而是一種行文的風格,一種“雕章麗句”的文風。如楊億在《西崑酬唱集序》中所言:
予景德中,忝佐修書之任,得接群公之遊。時金紫薇錢君希聖、秘閣劉君子儀,並負懿文,尤精雅道,雕章麗句,膾炙人口。予得以遊其牆藩而咨其楷模,不我遐棄,博約誘掖,寘之同聲。因以歷覽遺編,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發於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楊億《西崑酬唱集序》,王仲犖《西崑酬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2頁。
按,由上之序中可知,西崑體只是一種行文的風格和方式,是以一種“歷覽遺編,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的寫作方式,寫出一種“雕章麗句”風格之文,即以李商隱為宗,而專取其豔麗雕鏤、駢麗等的一種文風。又如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一五《與君貺學士書》:
復自翰林楊公唱淫詞哇聲,變天下正音四十年,眩迷盲惑,天下瞶瞶晦晦,不聞有雅聲。嘗謂流俗益弊,斯文遂喪。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一五,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80頁。
又同書卷一三《上蔡副樞書》:
今夫文者以風雲為之體花木為之象,辭華為之質,韻句為之數,聲律為之本,雕鏤為之飾,組繡為之美,浮淺為之容,華丹為之明,對偶為之綱,鄭衛為之聲,浮薄相扇,風流忘返。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一三,第1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