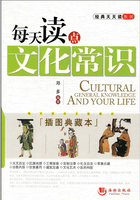詞中以女神傳釋人間佳麗的飄逸出塵、麗質天生,但也遺世獨立,幽居獨處。而除了承續傳統,夢窗詞女神書寫的特色,尤在於與自然相關的女神也往往直接成為自然的代稱,彷彿在其特具神話思維的靈視中,女神與自然原本即渾然一體。如望見雲雨的同時,“旦為行雲,暮為行雨”宋玉《〈高唐賦〉序》,《文選》(長沙:嶽麓書社,2002年9月),第587頁。的巫山神女也隨之出現眼前,一片雲煙縹緲,頗具夢幻色彩:
新煙初試花如夢,疑收楚峰殘雨。(《齊天樂》)
醉雲又兼醒雨,楚夢時來往。(《解躞蹀》)
作為女神化身,雲亦能醉,雨亦能醒。同樣的,神話中奔月而去的嫦娥,也幾乎被詞人視同明月本身,化成冰清玉潔卻孤獨遠隔、似含哀怨的意象:
延桂影,見素娥梳洗,微步瓊空。(《聲聲慢·幾漕新樓,上尹梅津》)
寶階斜轉,冰娥素影,夜清如水。(《絳都春·題蓬萊閣燈屏,履翁帥越》)
小窗春到,憐夜冷孀娥,相伴孤照。(《花犯·謝黃復庵除夜寄古梅枝》)
怨娥墜柳,離佩搖葓,霜訊南圃。(《古香慢·賦滄浪看桂》)
此外,花與女神在夢窗詞中也常密不可分,詞人似乎總在花的形貌氣息中,幻覺般的望見或者感受女神的存在:
行雲夢中認瓊娘,冰肌瘦,窈窕風前纖縞。(《花犯·謝黃復庵除夜寄古梅枝》)
渾似瀟湘繫孤艇。見幽仙,步凌波,月邊影。(《夜遊宮·竹窗聽雨,坐久,隱几就睡,既覺,見水仙娟娟於燈影中》)
湘娥化作此幽芳,凌波路,古岸雲沙遺恨。(《花犯·郭希道送水仙索賦》)
詞中或以巫山神女與女仙許飛瓊摹寫風煙之中纖細雪白的梅花;或以凌波微步的洛神傳釋水仙在夢中幻化的迷離影象;最後一首則如前引《過秦樓》,以女神為花的化身,幽香縹緲,多情遺恨。
由上可見夢窗詞中女神與雲雨煙水花月等幾乎融為一體,除了呈現朦朧遠隔、飄逸迷離的形象,有時亦微露情思,甚至多情有恨,使詞中的自然彷彿是女神臨在的世界,神影縹緲、空靈夢幻,饒有情思。
除了摹寫自然,借由女神意象的形塑,夢窗亦傳釋其對於情的體悟與感慨:
衣白苧,雪面墮愁鬟。不識朝雲行雨處,空隨春夢到人間。留向畫圖看。慵臨鏡,流水洗花顏。自織蒼煙湘淚冷,誰撈明月海波寒。天澹霧漫漫。(《望江南·賦畫靈照女》)“靈照女”典故出自《傳燈錄》,乃襄州居士龐藴女,名靈照,後作為人女的代稱。觀此詞所用娥皇女英、李白撈月典故,此畫中女子似是投水而亡。
此詞所寫畫中女子,一身白衣,容色似雪,予人冰清玉潔的印象,然愁字則透露神情,並引出以下二句。詞人變化巫山神女神話,喻此女子彷彿是為情來降人間的女神。“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的巫山神女,與楚王的會遇原是一場短暫的春夢,所謂“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白居易《花非花》。,來去自在,不為情累,纔是女神的真實性格案:據葉舒憲《高唐神女與維納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12月),巫山神女在神話中具有愛與美之神的神格,而就宋玉二賦形塑之神女形象,確實美麗多情,但也能放下情累,不受牽絆,展現女神雙面特質。然夢窗卻幾乎顛覆了女神形象,未能忘情,迷戀春夢,來降人間,但也因此付出代價,芳魂遠逝,徒留畫中蒼白愁容供人憑弔。下片則是一片鏡花水月,寫女子生前為情所苦,無心對鏡梳妝,而“流水洗花顏”或寫其以淚洗面,同時暗示投水自沉如花落水中,隨即引出以下娥皇女英自沉湘水及李白撈月溺水等傳説,“自”、“誰”、“冷”、“寒”等字,與上片之“空”字前後呼應,隱約透露詞人感慨,情之為物美麗卻空幻,為情至此,實為枉然。末句以景結情,漫漫迷霧如女子愁思,亦如女神縹緲無託的幽魂。
除了形塑女神多情樣貌,透露多情遺恨的感懷,多數夢窗詞中的女神如巫山神女及洛水女神等,往往亦還原其神話形象,如一場春夢,一抹驚鴻,美麗而短暫,結局總是雲散夢醒或凌波而去,如神話及文學中屢見的邂逅女神主題參坎伯《千面英雄》及張淑香《邂逅神女——解〈老殘遊記二編〉逸雲説法》,《語文、情性、義理——中國文學的多層面探討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臺大中文系,1996年4月)。,既引人經歷擁有的美好,也備嘗失去的憾恨,而除了回憶,似乎什麽也不曾留下。在耽於書寫追憶主題的夢窗詞中參宇文所安《繡户:回憶與藝術》,氏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12月)。,行雲夢影、凌波微步等女神意象即常出現於歌酒相伴,風月流連的往日回憶中:
記行雲夢影,步凌波、仙衣翦芙蓉。念杯前燭下,十香搵袖,玉暖屏風。(《八聲甘州·和梅津》)
西湖舊日,留連清夜,愛酒幾將花誤。遺襪塵銷,題裙墨黯,天遠吹笙路。(《永遇樂·探梅次時齋韻》)
春來雁渚。弄豔冶、又入垂楊如許。困舞瘦腰,啼濕宮黃池塘雨。碧沿蒼蘚雲根路。尚追想、凌波微步。小樓重上,憑誰為唱,舊時金縷。(《絳都春·余往來清華池館六年,賦詠屢矣,感昔傷今,益不堪懷,乃復作此解》)
柳暝河橋,鶯晴臺苑,短策頻惹春香。當時夜泊,温柔便入深鄉。詞韻窄,酒杯長。翦燭花、壺箭催忙。共追遊處,凌波翠陌,連棹橫塘。十年一夢淒涼。似西湖燕去,吳館巢荒。重來萬感,依前喚酒銀罌。溪雨急,岸花狂。趁殘鴉、飛過蒼茫。故人樓上,憑誰指與,芳草斜陽。(《夜合花·自鶴江入京,泊葑門有感》)
在詞中女神意象總是與往昔的美好時光、旖旎情境交織一片。然佳人的香氣、墨痕、歌聲與一同流連美景的時刻,如今縱使沉浸追憶,或舊地重臨,也依然是消逝遠隔,難以尋回,確實如一場夢幻。此外,在時序感懷的詞中,透過今昔情境的對照,更凸顯失去的悲涼:
麗花鬥靨,清麝濺塵,春聲遍滿芳陌。竟路障空雲幕,冰壺浸霞色。芙蓉鏡,詞賦客。競繡筆、醉嫌天窄。素娥下,小駐輕鑣,眼亂紅碧。前事頓非昔。故苑年光,渾與世相隔。向暮巷空人絶,殘燈耿塵壁。凌波恨,簾户寂。聽怨寫、墮梅哀笛。佇立久,雨暗河橋,譙漏疏滴。(《應天長·吳門元夕》)
上片寫月光下的蘇州元夕,佳人鬢影衣香,詞客競騁文思,良辰美景醉人,然過片一句“前事頓非昔”則將所有賞心樂事、佳人麗影一概推向往昔,與如今獨處的境遇彷如是完全阻隔無法跨越的不同世界。獨立黃昏空巷,面對殘燈塵壁、簾户無聲,在詞人心中,往昔的美好彷彿隨著凌波而去的女神一併消逝,只留憾恨。詞中洛水凌波的女神意象,似亦暗指曾被無心錯過而黯然離去,如今已是重尋無蹤的女子。
以下詞亦與時序追憶有關,借女神意象所構設的天地亦予人女神臨在的幻覺,真幻今昔,重疊交錯:
捲盡愁雲,素娥臨夜新梳洗。暗塵不起。酥潤凌波地。輦路重來,彷彿燈前事。情如水。小樓薰被。春夢笙歌裏。(《點絳唇·試燈夜初晴》)
元夕前夕,雨後初晴,臨安城中應是分外喧鬧。上片雨收雲散,初晴的夜空明月皎潔,詞人望之如洗淨塵妝、鉛華不御,冰清玉潔的嫦娥;至於大地經雨之後亦是一片清潤,即使佳人行樂,步履搖曳,也不揚起半點塵埃,而詞人望之卻有一種縹緲迷離,彷彿隔著一層氤氳水氣,眼前的鬢影衣香、婀娜身影,剎時如洛神凌波,予人如在夢幻,不甚真實的感受。“暗塵不起”變化“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的神話情境,似乎亦是無情的暗示,即在詞人眼中這女神臨在無雲無塵的清淨天地,如今已是與其無關的無情世界。下片“重來”二字,將上片所寫情景又隱約推向往昔,眼前所見,今昔交錯,所不同者不在表象而在詞人内心感受。“情如水”一語雙關,寫往日之柔情似水,呼應其後之小樓薰被與笙歌相對;然同時亦指情如逝水,如今重來,昔日的温馨情境,已如消散的一場春夢。
行雲夢影與洛水凌波,女神在夢窗詞中常只留下朦朧的背景或殘餘的香氣,隱喻逝去的美好時光、美麗情緣,然如前引《應天長》所見,在某些詞中如水如雲的女神意象也隱隱指涉一位離去的女子,一段遠逝的愛情:
燈火雨中船。客思綿綿。離亭春草又秋煙。似與輕鷗盟未了,來去年年。往事一潸然。莫過西園。凌波香斷綠苔錢。燕子不知春事改,時立鞦韆。(《浪淘沙》)
南樓墜燕。又燈暈夜涼,疏簾空捲。葉吹暮喧,花露晨晞秋光短。當時明月娉婷伴。悵客路、幽扃俱遠。霧鬟依約,除非照影,鏡空不見。别館。秋娘乍識,似人處,最在雙波凝盼。舊色舊香,閑雨閑雲情終淺。丹青誰畫真真面。便只作、梅花頻看。更愁花變梨霙,又隨夢散。(《絳都春·燕亡久矣,京口適見似人,悵怨有感》)
詞中可見夢窗漂泊世路異鄉為客的感傷,而對舊情的執著似乎是其流離無繫的生涯中唯一不變不移的依託。《浪淘沙》詞中的西園對詞人而言應是具重要回憶與特殊意義的地方,在其他詞中也一再出現如《風入松》:“聽風聽雨過清明。愁草瘞花銘。樓前綠暗分攜路,一絲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曉夢啼鶯。西園日日掃林亭。依舊賞新晴。黃蜂頻撲鞦韆索,有當時、纖手香凝。惆悵雙鴛不到,幽階一夜苔生。”。莫過西園,卻過西園,只見已無人跡的路上綠苔滋長,不知人事已非猶立鞦韆的燕子,更反襯詞人心中的惆悵。凌波香斷,離去的女子不再歸來,就連曾留下的餘香也幾近消散。此外,《絳都春》所叙情境更透露詞人的戀舊與癡情。一位眉眼相似的女子,短暫的帶來驚喜與慰藉,然閑雨閑雲,又隨夢散,夢窗借神話中看似多情卻無情的女神真實形象,傳釋其内心的理性領悟,深知對方終究情淺,無法替代所思念的佳人,也終究明白如此奇遇很快又將如夢消散。
經詞作閱讀可見,夢窗詞中女神意象並不只作為典故或者點綴,作為自然的化身,情思飄渺的女神再次展現詞人充滿神話思維的心靈,自然天地在其靈視之中,原是女神臨在、萬象有情的世界。此外,傳續女神在神話中的雙重面相,夢窗也重塑女神或多情遺恨,或無情遠離的對立形象,既傳釋其對情的感慨思索,也寄託其對往日的依戀與失去的遺憾。透過女神書寫,夢窗亦鏤刻其内心在執著多情與渴望忘情間的矛盾衝突。
(二)夢窗詞中的樂園意象
神話中的樂園仙境,大抵是人們為了滿足生存或追求更理想生活的願望,而幻設想像的虛擬時空。其情境不外物產豐饒、寧靜和諧、淳樸自在,無衰老死亡,無疾病戰亂,或者美景天然,樓閣輝煌,仙樂飄飄等。然看似弔詭卻極為真實的是,滿足或投射人們自由、長生、享樂等願望的樂園仙境,也往往被幻設在遠隔難至的高山、大海或天上,甚至是與現實世界相對的夢幻他界,或者再也回不去的往昔歲月中。常人不是始終無法到達,便是必須有偶然機緣、特殊助力纔能置身其境,而一旦離去,便再也難以重返參李文鈺前揭書第五章《宋詞中的他界神話運用》。美好而遠隔,難以到達又容易失落,樂園仙境等神話意象亦如女神具有矛盾對立的内涵,烙印人們深刻的追尋體驗參李文鈺《漂泊與思歸——從東坡詞中的他界意象論其内在追尋》,《漢學研究》第27卷第1期(2009年3月)。
在詩詞傳統中,氣象華麗的樂園仙境常用於壽詞,點染富貴長生的氣息與祝願。夢窗亦見相關詞作:
紫霄承露掌,瑤池蔭密,蟠桃秀、蠡蓮綻。……繡裳五色,昆臺十二,香深簾捲。……賜長生玉字,鸞迴鳳舞,下蓬萊殿。(《水龍吟·壽嗣榮王》)
萬壑蓬萊路。非煙霽、五雲城闕深處。璇源媲鳳,瑤池種玉,煉顏金姥。(《宴清都·壽榮王夫人》)
此外,書寫山林寺院或山水美景的作品中,夢窗亦借樂園仙境意象傳釋其處身自然、如在塵外的感受,詞中描寫的景致或透露夢窗理想的樂園情境,清幽絶塵,美景相伴,而心中則空明虛靜,無欲無情:
長安林外小林丘。碧壺秋。浴輕鷗。不放啼紅,流水通宮溝。時有晴空雲過影,華鏡裏,翳魚遊。綺羅塵滿九衢頭。晚香樓。夕陽收。波面琴高,仙子駕黃虯。清磬數聲人定了,池上月,照虛舟。(《江神子·賦洛北碧沼小庵》)
屋下半流水,屋上幾青山。當心千頃明鏡,入座玉光寒。雲起南峰未雨,雲斂北峰初霽,健筆寫青天。俯瞰古城堞,不礙小闌干。繡鞍馬,軟紅路,乍回班。層梯影轉亭午,信手展緗編。殘照遊船收盡,新月書簾纔捲,人在翠壺間。天際笛聲起,塵世夜漫漫。(《水調歌頭·賦魏方泉望湖樓》)
詞中的碧壺、翠壺,或指海上蓬萊案:海上三神山蓬萊、方丈、瀛州,又名蓬壺、方壺、瀛壺,以壺器暗示其與世隔絶的封閉特徵,參高莉芬《蓬萊神話——神山、海洋與洲島的神聖叙事》(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3月)。,或指道教神話中的壺天幻境壺天幻境神話見葛洪《神仙傳》及《後漢書·方術傳》,乃謫仙壺公所攜酒壺中的幻境。其意象内藴參李文鈺前揭書第五章第三節。,華麗豐饒、寧靜無爭,但皆具有封閉的特質,與塵世隔絶,並非常人輕易可至。夢窗借此神話意象賦寫山林清景及登樓望湖沉醉美景的心情,二詞情境雖或有獨遊與衆樂、超然與處群的區别,但處身世外如在仙境的感受卻一致的流露詞中。此或透露夢窗心中的理想樂園,乃是封閉而與世遠隔,盡可能遺卻塵累,不受世俗所擾的純淨世界。而如此對塵世之外的嚮往,對現實世界逃離或怯避的心理,當與夢窗脆弱敏感的性格夢窗詞中常用“欺”、“壓”、“侵”、“驚”、“恐”、“怯”、“怕”等字,如《夜遊宮》:“香苦欺寒勁。牽夢繞,滄濤千頃。”《一寸金》:“秋壓更長,看見姮娥瘦如束。”《齊天樂》:“瘦骨侵冰,怕驚紋簟夜深冷。”《夢芙蓉》:“畫圖重展,驚認舊梳洗。”《花犯》:“但恐舞、一簾蝴蝶,玉龍吹又杳。”《淒涼犯》:“小鈿梳唇,洗妝輕怯杳。”《聲聲慢》:“繡茵展,怕空階驚墮,化作螢飛。”透露其對外界敏感而脆弱的性格。,以及處身末世的沉重憂患感有關。
下引書寫貴族園林的詞中,夢窗在渲飾其華麗境象、享樂情味之餘,亦構築了與世隔絶且不受時間干擾、破壞的樂園:
暖波印日,倒秀影秦山,曉鬟梳洗。步帷豔綺。正梁園未雪,海棠猶睡。藉綠盛紅,怕委天香到地。畫船繫。舞西湖暗黃,虹卧新霽。天夢春枕被。和鳳筑東風,宴歌曲水。海宮對起。燦驪光乍濕,杏梁雲氣。夜色瑤臺,禁蠟初傳翡翠。喚春醉。問人間、幾番桃李。(《掃花遊·賦瑤圃萬象皆春堂》)
瑤圃乃理宗母弟、度宗生父趙與芮的宅邸,萬象皆春堂即在其中。詞中有關園林景致與宴樂情境的書寫,充滿華麗富貴如在瑤臺仙境的氣息,特殊的是最後數句,日日夜夜,任憑時光流逝,園中依然一片永恆的醉人春意,與人間的四季流轉、幾番桃李有所不同。除了呼應萬象皆春堂的命名,亦顯示夢窗的樂園書寫最强調的仍是與人間的區隔,不僅空間,即時間亦與俗世不同,而神話中樂園時間流速緩慢不易覺查或甚至無時間性的特質,亦無意間在夢窗筆下復現。如從宗教現象學家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的神聖時空觀點解讀參氏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1年1月)。,類此末世中華麗園林的建構與命名,具有再創世的模擬儀式意義,滿足人們逃避歷史、重返無罪無惡之純真時代的内在渴望。而夢窗如此與世隔絶,不被外力或時間干擾破壞的樂園書寫,亦透露内心類似的祝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