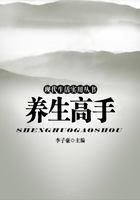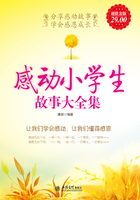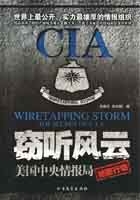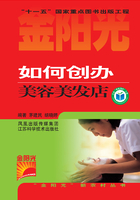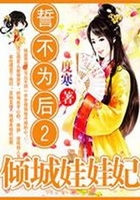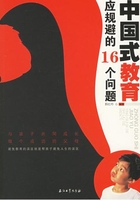“气聚而有形,形载而有质,质具而有体,体列而有官,官呈而性著焉”这句话不但适用于人,也适用于禽兽,那禽兽的气质之性又如何呢?难道人禽之别也是“习”所导致?难道因为从气质中看出天地之性,便断定性为气质所有?种子破土而出,可以说是土在发芽吗?刘宗周有一个“体认亲切法”,其前两句为(附图):“身在天地万物之中,非有我之得私(◎);心包天地万物之外,非一膜之能囿(◎)。”第一幅图大圈中的小圈是身(气质),大圈是天地;第二幅图小圈为天地,大圈为心。从中可以看出心并不受身的限隔,所以性也应该如此。既然性依气质而立,那么宇宙之性如何依人的气质而立?所以,他于气质上求性理的观点同他摆脱气质限隔、心合宇宙的观点有冲突。黄宗羲认为,这个气质是个“公共之物”,“公共之物”就有公共之性,所以“非有我之得私”!但是天下“公共之物”
多矣,如此岂不使人物化,并泯灭万物气质之性的差别了吗?另外,以“我”为“公共之物”如非亲证,也难免落为以意造境。其实,正是心体使性体有了着落,并非气质使性体有了着落。气质乃是使物理有了着落,但性体并非物理。刘宗周于此未辨。
由于刘宗周过于想把学术思想统一起来,所以他的一些理论有时就会显得有些牵强附会。比如,他文中所说“恻隐之心,喜之变也”等。刘宗周的这种联系自然是依据于传统五行理论,喜和仁于五行同属于木,恻隐之心属仁,自然同属于木,为东方之气,所以他推出恻隐之心和喜气的联系,并以此打通心、性、气。但这种联系过于机械,为什么恻隐之心不是“哀之变也”,反倒是非之心是“哀之变”?恻隐之心的确是仁,也潜藏着护生之意,但它会产生一种对受伤害者哀的情绪以及对伤害者怒的情绪,而不会是喜的情绪。
刘宗周对此其实是有所考虑的,但是他的解释很勉强,给人一种强为说通的感觉。他在《学言》中说:“恻隐,心动貌,即性之生机,故属喜,非哀伤也。辞让,心秩貌,即性之长机,故属乐,非严肃也。羞恶,心克貌,即性之收机,故属怒,非奋发也。是非,心湛貌,即性之藏机,故属哀,非分辨也。又四德相为表里,生中有克,克中有生,发中有藏,藏中有发。”我们从这段议论中可以看出,刘宗周已经预测到别人可能产生的疑问,并且这些疑问很可能就是他本人的疑问。刘宗周在对别人做出解释的时候也在作自我说服,只是他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不知是否真的能说服他自己。他要把《中庸》和孟子的观点统合到一起。其实《中庸》只对情绪分类,而孟子只对情感分类,二者本不相同,所以也不必强求一致。
总之,在刘宗周的心性哲学里,其心性的合一同他理气合一的观点一致。性为心之条理即是理为气之条理;其性情的合一同他不作已发、未发的区别的观点相一致,性不是未发,情不是已发,更不是因情见性,而是性之情;其离气质之性无义理之性的观点和他离气无理的观点相一致,理从气上求,义理从气质上求。这些观点在刘宗周的心性哲学里是一有都有的。只有这样,他的理论才显得特点鲜明,并且理论之间的相互呼应也会使理论能够自圆其说了。当然,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他的理论还是有一些纰漏的,尤其是他对性的理解同他对心的认识发生了矛盾。并且,他对先儒也有误会,认为他们“外心言性”,以性为心之对待物。
其实先儒所谓“明此性”固然是心去明此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心性的分离。心去明性并不是去明一个外物,而就是心去明它自己,佛家的“明心见性”所明的也是自家家当。故此,明性之说既不病性,也不病心。倒是刘宗周的从气质之中求性理似乎是在形器中求物理一般,有使人物化的倾向,似乎人性只似物理,不是见性之语。刘宗周在这里有些顾此失彼了。
(第二节 气质之性、天地之性与习
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的问题是紧跟前面一个问题而来的,所以这个问题前文已经有所涉及。这里针对刘宗周对性的认识作进一步分析。
如前文所述,刘宗周是将人性问题统合到“气质之性”上的,即所谓“性只有气质,义理者气质之所以为性”。他将天地之性(或者说天命之性、义理之性等)并归气质之中,成为气质之理,因为“毕竟离气质无所谓性者”。因此他对先儒义理之性和天地之性的分法提出质疑:“程子又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是性与气,分明两事矣。凡言性者,皆指气质而言也。或曰:‘有气质之性,有义理之性。’亦非也。盈天地间止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之性。如曰‘气质之理’即是,岂可曰‘义理之理’乎?”其实刘宗周和程朱等人的分歧就在于气质之性是否是善的,千言万语无非围绕着这个根本问题展开。刘宗周认为气质之性已经是善的,因此义理之性的说法没有必要;而程子所说的气质之性则是善恶之杂,因此有必要点出一个纯粹至善的义理之性来。故此,程子所说的“义理之性”其实等于说“至善之性”。如果把刘宗周所批驳的“义理之理”理解为“至善之理”,也就不再有问题了。程子如何会糊涂到其所谓“义理之性”是“义理之理”的地步?
不论张载、二程还是朱子都是将人之恶归于气质之性,而刘宗周和他们一样也是性善论者。他既将人性归于气质,自然不会像张载等人那样将气质之性视为恶,但他同时也不能回避恶,必须对人的恶做出解释。在他看来,人的恶是由于“习”于恶,是后天环境的影响。这个观点是他晚年的定说,和他壮年时的观点有些不同。
他在40岁所著的《论语学案》中,借着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话发表了自己对“气质之性”和“习”的看法: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此孔门第一微言,为万世论性之宗。“性相近”犹云相同,言性善也。圣人就有生以后,气质用事,杂糅不齐之中,指点粹然之体,此无啬,彼无丰,夫何间然者?但人生既有气质,此性若囿于气质之中,气习用事,各任所习而往,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而无算,圣贤庸愚,判若天壤矣。此岂性之故也哉!夫习虽不能不歧于远,然苟知其远而亟反之,则远者复归于近,即习即性,性体著矣……愚谓:气质还他气质,如何扯着性?性是就气质之中指点义理者,非气质即为性也。清浊厚薄不同,是气质一定之分,为习所从出者。气质就习上看,不就性上看。以气质言性是以习言性也。从这段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刘宗周认为气质和性之间是不相干的,即所谓“气质还他气质,如何扯着性?”“此无啬,彼无丰”,“非气质即为性也”,二者分明是两回事。性自然可以主宰气质,但也可能被囿于气质之中而不能显现。这里所说的性似乎依然是天地之性或义理之性,可见当时的刘宗周并没有将义理并归气质。
但此时的刘宗周的观点已经和前人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就是他强调了习。气质之性也因此在他这里有了不同的含义。在刘宗周看来,人的习影响人的气质,清浊厚薄因习的不同而变化,因此所谓的气质之性其实就是习性。他对于习的重视有些类似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只是行为主义者不会认为人有什么本性。
他的这种观点后来发生了变化。他不再以习性为气质之性了,而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生”(即气质)为本性了,但是对习的重视却保留了下来,只是不再以它为气质之性,而是视为影响气质之性的东西了。他在晚年所著的《证学杂解》中谈到了因习而导致的气质之病:
人生而有气质之病也,奚若? 曰:气本于天,亲上者也。
故或失则浮,浮之变为轻,为薄,为虚夸,为近名,为淫佚,为巧言令色,为猖狂,为无忌惮。又其变也,为远人而禽。质本乎地,亲下者也。故或失则粗,粗之变为重,为浊,为险,为贼,为贪戾,为苛急,为怙终,为无耻,为首鼠观望。又其变也,为远人而兽,亦各从其类也。夫人也,而乃禽、乃兽,抑岂天地之初乎?流失之势积渐然也。故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又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然则气质何病?人自病之耳。刘宗周对气质的理解很有他独到之处。他将气、质分言,并以气为阳、质为阴,可谓别具一格。张载在用“气质之性”一词时未必有此意。刘宗周尤其对人的轻浮之态有敏锐的照察。但他认为,不是气质本身有病,而是“人自病”,是习使人离了本初之性,流为禽兽。从中可以看出刘宗周已经将气质之性同习性分离,不再说“以气质言性是以习言性”这样的话了。也正因为作了性和习的区别,使得他认为“慎习”并不与本性相交涉。似乎在他看来,性可生习,但习不可以变性,因此人最佳的状态仍然是打并归一的,即“即习即性”。他在《习说》中就阐述了这样的观点:
或有言“学问之功,在慎所习”者。予曰:“何谓也?”曰:
“人生而有习矣,一语言焉习,一嗜欲焉习,一起居焉习,一酬酢焉习。有习境,因有习闻;有习闻,因有习见;有习见,因有习心;有习心,因有习性。故曰‘少成若性’,并其性而为习焉,习可不慎乎?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犹生长于齐、楚,不能不齐、楚也,习可不慎乎?”曰:“审如是,又谁为专习之权者而慎之?”其人不能答。予曰:“学在复性,不在慎习。”或曰:“何谓也?”予乃告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浑然至善者也。感于物而动,乃迁于习焉。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斯日远于性矣。无论习于恶者非性,即习于善者,亦岂性善之善乎?故曰:‘性相近,习相远。’盖教人尊性权也。”“然则学以复性也,如之何?”曰:“性不假复也。复性者,复其权而已矣,请即以习证。习于善则善,未有不知其为善者;习于恶则恶,未有不知其为恶者。此知善而知恶者谁乎?此性权也。故《易》曰:‘复以自知。’既以知其为善矣,且得不为善乎?既以知其为恶矣,且得不去恶乎? 知其为善而为之,为之也必尽,则亦无善可习矣。知其为恶而去之,去之也必尽,则亦无恶可习矣。无恶可习,反之吾性之初,本无恶可习也。此之谓浑然至善,依然人生之初,而复性之能事毕矣。”“然则习可废乎?”
曰:“何可废也!为之语言以习之,则知其语言以慎之;为之嗜欲以习之,则知其嗜欲以慎之;为之起居以习之,则知其起居以慎之;为之酬酢以习之,则知其酬酢以慎之。如是则即习即性矣。凡境即性境,凡闻即性闻,凡见即性见。无心非性,无性非习,大抵不离独知者近是。知之为言也,独而无偶,先天下而立,以定一尊,而后起者廪焉,是之谓性权。”或者恍然而解曰:“吾乃知慎习之功,其必在慎其独乎!”首肯之而去。此《习说》中和刘宗周对话的不必实有其人。我们可以把它看做刘宗周本人的一次自我对话,是中年刘宗周和晚年刘宗周的观点对话。这个对话者虽然没有说气质之性即是习性,但他和壮年刘宗周一样以习为性,而与此相对应的工夫就自然是“慎习”。按照刘宗周的思维习惯,他一定会向主人翁处讨分晓,故此他会意识到“慎习者谁”的问题。操此“慎习之权”者自然比“习”更为根本。如果“习”是“感物而动”的结果,那么操“慎习之权”者就是“人生而静”的“性”。既然性比习更为根本,且本身又是至善的,所以刘宗周自然就把工夫落脚到了率天命之性上了,此之谓“复性权”。在刘宗周看来,慎习的工夫并不彻底,即便是习于善,仍然不是本性之善,仍是人伪。他说:“‘率性之谓道。’惟性善,故率之亦无不善,若说性外别有个习性之善,可谓不揣其本,正恐连言善亦都是伪善。”只有工夫着眼于性体,才是真正自然的善。这样的善实无善可说。“慎习”应该被“慎独”取代,所谓的“独”即是“天命之性”。但是,慎独之说虽代替了慎习之说,并不意味着习可以废。因为起居、饮食等日用之间无不是习,无习就等于没有了生活方式,关键要发挥独体(即性体)之知的作用,这样知善为善,知恶去恶,就使得所习成为性体的流露,“即习即性”了。
刘宗周的这段议论有一个立论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操“慎习之权”者,就是本性。它比它所监察的“习”更为根本。可见刘宗周对习和性两者在理论上的区别是十分清楚的。他说:
真性中岂有习染? 后来世故交接,遂有习染。习之既深,口之所言,身之所行,即至衾影梦寐,无非是习。然此点良心却又完完全全,是以为小人者,虽习染深厚,至于呼之即应,叩之即觉,又不因习染深浅,遂分利钝。可以说,刘宗周的观点没有错。但是对此二者的区别在实践中并不容易,因为心仍然可以依照一种习照察另一种习,如果一种习做得主,心仍然可以依照这种习对其他习作出反应,就如同后念对前念的照察那样。如果这种习本身就是善的,并且人从出生以来便浸染此习,此习以个人后天无意识的形式存在于人心之中,我们如何能体察出它是习是性呢? 难道因为已经考虑到“无论习于恶者非性,即习于善者,亦岂性善之善乎”这样的问题就能证明刘宗周已经解决了个人后天无意识与自性之间的区别? 恐怕刘宗周也于此未辨:
先生说:“人生孩提知爱,稍长知敬,盖因幼时真性如八窗玲珑,四宇洞达,无所遮蔽。不知向后如何一转,便蒙蔽了。此一转甚是害人,大抵日转日甚,世故日深,真性日蔽,声色货利之场为所汩没者多矣。譬如看风水者,指南针虽不动,而移步换形,东西易面矣。然虽被习染,而真性未尝不在。”刘宗周所说的“人生孩提知爱,稍长知敬”,是从陆九龄所说的“孩提知爱长知钦”来的。事实上刘宗周和陆九龄一样,都是基于习得的观念思考问题,并未进行观察。儿童和成人相比的确是敞开的、未被社会化的、无后天观念的,但这并不是说真性在婴幼儿期便一定会展现。真性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仍需启发。根据今天的观察实验,并没有可靠证据证明爱和敬在人之初会有无条件的展现,而相反的证据却相当多。如果前人的假设是真的,那么“孔融让梨”的故事就不可能流传。所以,刘宗周本人常用习得的观念思考问题,他所认识的真性也是习得的。因此,刘宗周对问题的认识可能非常深入,但问题并不见得会靠“认识到”来解决,“知病”终不同于“治病”。我们对刘宗周是否能真正将习和性二者区分开表示怀疑。
由于刘宗周强调了慎独,使得习在他的理论中的重要性似乎有所降低,性的地位得到凸显。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如果抛开刘宗周对自己理论的理解,我们认为从本质上讲他仍和壮年时期一样以习为气质之性,只不过有两点差别:(1)两个时期对气质之性的理解有所不同;(2)壮年时期他明确自己以习为性,而老年时期所谓的“性”可能是另一种更隐秘、更有力的习,只是他对此无意识罢了。所以,如果刘宗周所说的自性并不真正完全是他的自性,那么在他理论中表现出的尊性抑习就不一定会是真实的;他的“慎独”就有可能是另一种“慎习”,是以一种习控制另一种习。虽然刘宗周和今天许多人本主义者一样主张发扬自性,但自性如何容易认得? 看来石梁所谓“识认本体”的说法恐怕也不可轻废。他自己的一些自性仍然被文化和环境所埋没,并且他《人谱》的谱人工程也是一套塑造人的程序。